本文摘自图书《为人父母》第二章(由磨铁图书·大鱼读品授权),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成为父母的意义看起来不言自明,毕竟每个人都被照料过,虽然这个照料者可能是父母、祖父母、继父母、合作性父母以及养父母。不管这些经历有何不同,成为父母无疑蕴含着一种期待,这是个人的期待,也是身边人的期待。很多这种期待与社群、社会和文化中的性别角色与正确教养方式挂钩。人们从自己的父母那里学会怎么做父母,最后成为他们父母的一个翻版,学界对这一观点已有深入研究。
然而,对教养方式的家庭、社会和文化溯源,却和另一大批研究的结果相左:大量研究表明,教养方式的诸多层面,尤其是亲子依恋关系层面,都是由生理、神经和神经激素来决定的。本章我们将囊括生物学、心理学、神经科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探讨几个相关的话题。
一、有多少是我能控制的?
成为父母的过程常被看作一个简单的自然过程。父母在其中经历的变化通常就被解释成一种生理上的发展,研究一下生理机制和脑化学就不难理解。确实,怀孕期间的很多生理和神经变化已日渐成为研究的焦点。神经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认为,孕期及分娩后的许多荷尔蒙变化对早期亲子关系,尤其是亲子间情感纽带的建立至关重要。
生理上来说,怀孕和分娩会给女性的身体带来暂时以及永久的变化。这包括早孕反应(白天有持续的呕吐感,一些女性甚至整个孕期都会有这种反应)、对强烈气味和特定食物的异常敏感及饮食冲动;强烈的疲惫感和波动不定的性欲;体温忽高忽低,爱出汗,有晕厥感,情绪反应强烈;经常哭,有时候是因为生气,有时候是因为沮丧。虽然在英国高达90%的孕妇表示在怀孕早期有恶心想吐的感觉,但这种症状看起来其实也是有文化特异性的。新几内亚和牙买加的女性就不太说自己有呕吐感,而是说自己睡不好,真的梦见自己怀孕了,容易感染,还容易起疹子、得溃疡。这说明,单纯的生理解释是远远不够的。
在怀孕的头几周里,孕妇的新陈代谢水平开始提高,由于需要大量的能量来维持胎儿的基本需求,孕期的头三个月里孕妇的血糖和血压开始降低。许多西方的妈妈报告自己在怀孕和产后照顾宝宝的头几周里有“脑雾”(brain fog)症状。这种现象常被称作“婴儿脑”(baby brain),即孕妇和产后的母亲脑力功能下降,记性差,反应慢,这常常反映出的是行为上的紊乱和异常。
一些研究表明,孕期女性的大脑会发生变化—脑室(分泌脑脊液的组织)之类的部位体积会增大,而大脑整体的体积则在减小,并在孩子足月的时候达到最小值。但脑部变化是暂时的,孕妇的脑体积会在孩子出生的几周至几个月后再次增长。孩子六个月大时,孕妇的脑体积普遍就可以恢复到孕前水平了。
艾尔斯琳·霍克兹马(Elseline Hoekzema)与同事在荷兰和西班牙开展过研究,在怀孕前和分娩后用核磁共振技术(MRI)扫描父亲和初为人母的女性的脑部,发现男性的脑部没有发生改变,但女性显示出一系列变化:最引人注意的是,影响前后皮质中线部、双侧外侧前额叶以及颞叶部分的灰质体积大幅度缩小。 灰质的改变反映出许多神经变化,比如大量突触、胶质细胞 (一种非神经元细胞,可以维持稳态并形成髓磷脂,包裹保护中枢神经系统和周围神经系统的神经元)和神经元数量减 少以及树突结构的改变。
这种现象被称为突触修剪( synaptic pruning ),许多神经科学家认为这是孕期大脑回路精修微调的核心过程,它使脑功能特化,对健康的认知、情绪和人际发展至关重要。霍克兹马和同事们认为,失去部分灰质并不意味着失去了部分脑功能—事实上这一过程更像是一种优化,让大脑可以在孕期内更高效地运转。进一步的神经病学研究表明,这种让许多女性产生“脑雾”的孕期灰质变化,也许会帮助形成分娩后的亲子依恋关系,其实也就是一种转换母亲身份的适应性过程(当然了,前一章说过,依恋关系本身依旧有争议)。而神经生物学研究的发展也已证明,负责社交行为、共情和焦虑的脑区(前额叶、中脑和顶叶)会被孕期和产后的荷尔蒙变化激活。
伦敦大学学院的安德里亚斯·巴特斯(Andreas Bartels )和塞米尔·泽基(Semir Zeki)称,母亲感到的潮水般的爱意、强烈的保护欲和持续的忧虑,都反映出女性的大脑在孕期和产后会做出调整,以此促进依恋关系的形成—而这通常被认为是为人父母的先决条件。他们的研究表明,母爱涉及一组相互重叠的特殊脑区,这些脑区是受到孕期和产后荷尔蒙变化调控的。实验中,他们让20位志愿者母亲看自己孩子的照片,又让她们看她们同时期认识的其他孩子的照片,测量并比较了两种情况下她们的脑活动。实验发现,与看到其他孩子时相比,母亲在看到自己孩子时,对孩子的依恋关系会抑制与负面情绪和人际判断相关的脑区。因此他们认为,对他人的强烈感情不但会抑制负面情绪,还会影响到此人进行人际判断的相关神经系统。
科学家们近来才开始揭示孕妇/新妈妈的行为与她们荷尔蒙变化、神经活动和脑化学的可能联系。研究女性的大脑或许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新妈妈们的产后抑郁和焦虑情绪。六分之一的女性称有过产后抑郁,也有很多人报告自己有过焦虑和强迫症的想法,尤其是想去查看孩子的呼吸、睡觉和进食。催产素(也用于引产)已被确认为一种所有哺乳类动物建立母婴纽带的重要驱力;它在孕期的分泌显著增加并在产后维持在高位。丹佛大学家庭与儿童神经科学实验室的金雨阳(Kim Pilyoung)记述了催产素水平如何在母亲看到孩子甚至听到孩子哭闹那一刻开始上升,她认为催产素同样会影响父亲对孩子的反应。这种变化对亲子之间的纽带建立非常关键,金雨阳将这种父母体验比作坠入爱河。
耶鲁儿童研究中心的詹姆士·斯温(James Swain)提出 了一种模型来描述,比如说,孩子的哭声如何启动父母的特定脑回路,调动他们的情绪和奖惩机制,激起他们的情绪和行为反应,让他们跑去查看孩子。这种刺激信号包括哭声、 视觉刺激、身体接触以及体味。斯温研究了人类父母的脑成像并结合了早期动物研究,提出“父母脑”(parental brain) 模型来预测母亲的大脑、情绪和行为将如何响应宝宝发出来的信号。斯温把母亲脑回路的激活方式描述为一种条件反射式的照料冲动,这种冲动被编入了她们的情绪和行为反应,是父母之爱和依恋关系的体现。他认为,进一步了解神经系统对为人父母的影响,对长期的亲子依恋关系和孩子心理健康和适应力发展都有深远的意义。
脑部变化也不限于女性。埃亚尔·亚伯拉罕(Eyal Abraham)和同事们开展的研究注意到,男性开始照顾孩子后,他们的大脑也发生了改变。有充分证据表明,父亲也会有类似荷尔蒙增多现象,这其中就包括与母亲和孩子接触后诱发的催产素分泌增多。他们的催产素水平与他们对孩子表现出的爱意成正相关。很多这种生理变化被定义为适应性过程,可以帮助父母和他们的孩子建立依恋关系。然而,也有很多研究者质疑,神经学研究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养育期间的适应性过程和学习过程。尽管孕期和产后的生理和荷尔蒙变化不可忽视,神经学研究确实不能彻底解释清楚,为什么全世界的男男女女会有那么多种为人父母的方式。此中许多差异要涉及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不仅要研究全球范围内教养方式的差异,还要考察社群、社会和文化影响是如何塑造教养方式的。
人类学家罗伯特·莱文(Robert LeVine)广泛地研究了跨文化间的教养方式,他的成果展示了教养方式间的差异,同时也表明这些方式都是习得的,可以帮助新父母更好地适应他们自己的文化和社群环境。所以,尽管我们不能否认,在孕期和照料孩子头几年里,许多的父母会经历各种生理和神经变化,但不同的社会也会鼓励新父母采取不同的、合乎规则的教养方式。
在婴儿死亡率高的地方,有时候,母亲对估计活不下去的孩子是没有什么感情投入的。人类学家南希·舍佩尔—休斯(Nancy Scheper-Hughes)写过很多关于巴西东北部棚户区婴儿死亡现象的文章。她描述了那里的穷苦母亲对婴儿强烈的矛盾心态—她们不“相信”这些孩子能活下来,所以几乎不投入什么感情。她们不承认也不认同独立的人格,一个名字会反复给母亲生下的几个孩子用好几遍, 她们也几乎不会公开地悼念死去的孩子。
很小的孩子是基本不被当作人看的,只有当他们有了活力的迹象,有了求生的愿望,年龄再大些,这时的他们才值得感情投入,母亲也才会承认他们这时才更有人的样子。这些母亲倾向于忽略没有什么活力的、病恹恹的孩子。她们认为有些孩子是注定活不下去的,因此不会拼命去救活他们,也不会给(通常是买不起)他们药吃,对他们的死亡抱着听任甚至冷漠的态度。这些发现得到了一套完善的人类学研究的支持,研究重点指明了家庭、社群、社会和文化因素是如何塑造出全球范围内诸多的教养方式的。
二、我会成为自己父母的翻版吗?
社会学家弗兰克 · 富里迪( Frank Furedi )在《偏执的育儿》(Paranoid Parenting) 中写道,成为家长不光是接受自己有孩子后的新角色,也是对自己身份的一次认同。但是,我们又很难把新家长的愿望、抱负和社会施加的压力相剥离。任何社会在任何时候都会给新手父母提出一些建议、期许和要求,告诉他们成为父母的意义,以及他们应该怎么做。
显然,人们会从自己的父母和照顾他们的人那里学到一些为人父母的知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些教养方式会在家庭中代代传承,也就是英国开放大学的温迪 · 霍尔韦(Wendy Hollway) 教授所说的代际回响效应 (intergenerational echoes)。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的心理学教授杰伊 ·贝尔斯基(Jay Belsky)和同事们在 2009 年提出了一个理论模型,试图解释家长的教养行为是如何被自己父母的教养方式塑造的。而这个话题的早期研究则出现在 20 世纪 50 年代左右,不过那时的侧重点在于代际传递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以及为什么像虐待和好斗这样的行为会在家庭中代代沿袭。
代际研究深度关注的是,父母的身份认同如何从他们早年经历的家庭中发展而来。这类研究通常使用个人对家庭生活的反思和回忆,询问父母和祖父母一辈的人是怎样抚养自己的孩子的,以及他们自己又是怎样被抚养成人的。此外,这类研究也经常会问小孩子,他们觉得父母的教养方式怎么样,觉得自己想成为或会成为什么样的父母。
举例来说,一个孩子在人生头几年里就会接触到各式各样的行为方式,而这些或多或少都会影响他们的思维、想法以至未来行为。比利时鲁汶大学的伊莎贝尔 ·罗斯克姆(Isabelle Roskam) 在 2013 年开展了一项横跨三代人的研究,她发现祖父母、父母和孩子都明确提到一些相同的教养方式,其中包括热情体贴等积极行为以及严苛管教等更为消极的行为。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教养行为都是代代相传的。这项研究发现,经历过温情和支持型教养的孩子更愿意成为使用同样教养方式的家长,而不是成为控制型家长,尤其是管教严苛的家长。
和采用其他自陈式方法的研究一样,上述的结果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记忆和解读,所以可能会产生问题。而且想象自己从孩子变成虚构的家长的未来,然后想象自己会采取什么样的教养方式,显然不能很好地预测你实际上会变成什么样的家长。况且,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会沿袭自己父母的教养方式和行为。有些人不赞成甚至否定自己受到的教养方式,并且竭尽全力确保自己将来不会采取同样的方式。就像安德鲁 ·所罗门写的:
只要孩子跟我们有些相似,他们就会是我们最真诚的 崇拜者;只要他们跟我们有些不一样,他们就会是我们最 严厉的批评者。一开始我们就引诱孩子模仿我们,希望自 己得到这世间最大的肯定:孩子会选择按照我们的价值体 系生活下去。我们自己跟父母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无比自 豪,可孩子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又悲伤不已。
心理学家奥利弗 ·詹姆士(Oliver James)在他写的《去你的》(F*** You Up)中敬告各位家长提防把人惹毛的可能性,并在另一本《如何不惹毛他们》(How Notto F*** Them Up)里为准父母提供了详实的案例和解决方案,避免跟孩子大发雷霆。詹姆士引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成果,描述了孩子的行为被父母的行为塑造,父母的行为又被他们的父母塑造这一复杂的过程 — 而且这个过程亘古不变。这类研究对认清家庭内部的学习传承显然有益,但不能清楚地解释,为什么有的孩子会认同并固化一些教养方式,有的孩子却不会。
而且这种观点会有一种暗示,就是孩子完全是被动的,教养不过是对他们“做完就完了”( done to them)的一类事。儿童神经病学家迈克尔 ·鲁特爵士( Sir Michael Rutter)认为,人们之所以低估孩子自身对教养方式和亲子互动的塑造作用,就是因为没有考虑到无数代家长在有二胎之后他们都能观察到的一个现象,那就是,孩子之间差异可以这么大,他们跟孩子的关系也可以如此不同。
加拿大心理学家史蒂芬 ·平克( Steven Pinker)认为,人们很容易就“把孩子看成是一堆等着塑形的腻子”,从而忽视了他们对父母的行为有何等重要的作用。我们有必要在这里特意解释一下这个观点,因为很多关于教养方式的当代学说都认为,在教养关系中,孩子与父母的地位同样重要。
亲子关系近些年来已成为研究的焦点,尤其是“双向性”(bidirectionality)这一概念,即亲子之间会持续地相互影响的现象。大量研究关注了儿童及其家长的个性与行为特性,以此理解亲子关系将如何影响父母的身份认同发展以及儿童在 家庭中的发展过程、学习过程以及信念习得的过程。这类研究非常复杂,因为它们想要揭示的是亲子互动与行事“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当然,关于教养方式还有很多难懂的问题。家长的一些行为经常是难以理解的,甚至很难用常理解释。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的神经病理学》(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Life)中认为,成年人几乎不是自己行为的主人,他们经常(甚至一直)只是在响应深藏内心的想法和感受罢了。尽管弗洛伊德的这本书强调了家长应努力(通过精神分析)链接内心深处想法,从而理解自身行为的重要性,而当代的研究则开始以融合神经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方式来解读父母身份的种种行为。
在《爱的重要性:爱抚对婴儿大脑形成的影响》(Why Love Matters:How affection shapes a baby’s brain)一书中,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师苏·格哈特(Sue Gerhardt)强调了理解教养过程中神经生物学和心理学原理的重要性。这本书侧重于幼年经历如何既传授孩子知识,使他们社会化,同时也能(尤其是在出生后的头几个月)塑造他们的神经通路。她这本书的很多内容建立在大量“脑可塑性”(brian plasticity)研究基础之上。脑可塑性研究并不认为行为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认为支持和强化某些特定行为的神经通路具有可塑性和灵活性,可以作出相应的适应和改变。
无独有偶,以色列巴伊兰大学贡达多学科大脑研究中心(Gonda Multidisciplinary Brain Research Center)的露丝·费尔德曼(Ruth Feldman)也认为,幼年情绪体验铺设的神经通路有助于形成思维和行为的神经通路;这一现象涉及面积极广,所以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家长的教养方式总是回归他们自己幼年经历的那种方式。但费尔德曼和同事们也指出,人脑的可塑性和发生变化的能力意味着,早年形成的神经通路是可以被改变的—这正是第一章中依恋理论批评者的核心观点。
大脑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荷尔蒙的影响,但也并不总是如此,有研究表明大脑的改变也受到亲子互动、广义的社会和环境因素以及学习的影响。这可能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许多新手父母会回避采用他们童年接受的教养方式。大脑的可塑性也让无数家长体会过这样一种感觉—通常是养不止一个孩子的家长—随着生活的继续,你的家长身份认同会改变,你的教养方式和互动方式也会改变,这样才能面对孩子们不同的需求和不同的性格。
当然,家长们有各自不同的育儿理想。这些想法可能很多是受到自己童年的教养方式的影响,不过也可能是受到文学作品和媒体报道的影响,因为里面会明确传递各种教养方式的信息。伴侣关系也许会破裂,家庭状况随时都在改变,但父母是一生的角色。然而,此中暗含的一种观念是,成为何种父母对一个人有着持久的影响—对他们的教养方式有影响,对孩子未来的走向也有影响。所以说,家长有责任培养出健康快乐、适应环境的孩子;要是出了岔子—家长也容易被指责。
对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来说,成为父母如同一场危机,意味着太多的新要求,包括生理上的、情绪上的、心理上的,还有经济上的,比如要有更多的财务负担,可能还会给现在的亲密家庭、休闲时光以及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带来一丝不确定因素。除了极特殊情况,人们通常这样描述成为父母时内心的挣扎感:往往是一种强烈的失去自我的感觉,背后是互相竞争的个人、社会和文化的影响。
三、我可以全都要吗?
父母的互动和养育被认为有着深远的影响,甚至可能会奠定孩子未来的基础。各种新闻头条反映了—还有些人认为是新闻引起了—许多家长对孩子养育问题的关注。要不要送孩子去托儿所,要不要在家里做儿童保护措施,一个人带孩子会有什么后果,宝宝还小的时候就离开他们去上班会对他们的未来发展有什么影响,这些都是经过深度讨论的话题。
那么,平衡这么多责任意味着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既维持和谐持久的亲密家庭关系,又拥有稳定安全的财务独立,还能有一份满意的事业,同时能让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呢?家长该如何平衡这么多需求呢?对此,新手父母会有很多的问题和关切。第三章里,我们会考察已有的研究,看看不同家庭环境对孩子的交际和情绪发展有哪些影响。在这里,我们先来看看母亲在带孩子的同时去工作会有什么影响。
仔细读读研究资料就知道,把所有上班的女性归为一类,把所有家庭主妇归为另一类,根本没法涵盖所有女性和所有孩子的情况,更何况他们各自的生活环境也大相径庭。家长能够有机会决定自己的个人和家庭处境至关重要。在英国,家庭主妇的比例在过去二十年中下降了不止三分之一。也有很多女性选择在孕期工作,孩子出生不久后也会重返工作岗位。自1951年起,英国就业女性的数量翻了三倍多,而且最新数据显示,有68%的带孩子的女性仍在工作。这种家长人群中的人口学变化被媒体登上头条,意在强调一种潜在的危险—职业妇女的孩子更可能功课欠佳,不善社交,更容易发生吸毒和未成年性行为等不良行为。
的确,在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女性就业率逐步上升的国家开展的研究表明,母亲工作对孩子的学业表现和人际发展确实有潜在的负面影响。受约瑟夫·朗特里基金会(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委托,埃塞克斯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埃米施(John Ermisch)和马尔科·弗朗切斯科尼(Marco Francesconi)于2012年开展了一项研究,测算家长工作对孩子的影响。结合英国家庭状况调查(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tudy)的数据,他们发现,尽管全职工作女性可以增加家庭收入,但工作会限制她们和家庭互动的时间,还可能降低她们孩子未来的受教育程度。
这项研究表明,在孩子1岁~5岁期间,母亲长时间全职工作可能会降低孩子获得更高学历的机会,并会增加他们失业的风险,让他们更容易在刚成年的生活拮据,青年时期经历心理困扰的风险也会增强。而兼职工作的母亲对孩子长大成人似乎没什么负面影响。研究中,父亲参加工作的影响并没有母亲参加工作那么明显。孩子上学前父亲长时间工作与降低孩子未来失业的风险相关,也与降低他们成年早期生活拮据和青年时期经历心理困扰的风险相关。
总体来说,这份研究认为,抚养孩子的时候,父母上班对孩子的发展有负面影响。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其中的研究方法就会发现,数据中使用了大量很笼统的归类,比如只有兼职和全职中“父母是否有薪工作”和“父母陪伴时间”这种条目,却没有分析家庭生活中的种种复杂情形。比如家长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他们是不是自己选择去工作的,这些也都是值得考虑的内容。
1991年,美国国家儿童健康和发展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and Development)在美国境内开展了一项历时研究,考察女性就业与儿童发展结果的关系。这项由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珍妮·布鲁克斯—冈恩(Jeanne Brooks-Gunn)、韩文瑞(Wen-Jui Han)和简·沃尔德福格(Jane Waldfogel)实施的研究发现,女性在孩子3岁前参与全职工作,与孩子的行为问题显著相关,其行为问题包括攻击性行为和4岁半时的人际焦虑。1岁前母亲全职工作的孩子,比1岁前母亲兼职工作的孩子,更容易发展出破坏性的行为问题。在认知差异方面,1岁前母亲全职工作的孩子在认知测试中得分更低,而1岁前母亲兼职工作的孩子则没有这样的低分情况。
虽然女性就业与孩子的行为问题和发展结果有着种种负相关,布鲁克斯—冈恩和她的同事们却认为,女性就业未必对孩子的智力和人际发展有负面影响。她们把女性就业和其他影响因素(比如亲子互动、家庭收入和儿童看护)放在一起看,发展出了对女性就业与儿童发展关系更为细致的理解。她们发现,尽管女性在孩子年幼时工作存在消极的一面,但女性就业对大一点的孩子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复杂的。这同婴儿时期不一样,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女性就业对孩子发展不好,而更应该结合个人情况来权衡利弊。对很高比例的一部分女性来说,不断增加的财务安全让她们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儿童护理,有更多机会创造更多提高孩子生活质量的体验,同时惠及家里的其他子女。
2005年,新南威尔士大学为澳大利亚社会政策研究中心(Social Policy Research Centre)做的一项大规模研究发现,有工作的父母给他们新宝宝的居家团聚时间和照料—通常认为母亲出去工作的时候,这些就被牺牲了—实际上依旧保持在高位。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ARC)主席林恩·克雷格(Lyn Craig)教授研究了5岁以下孩子的父母并发现,相比牺牲照顾孩子的时间,有工作的母亲更倾向于牺牲自己做家务、放松和休息的时间,以此保证不工作时合家团聚的黄金时间(quality time)。为了留出和孩子(们)相处的时间,相比不工作的母亲,有工作的母亲会把更少的时间花在做家务、个人护理和独自休闲等方面。
这项研究也解释了职业女性是如何“倒时间”(time shift)的,她们重新安排家庭事务,从而有更多的时间和孩子待在一起。比如说,每天起早一些,出门上班前先和孩子多待一会儿;然后,每天睡晚一些。当然,对很多女性来说,上不上班没得选—但她们上班也有各种缘由。林恩·克雷格也承认,这些选择不多的女性往往过得都不太好。因为不得不去上班,所以把孩子留给别人照顾,这在情感上让她们难受。另外,很多母亲维持不起高质量的照料,而对于独自照顾孩子的母亲来说,情况更加难堪。对很大一部分女性来说,成为母亲的挑战不仅来自要平衡诸多责任,也源自她们不得不解决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困境,弄清楚到底哪些对孩子好,哪些对孩子不好。
对很多职业女性来说,拥有一份工作、一份事业对她们的幸福感、安全感和生活满意度是有积极作用的;而对其他很多女性来说情况正相反,工作不是选择也不是抱负,而是一种不得已的事情。林恩·克雷格认为,对于后者来说,她们为平衡工作和养孩子所面临的压力会比主动选择工作的职业女性更大。大量研究表明,父母的幸福水平是预测孩子发展结果的重要指标之一,而且孩子的情绪与人际发展是与父母的幸福、忧虑和压力相关的。许多心理学研究显示,父母的忧虑和压力可能会导致孩子面临人际和情绪问题的风险。
在《孩子什么都学:父母的压力是孩子的毒药》(Kids Pick Up on Everything:How Parental Stress Is Toxic to Kids)一书中,教牧咨询师戴维·科德(David Code)例举了大量心理学实验并提出,父母的压力水平会影响到孩子人际、情绪和认知的发展。尼克尔·塔尔格(Nicole Talge)和同事们于2007年开展的研究表明,如果一名孕妇在孕期感到压力,那么她的孩子更有可能面临潜在的情绪和认知问题,比如更有可能感到情绪焦虑,或在童年时期更有可能语言能力发育迟缓(第一章引用的文献中也提到过这一点)。
其中,母亲的压力荷尔蒙皮质醇(stress hormone cortisol)水平被认为是一个关键因素。总的来说,父母的压力比就业这单一项更可能影响孩子的发展。尽管这一章里,我们没有考察导致父母压力的决定性因素,但应该看到,父母会在许多方面感到压力,比如财务稳定、住房保障以及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因此我们也有必要考察一下形成父母生活经历的诸多因素。
生理因素对为人父母的影响毋庸置疑—最基本的有为了适应分娩而做出的生物学改变,再进一步也有为了方便建立亲子纽带而发生的神经学改变—但人类通过广泛学习来影响和塑造教养方式的能力也不可忽视。人们可以做选择,也确确实实在做选择。我们的研究结果并不把为人父母看作被生理属性和文化因素决定的一成不变的角色,父母有能力改变和调整他们的行为,创造出适应他们各自环境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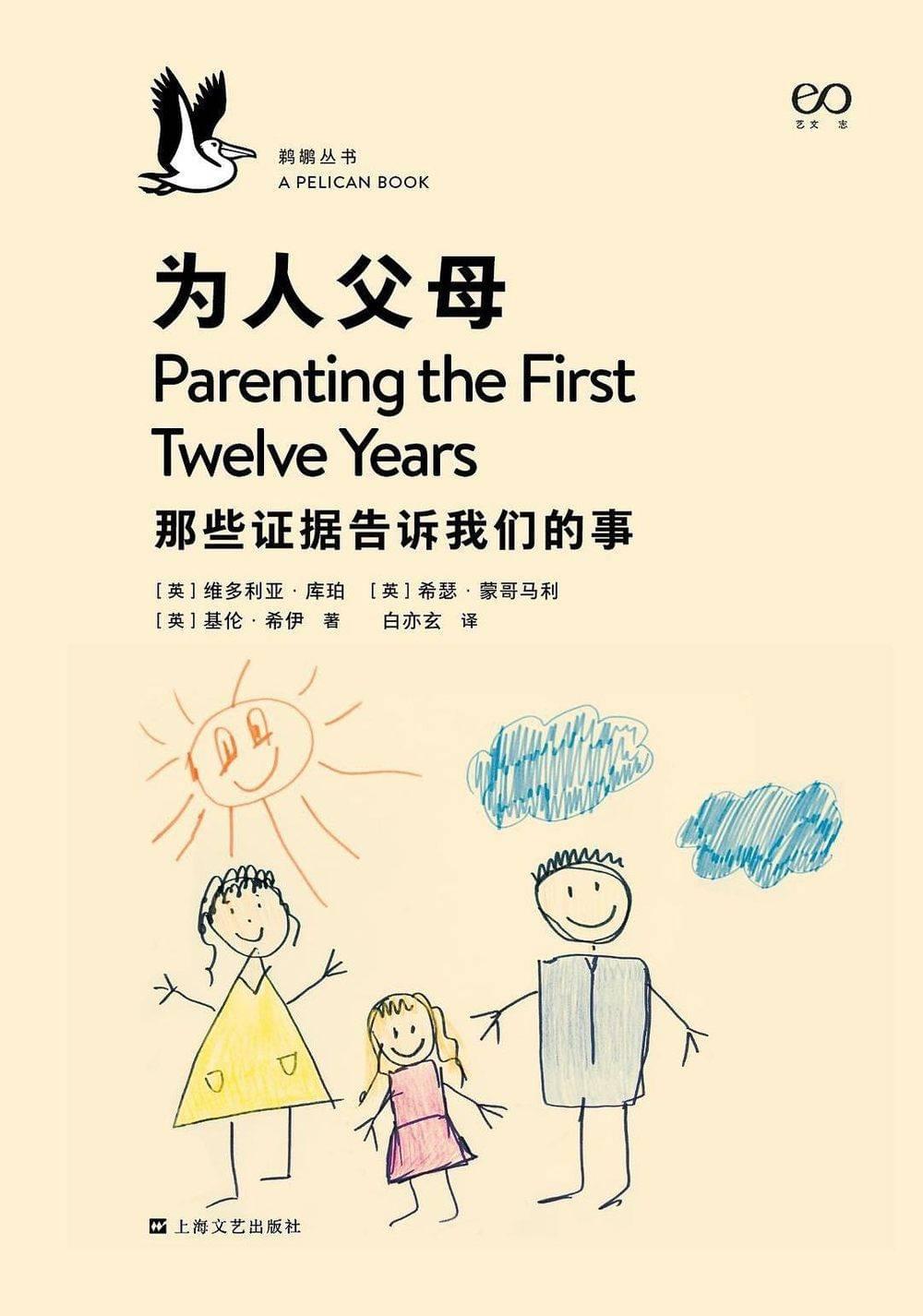
本文摘自图书《为人父母》第二章(由磨铁图书·大鱼读品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