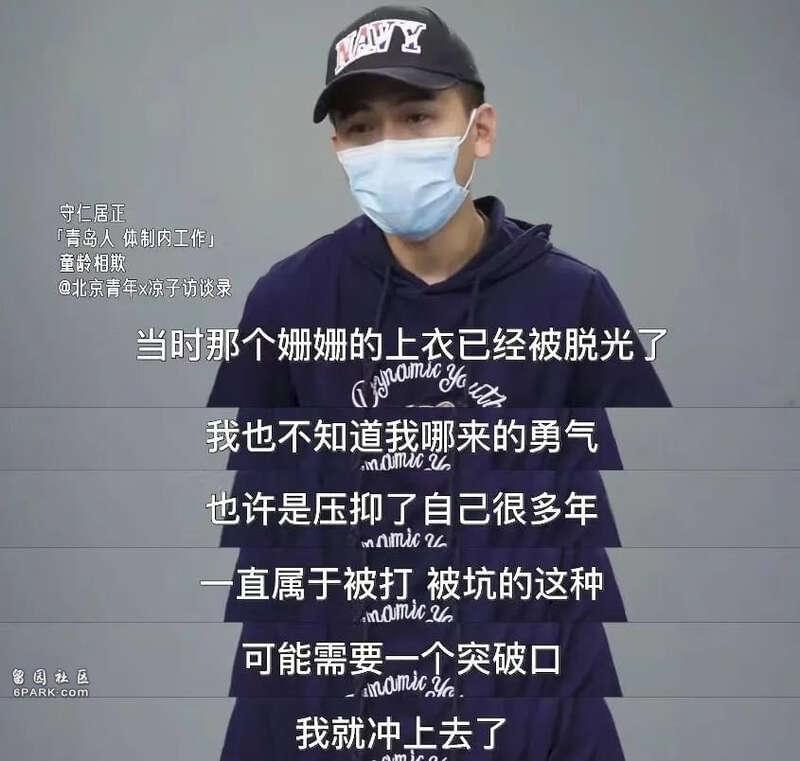
守仁居正的噩梦是从幼儿园开始的。
他记得园里有位女老师,人前人后有好多副面孔。她喜欢扇学生耳光,骂长得漂亮的女孩子是“婊子”,也会在小房间里解开外套,让学生摸她的胸部。
守仁居正不懂这样的区别对待意味着什么,只是越来越内向压抑,长年遭受校园霸凌也不敢反抗。直到那天,看到曾经的幼儿园男同学,像当初抚摸老师胸部一样性骚扰女同学时,他直接冲了出去……
一名校园霸凌的受害者、见证者、救助者,如何对抗隐秘的暴力?
以下是守仁居正的自述:
讲述者|守仁居正
会“变脸”的幼儿园老师
4岁之前我在农村老家生活,日子过得无拘无束。后来父母工作变动,我便跟着他们进了省城,进入了黑白电视里的那个“人间天堂”一样的世界。
城里的街道干净又宽阔,马路笔直,车来车往。我们住的院子也漂亮,房子建得整整齐齐,像昂首挺胸的士兵在等待首长检阅。因为工作繁忙,父母决定把我送进托儿所,他们说,那里的孩子大多都是体制内的子弟,个个听话懂事,老师也亲切友善。
我被宽宽大大、亮亮堂堂的城市迷住了,万万想不到那里就是我噩梦的开始。

我并不淘气,是很安静的那种孩子,之前在农村,每天就是吃饱饭、看看鸟、看看电视,从未和任何人发生过矛盾。可没想到,入学第一天我就挨了打。
那天,同学黑娃可能因为想妈妈,一直在哭,怎么哄都哄不好。我坐在他旁边,受他的情绪感染也开始哭。我们俩旁若无人,越哭越凶,然后突然听到“啪啪啪啪”四声,脸颊就开始火辣辣的疼。
我被打懵了,一抬头,看见一位身材高挑、特别漂亮的女老师,正恶狠狠地瞪着我们。她说,“再哭的话中午就不要吃饭了!”大概是被这句话吓住了,我俩瞬间收了声,眼泪也奇迹般地憋了回去。
很快,像要躲着谁似的,老师领着我们两个人到了洗漱间,把我们脸上的泪痕都洗干净,还涂了郁美净之类的香香。我记得那双手很温暖,又长又细又白。我盯着他一言不发,想不明白,这样的一双手,打起人来怎么那么疼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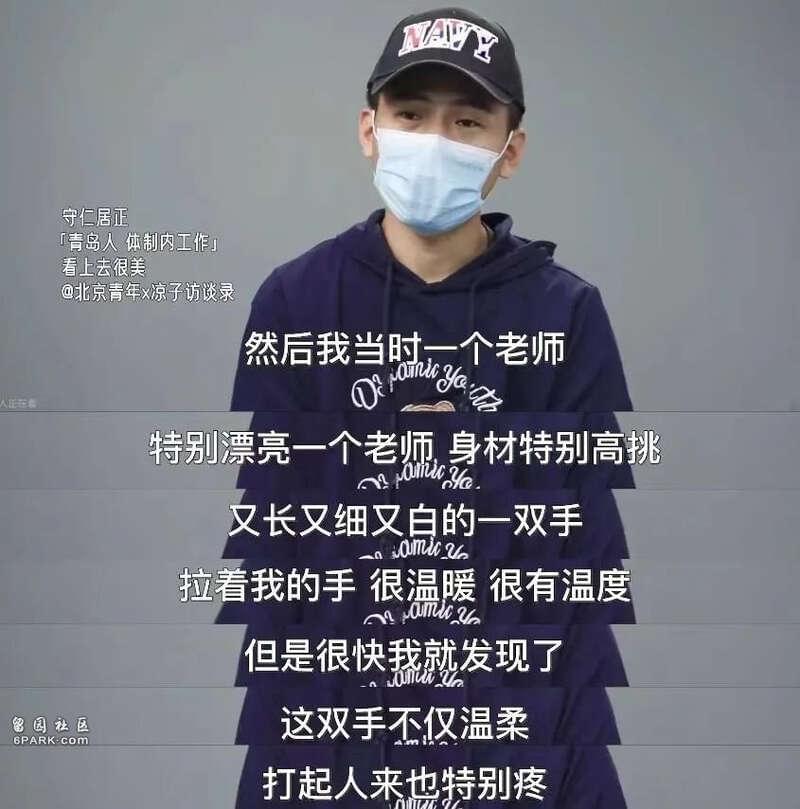
后来我越来越发现,那位漂亮的女老师可真是奇怪,她好像会变脸似的,一会儿一个面孔。
她经常会对女生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说某某女生长得丑,像《动物世界》里的狮子或者大猩猩一样。如果是长得好看的女生,老师的话就会更难听,说她们是“万人骑的小骚货,长大也是个婊子,长那么好看给谁看”,然后“啪啪啪啪”又是几巴掌。
那时候年纪小,老师说的很多话我其实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只记得女孩子们的泪水,和教室里的哄堂大笑。
可对待某些同学,老师又会表现得格外“温柔”“包容”。
那天,我抱着床单去水池,无意间瞥见了屋子里有一大一小个人,是那位“温柔”的女老师和我的同学于童。
我看见,老师把外套给解开,让于童用手触摸她的乳房。于童不敢,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她就把他紧紧抱在怀里,握着他的手往自己胸上放……
我当时惊呆了,完全搞不清楚这是什么状况。只是觉得这小子的待遇真好啊,我们不听话,老师只会赏我们几个耳光,可是不管是尿床还是不听话,于童好像真的从来没有挨过打,还得到了老师这样的“安慰”。
那时候,我绝对想不到,老师的这个举动已经埋下祸根,影响了几个孩子此后的命运。
当受害者成为加害人
因为在幼儿园里长期受到老师的“严格管理”,父母也不在身边,我性格越来越内向,见到生人不敢说话,受了委屈也不敢表达。
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小区里,我这样的闷葫芦,慢慢就成了同龄人可以随意霸凌的对象。很多打人的孩子就是我曾经的幼儿园同学,打人的方式基本是扇嘴巴子,眼神、脏话像是一个模子加工生产出来的——都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这是他们最熟悉的压制别人的方式。

这些委屈我都没跟父母说过,说了有什么用呢?在大人眼里,这都不是什么大事,一起喝个酒,黑不提百不提就结束了。更何况,我们的父母都是一个系统里的,涉及到上下级问题,有些话更不好对外说了,说不定还被认为是我自己惹是生非,额外再领一顿父母的混合双打。
日子就这么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挨打,忍着,挨打,忍着。我从不告诉任何人自己受的委屈,也没心思关心周围人的处境,直到于童又出现在我的生活中。
初中时,我和于童又成为了校友,没什么交集,只是经常听说他的风云事迹——开学没几天,他就凭借拳头成为了初一年组的“一哥”,整日骑着辆没有牌照的三轮摩托,带着他的小跟班在学校里面横冲直撞,没人敢管。
那时候我们班上还有我的另一位幼儿园同学,叫姗姗,是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女孩。有一次早自习,我发现她坐在座位上哭,不知怎么立刻联想到早上进校门的时候,于童撞了她一下,还拽了她的书包带子。后来我悄悄问姗姗是不是于童欺负她了。她什么都没说,趁着身边没人快速把领口拉低了给我看了一眼,有很多红色的抓痕。
我问是不是于童干的,她点点头,又开始沉默地流眼泪。
直觉告诉我,于童晚上肯定还要再欺负姗姗,放学后就悄悄跟在她后面。没想到刚到胡同口,姗姗就被于童和他的三五个小跟班直接拖进胡同里去了。我躲在墙壁后悄悄看,我姗姗的上衣已经被脱光,于童跟他的同伴,竟然在用小时候幼儿园老师教他的那个手法在摸姗姗的胸部!
姗姗痛苦不堪,一直在挣扎躲避,大概是被狠狠地捏了一下胸部,她发出了特别痛苦的叫声。

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可能是多年来被打骂、欺侮的情绪需要一个出口,我脑袋一热,直接冲了出去跟于童扭打在一起。他的跟班从地上捡起一块板砖砸在了我头上,血像没有拧紧的水龙头,从额头上顺着我的鼻梁开始往下滴。
大概是被血吓住了,于童和他的手下都停了下来,冲着我扔了一句狠话:“明天我活埋你”,然后就跑了。姗姗坐在地上,双手护着胸前,一直在发抖,有个好心的阿姨路过给她披上衣服后,她才开始沉默地整理仪表,一边擦眼泪一边往家里走。
我脑袋也一片空白。血顺着我额头一直滴,流到嘴边,舔一下是咸的。我觉得自己的生命也快走到尽头了,身心反而有一种特别轻松的感觉——
这么多年,我挨过很多次打,但这次不是因为自己怂,而是为了保护别人受了伤。我觉得自己值了!如果我死了的话我就是英雄。
挨打的第二天,我抱着必死的心情去上学,甚至写了一封遗书带在身上。我在等待于童的报复。
就那样惶恐地过了半个月之后,我忽然得到了一个消息:于童死了。
听说,于童喝完酒骑着跨子在公路上超车,跟其他的车发生了刮蹭,三轮摩托发生了翻滚,被后面过来的车辆直接碾压,昏迷好多天后不治身亡。
那一瞬间,我确实有种庆幸的感觉,庆幸我没有死,没有被人活埋。他消失这些天里,我常常以为他会像职业杀手一样躲在暗处伺机把我绑走,我从此就杳无音讯了,我的父母可能永远都不知道我去哪了。

可是随着年纪增长,我越来越觉得,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
姗姗越来越沉默,甚至还会故意躲着我,好像只要看到我,就会永远被困在那个胡同里。也没有任何人为她那天的遭遇讨回公道,在我们父母所处的那个生态系统里,除了公平正义,还有其他不得不遵守的规则。
后来,姗姗跟着家人去了国外,成了带发修行的居士,始终是单身。
于童永远地离开了。随着年龄增长,我对他的态度,也由愤怒、不屑慢慢转变为了可怜。他的确做错了很多事情,可他是如何变成那样的呢?
从小到大,他可能只是别人眼里的一个工具,下边的人为了讨好他的父亲,一直在无底线地纵容他。在最该接受教育的时间里,他没有树立起是非观,把打架、逃课、飙车、欺侮女性视为寻常事。
作为霸凌者,他毁了姗姗的一生。可他自己,又何尝不是畸形成长环境的受害者?
我越来越觉得,在隐秘的角落里,校园霸凌者和被霸凌者同样需要得到拯救。
噩梦重现
带着那些内心的创伤,我努力地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我今年36岁,考上了军校,读了双博士,还因为表现优异被一路提拔进京。我拥有了温柔的妻子、可爱的儿子,生活得安全体面。
但那些记忆并没有消失,它像一根刺,深深扎在我心里,并影响着我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直到现在,遇到事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自己先去忍,而不是寻求解决方式。我一直在试图去掰正这种影响,但是掰正第一反应太难了,我需要一生去摆脱校园霸凌的阴影。

更让我绝望的是,我经历过的痛苦,居然再次发生在我的儿子身上。
那天,有位母亲在幼儿园的家长群里问,有没有发现孩子在家有些怪异举动,她怀疑孩子可能在幼儿园里被打了。我立刻和儿子视频通话,没想到他不仅确认了这个说法,还模仿了老师打人的动作和手势。
我找其他家长去核实这个事情,孩子们一开始都不说实话,后来被家长用纸杯蛋糕引导才承认,确实被老师打过,而且所有孩子说出的被打情形几乎一模一样。
我后背发凉,根本不敢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北京的幼儿园里。我受过这样的苦,绝不允许我的儿子再深受其害。
我和其他家长一起去找园长,对方态度不明,先是保证绝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又请求给他一点时间内部调查,后来又直接报了警。可是老师打孩子不会那么重,身体上的痕迹找不到,心灵上的伤害无法衡量,取证艰难,警方调查了三周,迟迟没有明确结论。
家长们对监控不抱希望,也不愿意花费那么高的时间成本,很多人带孩子转园后也就不再参与维权之事了。甚至有些人觉得我们这些坚持要说法的家长是在无理取闹。在他们看来,每个人都有情绪好和情绪不好的时候,孩子淘气的时候上去给两巴掌踢两脚是很正常的,没有不打孩子的老师。
小时候的无力感再度袭来。三十年前,面对校园霸凌,我不敢反抗;三十年后,相似的事情在我儿子身上重演,我依然找不到最优解。
我承认大环境已经有了很多改善,一旦出现相关问题,警方、教委都会及时介入,这是建立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血泪上的进步。可是,受制于维权成本、社会文化,还是有很多父母把校园霸凌看作简单的“磕磕碰碰”,还是有很多人把维权视为“小题大做”,这让我怎么能不痛心,怎么能安心?
9月,又有一批小朋友,要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走进幼儿园里。这是北京最美的季节,阳光灿烂,微风拂面。我真心希望,孩子们能永远生活在阳光下,健康快乐地长大。
我也想告诉家长们,不要只是想着拼命给孩子提供好的物质条件,拼命托关系把他们塞进所谓“好”的幼儿园,更要多听听、多观察孩子的状态,做孩子们可以信赖、求助的对象。不要让孩子因为求助无门而成为受害者,也不要因为教育缺位而让孩子沦为加害人。
治理校园霸凌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家庭应该成为这堵防护墙的第一块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