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出去旅游,
而是找个清静的寺庙住几天,
在年轻人中悄悄变得流行起来。
江西庐山风景区里的诺那塔院,
20年来一直做公益的禅修营,
最近一年来,
它每个月的报名通道被挤爆,
众多95后,00后组团前往。

▲
在山间郊游,拜访邻人

▲
氛围轻松自在
8月中旬,一条采访了6位参加禅学营的年轻人,
有将将毕业的大学生、刚回国的海归、
被行业寒冬“憋住”的打工人们……
他们因失恋、焦虑或职业困惑上山,
或者只是寻求一次短暂的休憩,
歇好了,再重新下山面对生活。


▲
山顶的白塔

▲
寺内松月斋和大殿
炎热的三伏天,庐山上最高气温也才28度,一出索道仓门,就扑来凉爽的山风。车子往里走,到达满是红房子的牯岭镇,诺那塔院就落在最高处的山尖尖上。
上千级白色的台阶,将如织的游人和山顶的寺院隔开,松柏在院里投下墨色的阴凉,60个年轻人在这里开始了5天禅修。

▲
“出坡”,包括扫地、倒垃圾、给花瓶换水等

▲
凌晨6点打坐
内观、干活和闲谈,是在塔院主要的三件事。
清晨从“打坐”开始。6点,先“跑香”,大家甩开胳膊快速绕行,15分后身子热了,迅速折返回垫子上,静默,盘腿,正背,瞑目,数呼吸,一动不动45分钟。
7点早饭,全程是安静的,之后是“出坡”,扫地、倒很沉的垃圾、洗几百个碗……午休有3个小时,下午有佛学课,晚间“普茶夜话”,大家围坐,在小纸条上写下自己的问题,跟同伴们热腾腾讨论。
塔院的禅修营是公益性的,面向普通大众。从2001年开始,办了20多年,它要求严格,时间安排地很满,但就是不断有年轻人涌上来。
这期的报名通道只开放了10个小时,立马收到400份报名表,因为住宿房间不够,到顶只能容纳50人左右。

▲
塔院“团宠”小黑

▲
休息时,大家会玩捡石子游戏、打羽毛球

▲
一位学员请师父给自己剪掉3年的长发
准备捐给武汉儿童癌症中心
各人上山的目的不同。这拨主要是95后,有一线城市白领,卷累了,请了15天的年假过来,“旅游也很累的,山上让我睡得好。”一位程序员趁着跳槽的空档上山,5天待完了不想走,留下来再做5天义工。
不少00后学生利用暑假来,还有人是因为失恋、抑郁、职业焦虑,单靠自身无法走出痛苦,强制性地换个环境。

▲
大家喜欢与师父闲聊

▲
结伴上山顶看日落
在塔院,不分男女老幼,都互称“师兄”,去掉了社会性的标签,很容易进入到一种纯粹的交心状态。
师父们都很年轻,好几位是90后,笑起来很灿烂,平时也刷B站,听罗翔和许倬云的课,懂流行梗,学员有什么困惑,他们往往立马能抓住那个点。
远离手机、KPI和考试。晚饭后,三三两两的年轻人,穿着素色的衣服,围坐轻谈,有人打羽毛球,摸摸狗狗小黑的肚子,或者只是倚在台阶上听高高的风铃声。
这样待几天后,人会变得沉静,“好像感官被放大了,在山上你会觉得周围很鲜亮,树特别绿,云很白,蝉鸣很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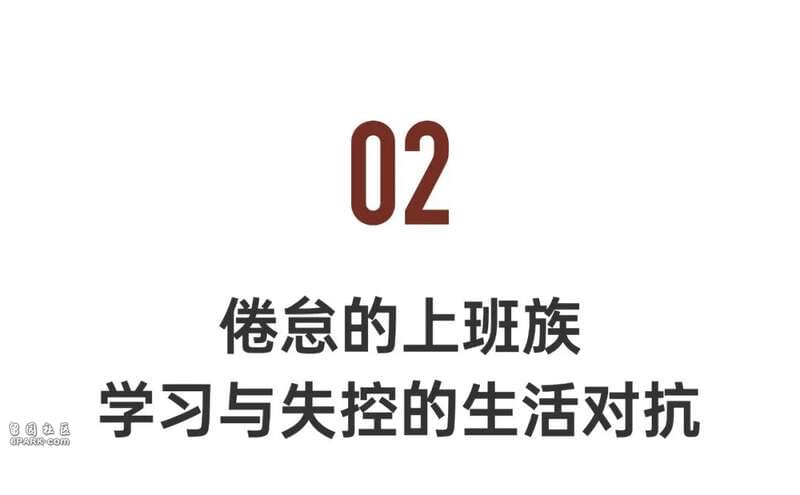

Violet,32岁,互联网公司运营
1年前开始来塔院
Violet在一家头部互联网公司工作,强度高,常常需要加班到夜里10点,她是高敏感型人格,“老板骂同事,我都会跟着冒汗的那种。”
此前,她在上一段感情里遭遇了严重的PUA,对方很博学,“他会告诉我很多负面的,尤其会跟我说父母不爱我,把我身边所有的关系都隔离开后,我就只能围着他一个人去转。”
虽然已经分手一年多,影响依然存在,她深陷孤独,对周围人抱有强烈的紧张感,自己常常莫名其妙地哭。
正好那段时间对冥想感兴趣,这块跟禅修很像,五一期间就报名来庐山。

▲
Violet在去年5、6月份上山,碰上吃粽子和郊游

▲
行走在大山间让人心情舒畅
前3天只当是来旅游,心态有些浮,直到她生了一场病。
5月份山上还很凉,她肠胃不太好,闹肚子,同伴们围过来,其中一位是学中医的,Violet第一次喝到那种真正熬出来的藿香正气水。
“好奇妙,这些人你跟他无缘无故,也没有任何利益往来,他们就这样无微不至地照顾你,你就好像得到了人生一直在追求那种Unconditional Love(无条件的爱)。”
她延长了假期,待了8天,后面几天人比较少,她一有空就拉着师父“辩论”——人性本善还是本恶,人单纯为了自己活是否可以,父母重男轻女怎么办……
也不见得次次被说服,但最关键的是关于重新发现“善”这件事,她试着代入一种更为温和的视角,去看待自己与父母、同事的关系。

▲
今年4月,与朋友们在公园聚餐
下山后,她能明显感觉到自己心态变了,但“疗效”只维持了1个礼拜,她赶紧又在端午节回来。3天假期被用到极致,“我当时很疯的,夜里9点北京坐卧铺出发,第二天6点到庐山,同样的方法睡回北京,这样3个完整的白天可以在山上。”
在工作上跟同事出现摩擦,搁从前她会很容易生气,现在平和很多。她希望自己的工作更能涉及到帮助他人,于是申请了内部调岗。
今年6月,她开始有了跑步的习惯,形容这一年自己的变化,她用了一个比喻,“到现在,好像能听到自己骨骼生长的咯吱的声音。”


佳莹,22岁,应届毕业生
2个月前开始来塔院
佳莹今年刚大学毕业,6月初从辽宁盘锦坐了21个小时的绿皮硬座到庐山,7天后赶回老家参加国企考试,之后立马又坐了一趟绿皮车过来。
屁股都坐疼了,这样来回三趟,她陆陆续续在塔院待了2个多月。
上山前,她刚被分手,对方不给理由,“我就想不通,前一天他还说老爱我了,怎么第二天死活就不处(对象)了,就接受不了。”她陷入巨大的自我怀疑,什么事都做不了,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到塔院是为了静静心,谁料第二天,她就在朋友圈看到前男友和新女友的合照,突然就崩溃了,顺着对面的山坡,一路哭上去。

▲
佳莹总在忙活
5天的禅修,全是功课,很多人坚持不下来,这反而很适合佳莹,她故意一头扎进重复性的劳作里,让身体疲乏到极致,来不及思考。
实在没活干了,就拉着人狂聊天,佳莹同一个宿舍的人,有人社恐,有人与父母有矛盾,有的是婚姻问题,大家凑一起,很容易就能共情。

▲
在塔院喜欢上书法
她渐渐感觉到自己的情绪被接纳,不过对前任的怨恨依然消解不了,“那我就问师父,那个男的劈腿,他会遭报应吗?师父说不一定,可能他会过得很好,因为从另一个角度,他客观上帮了我一些忙,假如不是这次失恋,我也不会上山,认识这么多好朋友。这么想,好像也有点道理。”
7天之后,她下山,再也没哭过。回到家里,心情舒畅,干活儿利索很多,工作也顺利找到了。二姨看到这么明显的变化,还让她下次带着表妹一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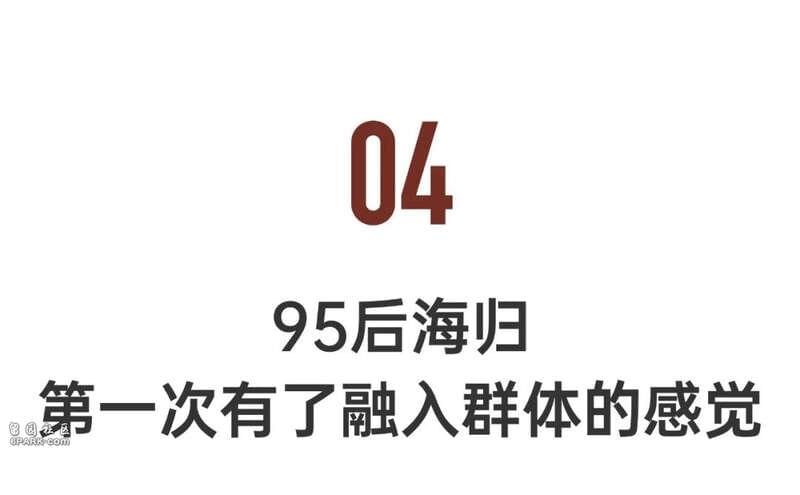

小崔,24岁,民宿创业者
1年前开始来塔院
小崔15岁就去了加拿大,在那儿生活和学习了8年,2020年他回到老家珠海。最初来塔院,只是为了调整自己不健康的“北美”作息。
他学的酒店管理专业,去加拿大工作是顺理成章的,那边节奏舒缓,熟门熟路。在塔院待了3个星期之后,彻底推翻了之前的规划,他决定留在国内,创业做民宿。

▲
小崔每次来,都会减掉10斤体重
他形容此前的自己,一直有种Outsider(局外人)的感觉,“在国外我都一直是独自生活的,回来后碰到的同龄人,要么是比较卷,要么以短期利益为主,很难有深度的交流。”
师父们擅谈生死和选择,这里类似一个大型哲学和心理学交流场,大家很容易就敞开心扉,小崔立马有一种融入感。

▲
小崔为大家演奏萨克斯
谈及到被吸引,都是很微小的,“我们吃午饭,有个同伴的米饭掉地上了,他捡起来把它吃掉了,我就觉得你怎么能做到这个样子。我就跟他说我做不到,我好佩服你,他就说’米也只是米呀’,那一瞬间我就很受触动。”
后来陆续在塔院待了3个月的时间,遇到了很多观念相像的人,有的虽然只认识一两天,在山下也成为了好朋友。“我开车全国到处跑嘛,每逛一圈,能见十几个,大家认识的时候没什么功利心,我打个电话,他就开车带我去吃饭。”
原本他对待工作,只是想着投资回报率和运营策略,现在除了想要挣钱之外,他还想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最好能把民宿做出来像塔院这样的氛围。
他想学更多,即将进入香港理工大学读研究生,“这很难的,但哪怕你是一粒尘,带来的能量很小,你有在传达一些东西,你的世界在变好,整个世界也在变好。”


英子,31岁,旅游博主
3年前开始来塔院
英子是一位旅游博主,自己创业,经营各平台的账号,每天深夜推送文章,精神压力大,体重蹭蹭蹭往上跑。
3年前她因为工作拍摄第一次来塔院禅修,下山之后,疫情爆发,旅游业首当其冲,她一下子就懵了。

▲
英子第一次上山是在冬天

▲
即便大雪纷飞,也需要按照日程“出坡”
大局势无能为力,能着手的只有微处,她回想起山上的生活,“虽然是冬天,每天5:00起床,我会觉得白天特别长,那种感觉特别好。”
她想留住这种感觉,于是自己在家,也开始每天早晨4:30起床,夜里9点入睡。这种对自我生活节奏的掌控,让她得以对抗疫情带来的焦虑,稳住心态。
半年后,疫情得到控制,她的工作也恢复正常,还成功瘦掉了20斤。

▲
英子喜欢喝茶,常常带了茶具来塔院
她想攒钱,但总是苦于大手大脚,赚10块钱能花9块,甚至花11块,她在微信上跟师父聊天,“师父就说因为我念力不足,也就是想做成某个事情的志向和信念不足,才没有动力。”
她细细思考,这辈子最想做到的事情,是给老家建一座乡村图书馆。那之后就给自己立个规矩,为了这个目标,每天存28块钱,渐渐也能攒住了。
在山上她学到的,并不是闲云野鹤,而是讲究善意、自律和表率,“能做到这些还蛮难的,绝对不是摆烂。”
这次她上山,还带了丈夫和几位朋友一起,认识了几位新朋友,约好之后一起去家里聚聚。


聪聪,34岁,高校教师
7年前开始来塔院
聪聪来自高考大省山东,本科在中央音乐学院,研究生在北京电影学院,都是艺术类里的TOP级高校。
第一次上山禅修,是在2015年刚毕业的时候,感觉不错,不过很快就被回北京上班的紧张感冲散了。
她学的是制片管理,从2016年开始,影视行业的寒冬就有了端倪,无论她怎么加班加点,项目都很难推进下去。
她有做事的野心,也有一些人脉,索性自己创业,跟人合伙做线下的儿童戏剧教育,2年赔进去不少精力,迎头撞上2020年疫情,憋在家里,她无计可施。
“有一段时间会不甘心,我觉得自己办事也靠谱,也不是没有能力,可是碰上整个行业和大环境是这样,工作上总是不顺”,有时候她遇到的一些人,可能连说话都不太利索,但是好像又混的挺好的,那种不甘的想法常常会冒出来。
上山吧,换个环境,好好梳理一下自己这些年到底怎么了。

▲
聪聪与同伴们一起在湖边歇脚
在塔院,她遇到久违的师父们,烦心事一股脑地倾倒出来,师父开解她“是做事的机缘还没有到”,但建议首先要保证生活的基础,有了稳定的收入后,再等做事的机会。
她觉得有道理,听进去了,考了高校教师资格证,受聘于一所大专院校当讲师,闲时上山帮帮忙,只是没想到一待就是这么久。
学校里每学期4个月的课程,被她压缩到2个月进行。如今她有8个月的时间在山上,管理着每月3次、每次60人的禅修营,大到日程安排,小到提醒学员山上有野猪,以及跑去问民宿老板娘借冰激凌蛋卷皮。

▲
打羽毛球、和学员们聊天

▲
空下来了就备课
临近9月份开学,还得紧锣密鼓看书备课,她对自己要求严格,“别人来塔院是想着放松的,我比山下还累,同时干两份工,两份还都得干好。”
有大学同学成功定居北京的,经历结婚、生子、买房、还贷款,大家道路不同,偶尔互相点个赞。有一次,她在朋友圈发了塔院清晨的云海,那位同学看到了,特地给她发私信“我好羡慕你现在的生活”。
大约在半年前,那种“不甘”的情绪消失地差不多了,“这么多人在这吃喝拉撒,跟你管剧组是很像的,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能力在变强。”
她还在等项目,只不过现在变得更有耐心了。
这期禅修营的最后一天,学员离开的差不多了,聪聪稍微能松下来。
这天是农历十八,月色如水,聪聪邀了同伴,一起爬上山坡,月亮缺了一些,像一枚高悬的鹅黄色毛玻璃石,映照着远处蜿蜒的江流,泛着盈盈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