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空总是很晴朗,上海最宜人的时节已经到来。照片中蓝色的部分格外突出,蓝色似乎不再是令人平静、心情舒畅的颜色,它让人直接联想到的是防护服、口罩和塑料。而如今出现在上海的蓝色更多的是路标、指示牌、禁止机动车通过的告示牌与遮阳棚,以及那些将街道包围起来绵延数百米的蓝色围挡。
迪耶·萨迪奇在《城市的语言》中写道:“城市街道远不止是一种基础设施投资。是街道在支撑着一座城市的居民,使他们能够在任何时间、以自愿选择的任何出行方式在自己的城市里移动。”如今铁皮包住了街道。不只是上海,疫情下各个城市的“围挡”都在以各种形式增加。当一座城市被处处围挡,与其一起消失的又新增的到底是什么?







上海城市里的蓝色围挡©️朱润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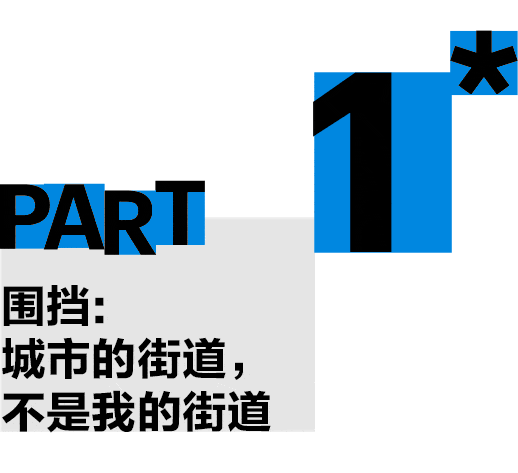
照片里上海弄堂区的围栏几乎跟街道一样长,弄堂街景被罩在铁皮里,完全没有行人,不能行走。恐怕不会有人比上海朋友更能赞同丹麦城市设计师扬·盖尔在《人性化的城市》中提出的观点了:“人是为行走而生的。在人群中行走的过程中,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逐渐展开......在城市里,步行的意义远不止如此;人们和周边的社区之间产生直接的联系——新鲜的空气、户外的运动、自由的生活乐趣,也获得经验和信息。”城市需要人在行走中创造出的“使用感”,一种烟火气 。
4月7日,在浦西一间50平米的屋子里封了7天后,摄影师朱润资第一次出门。当他骑着电动车在江苏路、延安西路上驶过时,街道静极了,能听到鸟叫,从很远的地方传来。这时距离上海全市封城过去了一周,马路上只剩下了单行线。他说他感觉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自由和辽阔。因为部分道路封闭,无法正常骑行,索性扔掉导航,随意穿梭。
在封闭下上海很多人无法获取日常所需的药品,朱润资所在的小区老年人居多,对用药有着巨大的需求。于是他报名成为一名配药志愿者,在小区老人配药的途中,得以有机会拍下这些照片。一周有一两天,他都会提着20包药从医院到小区,按居民需要的挨个将药分给焦虑的老年人们。其中大多数是胰岛素、降压药和艾斯挫伦片(一种缓解失眠问题的处方药)。
自由会在某个路口被突然打断,警察在几乎每个主要路口都要求出示核酸证明和通行证。最初是大小路口,过了几天,他们会干脆封锁小路,在大路口设卡,到了最近,似乎有了放宽,变成了区界。









上海城市里各种形态的围挡©️朱润资
刚封城的那几天,秩序尚未完全建立,管理者用各种物件来做围挡。比如横七竖八摆在路中央的共享单车,那些混乱排列的单车确实成功阻拦了一些车。这可能暗合了我们的某种惯性思维,我们不需要知道它是什么,只要发现眼前的这条路降低了效率,绕道而行便是。
围挡还包括椅子、伞,市政公司作业告示牌,以及放在一起的马路隔离栏和停车锥。一周后,这些临时拿来充数的围挡物都变成了蓝色白色,嵌了层假草的铁皮围栏。有的地方会沿着小区外围围一圈,但有的地方,只需要门口放三块铁皮,能起到同样的作用。在小区出入口,外卖货架、椅子也变成了门。那些日常的东西被赋予了封闭的功能。













被以各种形式围挡的社区出入口©️朱润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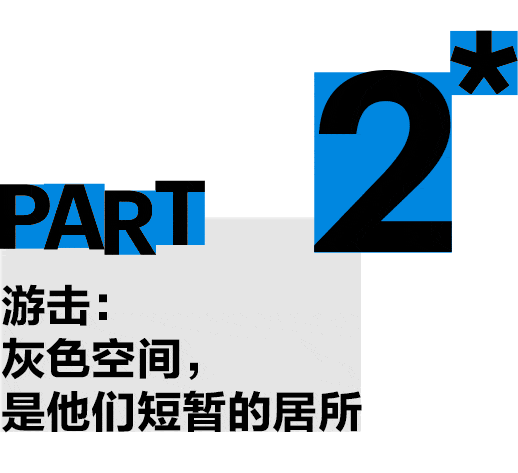
4月初,一家上海本地媒体发了一段视频,视频里外卖员为了保证物资供应,回不了家,只能就地睡下。一个为他们提供的,有天花板,有插座可以保证电力,适宜居住的地方?在上海还有几处呢?
视频中的暂时居住地原本是一间咖啡店,因建在桥洞下,所以被叫做桥下咖啡。疫情之前,咖啡馆吸引的大都是周围社区的居民和一些摩托车爱好者。封城前一天,老板锁店,特意留了盏灯没关希望给予城市一些希望。于是咖啡馆成了流浪者们的落脚点,10多米的连廊上人挨着人。连过道都被用来停电动车。
新闻播出后第三天,朱润资路过桥下咖啡的桥洞,翻过一圈绿围栏,在里面只见到三个人。侧躺在地上的男人说,他们也要走了,这里不允许住人了。



居住在桥下咖啡的人©️朱润资








居住在城市桥下空间的人©️朱润资
“你必须把自己想象成他们,如果我是他们我会搬去哪儿?”朱润资开始追踪上海流浪者们的踪迹,沿着四号线骑电动车——4号线北部是内环附近唯一一段地上城铁。四号线桥下有支起野外帐篷的流浪者,沿街商铺前的脚手架中亦有。脚手架内并不安全,但便于隐匿不被发现,同时也方便从营业的商铺那里借一点电的外卖员,于是似乎成了不错的暂居地。
沿着吴淞江找,在河与街道交汇的桥下,在南北高架路桥下,高架上的车辆减少,正因此,寄住在这里的人们不必忍受车辆造成的轰鸣声。这里几乎没什么声音,不必忧心忡忡被暴露。人们临苏州河支起帐篷,同一片儿有的帐篷在宽阔平台,有的占据楼梯拐弯处,帐篷远没有他们面前的电动车排得整齐,人们洗过的衣服挂在墙边,任风干。





居住在建筑脚手架内的人©️朱润资
这种追踪很快变成了游击战,一两天后路过同样的地方,流浪者们就不见了,人去帐篷没,只留下一地垃圾。这场游击战也愈发考验经验和智慧,起初,朱润资沿着马路驶过,便能偶遇他们。而现在,桥洞下被围挡的小路越来越多。沿着流动者的路线,他发现了很多不被外界注意的“灰色空间”,在正常的上海,这些流动者是很难留下踪迹的。
而现在,到处都是他们短暂生活过的痕迹:墙角拼凑在一起的纸板,小区门口连廊的垃圾,被丢在地上的棉被床单。“我一直在看这些状况在如何演变着。每天看着一个前一天还干干净净的(地方),突然全是人,然后突然又全是垃圾,人也没了。”朱润资说。



上海城市里依旧存在的“棚户区”©️朱润资
热气建筑的建筑师袁烨至今最后一次出门是4月1日前,面对城市灰色的占用她说:“这可能是一个契机,我们熟悉的空间被重新使用,城市空间会有一种临时的松动,不必一直在一种墨守成规的规则下,一板一眼。上海也许可以不要那么‘洁癖’,可以有一些机会与想象力。”
她认为,全球每个城市里都能展现这样自下而上的”空间游击”,不仅仅是特殊时期和底层人群,在日常的生活中民众也会自下而上地根据自身的欲望、身体的感知去适应这些空间。这种非正规性、临时性的特征是否有可能成为都市未来生活的一个议题呢?

5月以来,随着上海疫情的好转,街道上的人慢慢多了起来。先是穿梭在街上的外卖员,再是载着集装箱的运输车、私家车。冷清、凋敝的气息在慢慢散去。偶然看到的,堆放在小区门口,等待被清理白色泡沫箱依旧暗示着城市管理的停滞——这些泡沫箱成为政府发放物资以及团购的主要包装形式。在我们的印象中,一个有序运转的城市是不会积压垃圾的。当街道不再走人,它们被新的规则征用。












城市中随处可见的被遗弃的装物资的白色泡沫箱,该系列被摄影师命名为“White-OFF”©️朱润资
几个小区的泡沫箱有时候会放在一起等卡车拉走,有的隔天就从小区门口消失无踪了,有的堆积从几平米增加到了20、30平米。照片里的泡沫箱几乎一模一样,它们出现在不同的街区,只是背景在更换。
5月20日,朱润资无意间路过一处泡沫箱处理厂。那是一处废弃停车场——又是停车场,它已经成了被征用的主力。一个400米的操场那样大的空地,堆满了白色泡沫箱,差不多一人高。压缩机像灌水泥一样的轰响将目光引向压缩机前穿白色防护服的男人。从同济医院回来的路上,突然下起了大雨,朱润资在寻找桥洞避雨时发现了一处近百米的泡沫堆积点,这也是这一个月他发现的最大的泡沫堆积处,三名身穿大白的人员也在做着运输清理工作。





停车场、街道失去了原有属性,成为泡沫箱的堆放点©️朱润资
围挡外是更接近于“野蛮生长‘的状态,流浪的动物在街道上睡觉,公共空间杂草生长。此前网上流传的一张外滩生草的照片被大众热议,当砖缝里露出新芽,商铺台阶前生出绿草,我们却感应不到生机勃勃,无法为之惊喜。相反,我们从中看到的是萧条,是默默流走的时间,是不再有生机的绿意盎然,是未来得及感受就逝去的春光。






疫情下的面孔©️朱润资
疫情会如何改变城市?有些我们能想象到,比如某几家你钟爱的老街区里的小店终于支撑不下去,不得不停业关门,新的经济效益更好的连锁品牌、网红店将占领街区;一次又一次集体感染也许会改变酒店和公共住宅的通风设计,中央空调从此淘汰出局;没有48小时核酸证明的人似乎是在社会面“过期”,每日核酸成为准则;层层加码与出行禁令成为无形的围挡。但是更多是我们无法预料的,就像历史上的随机事件永久地铭刻在无形的日常生活结构上。
围挡之外,令上海自信张扬的天际线被冷落,城市前所未有的空。正如萨迪奇说:“街道是城市生长和繁荣的途径,为我们提供分享城市生活,体验‘拥挤文化’的场所,是街道塑造的行动模式与交通线让商店、住房、办公室和公共场所共存。”人,或者说居民的流动注定是城市设计与街道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在这种不得不的“围”与“挡”中,城市的共享与活力又将何去何从。

华庭宾馆被诟病存在管理疏漏导致疫情扩散©️朱润资
华亭宾馆建造于1986年,是上海规模最大、开业最早的五星级宾馆。今年2月16日,宾馆宣布歇业装修。装修第一天,宾馆被征用作隔离点。不到一个月后,这家宾馆被送上了“被告席”,罪名:因管理疏漏,引发疫情大规模传播。现在宾馆背面废弃的停车场堆着纸箱,纸箱里是送往各个居民区的物资


上海站

武康大楼

肇嘉浜路

南京路步行街

南京路步行街、浙江中路口

九江路

静安寺

南京西路

南京西路

陕西北路、南京西路口

西藏中路

北海路

江苏路

内环延安西路立交桥

泰兴路

外滩隧道

武康路、康平路口

南京西路、常德路口

江苏路、长宁路口

复兴西路、乌鲁木齐中路口

漕宝路

梅园路
2020年初,朱润资曾在曼彻斯特经历过近两个月的封城,面对2022年上海封城,作为建筑学背景出身的摄影师,他对城市和流动人群所面临的影响和变化,似乎有着某种隐约的预感。朱润资给这组照片命名为“Unfamiliar Familiarity”,他说那种陌生不全然陌生,里面还掺杂着熟悉,照片里的每一条街道他都走过,但一个人站在路口时,拍摄位置、拍摄角度、拍摄画面都让他感到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