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菜籽沟的日出(木贞摄)
当我们每天疲于抢菜、囤货,
注意力被各种信息牵制,
陷入焦躁不安时,
我们连线了远在新疆菜籽沟的刘亮程。
8年前,他把家从城市搬回了乡村,
重新过起了农耕生活,
忙于种菜、耕地、做木工。

刘亮程在乡村拍下的四季景色
刘亮程今年60岁,
上个世纪末,因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
一举成名,
这本书畅销了24年,感动8000万人,
其中5篇被选入中学、大学的语文课本,
林贤治赞美他是
“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
作为经历过逃荒、丧父、各种动荡的作家,
他笔下,几乎没有对苦难的描写。
他把苦难、战争、疫情
视为“非常态”,终有一日会平息,
他更乐于写乡村的平凡日常。

刘亮程在麦地
太阳的起落,一场又一场的风,
就连一朵云,一棵草,一只蚂蚁,
都被赋予了生命的意义。
这些曾被都市人遗忘的事物,
他都毫无保留地赞颂,
而这些,在疫情时期,显得尤为珍贵。
我们想知道,
他如何通过土地,收获抵抗“非常态”的力量。
自述 刘亮程
编辑 余璇 责编 倪楚娇


刘亮程在菜籽沟

木垒书院一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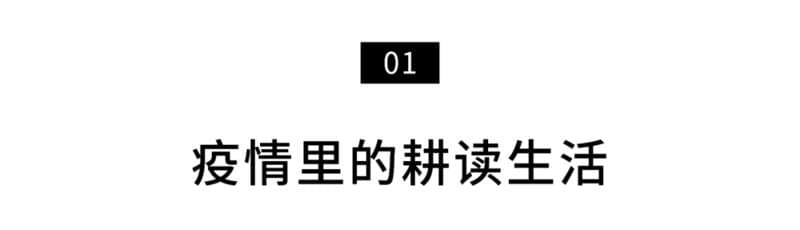
今年一开春,刘亮程就坐不住了,他开始在院子里种菜。
菜苗是冬天就育好的,先把菜种子一颗一颗丢进木盆,每天洒水,等它们长出来,再一颗颗地移开。茄子、辣子、西红柿、芹菜、洋葱、卷心菜……几乎所有的菜他都种。
刘亮程的菜地有3亩大,就在他的木垒书院里。2014年,他从乌鲁木齐搬到了天山北坡的菜籽沟村,买下当地一家废弃的学校改造成书院,又邀请了30多位艺术家来此居住,开始了边种地边写作的耕读生活。
去年7月新疆疫情,刘亮程正好被封在了书院里,一个月没出门。他带着三个志愿者,天天在地里干活。
再前一年,他春节探亲,也因为疫情被封在了沙湾县的一所单元楼里。因为无事可做,竟把小说《本巴》的主体基本写完,原本半年的计划最后仅花了40多天。

刘亮程在院子里种的南瓜
在刘亮程的眼中,疫情也好,封闭也罢,都是一个相对短暂的事情,迟早都会过去。
“最终人们还是会回到大地上,关注一年四季,关注春耕秋收,然后生儿育女,一年又一年,这才是人的常态。”
现在他的菜苗才长了一茬高,得再过一个月,才好栽到地里去。等到那时候,就可以看到哪颗菜长出了花骨朵,第二天开了花,有蜜蜂、蝴蝶在花朵上飞来飞去。然后,茄子、辣子纷纷长出来,再过一段时间,就能吃到这些菜了,那是一种充满了希望的生活。
因此,每天吃过早饭,他就想着把铁锹抓起来,到地里去。“一旦开始劳动,你头脑中的重就被解放了。我真正要是干起活来,我都不想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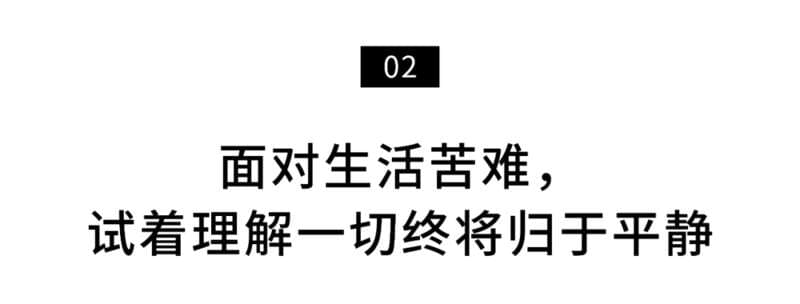

刘亮程养的狗他说:在村里,我们把宠物养成了动物
刘亮程被大家熟知,是因为1998年出版的《一个人的村庄》。
这是一本和大部分乡村文学截然不同的书。“几乎一个世纪的乡土文学,都在写乡土大地上人们的苦难,一场一场的战争、运动在碾压人性。”
刘亮程经历过父亲被迫害,也经历过“三反五反”,“但当我理解了生活终归是要走向正常,我就选择了生活中那些相对永恒的事物,不会过时的事物。”
在他的书里,院子里拉磨的驴,灶旁搬麸皮的蚂蚁,还有村子里家家户户养的狗……每一个寻常的生命,都得到了细致的描绘,被赋予神性。


菜籽沟的冬天
他这样写虫子的生命:
“我只是耐心地守候过一只小虫子的临终时光。在永无停息的生命喧哗中,我看到因死了一只小虫儿从此寂寞的土地。别的虫子在叫。别的鸟在飞。大地一片片明媚复苏时,在一只小虫子的全部感知里,大地暗淡下来。”
当乡村下起雪,他这样感慨:
“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
饥荒、动乱、战争、疫情,很少能长久占据他的心,因为:
人们时常埋怨生活,埋怨社会,甚至时代。总认为是这些大环境造成了自己多舛的命运。其实,生活中那些常被忽视的微小东西对人的作用才是最巨大的。也许正是它们影响了你,造就或毁掉了你,而你却从不知道。
在豆瓣上,《一个人的村庄》评分高达8.9,其中点赞最高的一条评论说:“如果有哪本散文,从我少年时代一直到成年甚至会到更年长的时候,仍然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那一定是这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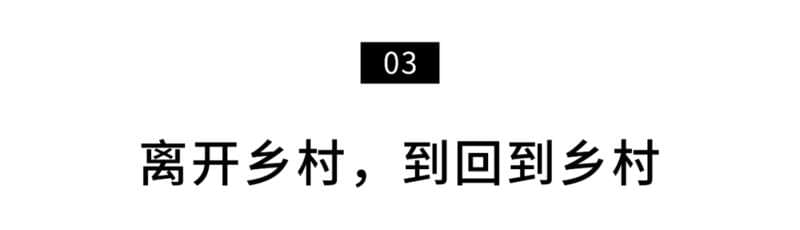

刘亮程在考察木垒县老羊头泉子村
刘亮程一辈子都在写乡村。从离开乡村,再到回到乡村,他花了20年。
在刘亮程出生前一年,因为逃荒,全家人从甘肃酒泉迁到了新疆沙湾县下面的一个小村庄,再过去就是沙漠。
小学断断续续地念完,他终于考上了中专。那时候是80年代,他的工作是在沙湾县城郊一个农机站岗当管理员,一年做两次报表,其余的时间就是骑着车在田间地头转悠,工作很悠闲。
他就在那时候开始写诗歌,写了十年,也在《星星》诗刊、《诗歌报》上发表。
后来个体户兴起,利用业余时间,他又开了一个农机配件门市部,不到一年,挣了1万块钱,“跟万元户似的,那时候觉得挣钱这么容易,就把配件门市部卖掉了,辞去工作,进到乌鲁木齐打工去了,那时候管这叫下海。”
在乌鲁木齐一家报社当了编辑,每个月拿四百五十块钱的工资,刘亮程开始了城市的生活。
因为忙于生存,诗歌再也写不出来,就开始写散文,花了10年,写出《一个人的村庄》。

刘亮程在院子里摘老苹果树上的果子
40岁的时候,靠着这本书的首版版税,刘亮程开了一个酒吧,装修花了一年,又开了不到一年,就倒闭了。朋友对他说:“你叫‘一个人的酒吧’,能不倒闭么?”于是他老老实实地去写作,《虚土》《凿空》两部小说就是那之后写出来的。
到了50岁,人生过半,眼看老去,刘亮程想,得给自己老年找一个营生干了。
他看上了一个道观,想当一个道长,带上一帮弟子,在那儿晨钟暮鼓地过老年日子。“但它是文物,买不了,也租不了。”
道长没做成,就到了木垒县菜籽沟。他的后半生,再次在乡村展开。
“年轻的时候,大家都向往远处的城市,但是等你活到你父亲母亲年龄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又回去了,回到你出发的地方。
乡村曾经是一个最诗意的居住地。它既可以安顿你的身体,让你在大地上劳动、有所收获,也可以安顿你的死亡、你的灵魂,这种美好已变成一个文化基因铸就在我们心中。”
以下是他的自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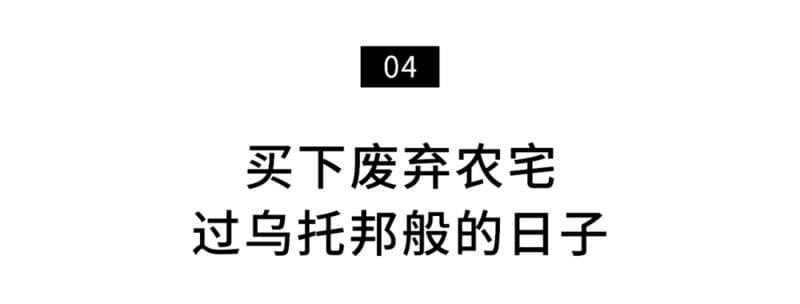

雨过天晴的菜籽沟
七八年前,当我来到菜籽沟,我觉得这里和我出生的村庄太像了。
那些人家的房屋,沿着小溪和山边,三三两两地排列着,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幅山水国画。
许多村民已经迁走,400多个农家院落里,只剩下了100多户人。剩下的空房子,也可能很快变成一堆木头,我心疼得不行,决定把家搬到这里来。我招来了30多个艺术家,一起申购了几十户农宅,一块儿在这生活。
他们以画家居多,还有作家、设计师、摄影家,等等,多半都是到了我这个年龄,退休了,来这儿收拾一个破院子,花很多精力很多钱,在这地方建一个自己的家,种种菜搞搞创作。

刘亮程在村里“走亲访友”
我在这里看上一所老学校,里面都是参天古树,有40亩地。买下来的时候,所有的教室和办公室里,都积着厚厚的一层羊粪。我们把羊粪一锹锹地清理出来,找到了教室的地,找到了讲台,还找到了那一代学生留下的铁皮铅笔盒。
我把这个学校做成了国学书院,叫木垒书院,给自己封了个“院长”,这算是给自己后半生找了一个营生。从那时候到现在,又忙忙碌碌折腾了将近10年。
不过书院只花钱不赚钱,我还养了几个人,帮我管理院子。偶尔有些培训班,可能有点小收益,这点收益可能还不够发厨师的工资。
但是我不着急,着什么急。《一个人的村庄》一直畅销,每年都有数万本的销售。而且我不断地有新书出版,靠版税还可以养活书院。

和志愿者一起扎的一段篱笆
我每年都会招3到5个志愿者过来跟我们一块生活、耕读。我会安排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活跟他们一块干,比如扎一段菜地的篱笆墙,或者修一段路,或者是用手工做一件东西。因为我木匠活很在行,就带着他们去干。
志愿者多半是大学生,还有研究生之类的。因为他们在学校已经读了太多的书,他们最需要的是动手去做事情。动起手来,他们就忘记去学习了,这是最好的状态,在动手中学习。
我记得三年前来了一个博士生,一个学戏剧的,正在写一个剧本,写不下去,到这来耕读。
正好是春天,我买了一些树苗,他帮我栽树。他从来都没挖过坑,栽树首先要用铁锹挖一个小坑,然后把树栽进去。当挖完几个坑,把树苗栽进去以后,他觉得非常有收获,自己终于学会挖坑了。我想以后在他的剧本中,他也会学会挖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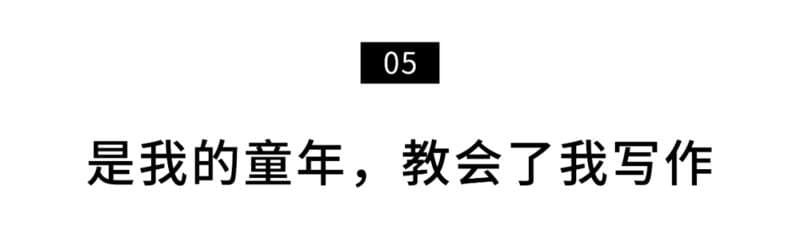

菜籽沟的冬季雪景 等雪消地开,草就开始长出来
我的文章收入中学课本之后,我也经常在微博上看到一些学生的留言。
尤其《寒风吹彻》那篇文章,有女生留言说,她在课堂上读着,她会忍不住流泪,哭出声来。
我想对被感动的孩子来说,他们已经读懂了。但是那些孩子紧接着留言说,一旦让他们开始做关于这篇文章的问答题的时候,就痛苦无比。
我们现在的语文教育,在当数学来教。语文应该是让孩子形成他自己无拘无束的、宽阔的情感,和无数的想象力的。
现在把它收紧到一个窄窄的道里面,那叫“系縻”,就是把牲口拴住的意思。这样怎么可能培养出一个作家来。

刘亮程在戈壁
我读书那会儿,小学上到一年级,父亲被迫害,不在了。二年级没上完,村子里面学校就停了,隔壁村的学校又太远,我就在家闲待着。直到十几岁时候,我才又重新去上学。
那时候,我喜欢看新疆辽阔的戈壁滩,能看见地平线,还有头顶如穹庐般的天空,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少有绿色,裸露的荒漠带给人一种荒凉。我一遍又一遍地,怎么也看不烦。
父亲去世后,我又有了一个后父,他是一个说书人。
一到晚上,好多村民就聚集到我们家。那时候房子也很小,大人就坐在炕上,小孩就蹲在地下,或者坐在小板凳上,听我父亲在那讲《三国》《杨家将》《薛仁贵征西》。一段一段,他讲一遍我就能记住,还可以讲给别的小孩听。
尽管那时候没有读到很多书,但我的后父让我很早就听到了一些书里的故事,也学会了讲故事。

刘亮程和外孙女知知
我觉得教育最重要的,就是还给孩子一个童年。
我们家小外孙女,你几乎不用管,把她放在地上,坐到一大堆玩具中间,她就把所有的玩具都编成故事,这颗心灵中装了好多灵性的东西,她会知道自己干啥的。
有人问我,我写了那么多虫子、狗,在里面能发现美,是不是我特别敏感,异于常人?
其实并不是,没有孩子小时候不会对着一只虫,一朵花发呆。
大人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但他肯定看到了远比大人看到的更丰富的东西,而这就是童年。只是很多人长大后,都把它给忘记了。
等我回过头去写自己的童年的时候,我才发现许许多多以后我再也看不到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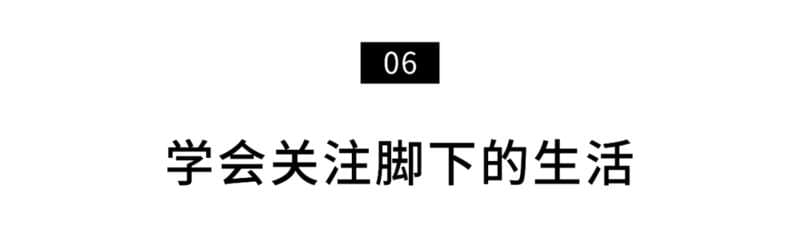

菜籽沟收割完的麦地
现在年轻人都很焦虑,我想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获得什么,可能他们挣钱的欲望比我们那时候更强烈,生活的压力也更大。
但是我觉得,物质可以改变表面的自己,却不能改变内心的自己。一个人最终的财富是他的内心。
内心世界是一个建筑,父母很早就给了我们一个内心,儿女唯一可以改变的就是不断地学习,不断地修养,不断地去知道这个世界更为丰富的内容,从文学、哲学、各个艺术门类来获得自己的心灵滋养,完成一个更高贵的内心世界。
有一颗能够自我安顿的心灵,你的愉快和不愉快都能自己把握。即使遇到大的挫折,这颗能够自我把握的心灵可以让你安静下来,让你重新再出发。

冬天书院里的小猫咪
面对命运的波澜,我觉得普通人要有一个普通的关注点。
近日俄乌战争的报道我也看,包括网络上的一些热点我都会看,但是我从来不过度关注。
当然那些大事总得有人去关心,但如果为了关心那些事,丧失了对身边大事的关心,你就是一个虚妄的人,一个躲清闲的人。
去年我加入了新疆野骆驼保护协会。4月或5月,我会抽时间去看看野骆驼。新疆的野骆驼已经濒临灭绝,我想去录制一些视频,呼吁大家去关注这样一个东西。
如果能够帮助野骆驼做点事,让这个种群从濒危到能够活下来,我觉得真是一件大事情。
因为我觉得身边发生的好多事很大。我们院子丢了一只猫,村里面前两天有一个老人住院了,这些事不大吗?在你的生活中,在你的身边,时时刻刻都在发生非常大的事情,只是你视而不见,你把它当成小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