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的院线片中,
初出茅庐的殷若昕《我的姐姐》、
邵艺辉《爱情神话》、申瑜《兔子暴力》,
都拿出了兼具女性意识和票房实力的口碑之作。
《导演请指教》综艺里,
总决赛男女比例是惊人的1:4,
拿到“最有价值导演”的是女导演曾赠。

德格娜在片场

曾赠在片场
在过去一年里
戛纳、柏林、威尼斯的最高奖
均由女导演获得。
在奥斯卡,被男性占据的最佳导演和剧情片,
越来越多地出现女性的名字。
这是史无前例的,崭新的,属于女性的时刻。然而,当我们继续探究,会发现,
女性从业者的数量和认可度,
远远比我们想象得少。
一条采访了多位青年女导演,
想看看,她们都走过什么样的道路,
才最终被看到?
撰文 洪冰蟾 责编 倪楚娇


德格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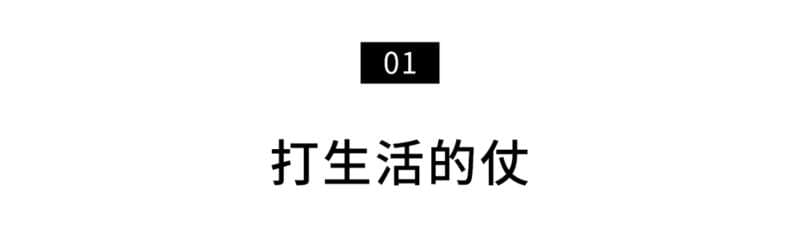
德格娜站上FISRT领奖台时,剃着寸头,肚子里怀着老二。
那是2015年,她31岁,凭借《告别》拿到FIRST最佳剧情长片奖。很多人以为这是她事业的起点,但她已经默默决定,把精力放回家庭,多陪伴两个孩子。
这个选择,意味着她难以进行高强度的工作。在此后的7年时间里,她没有任何一部长片问世。直到她上了综艺《导演请指教》,很多人才想起她的存在。

冬天的早晨,德格娜骑滑板车出行
多数时候,德格娜就是在柴米油盐里“打生活的仗”。
照顾两个孩子,大的那个刚上小学,德格娜基本没有懒觉可以睡,家里根本没法安心工作。偶尔出门去看点书,是她少有的属于自己的时间。她会骑一辆电动滑板车,冬天的时候裹得只露出一双眼,来去自由。
“有一回张大磊(《八月》导演)跟我说,他要回内蒙,去写个剧本,顺便带孩子。我一听就笑了。有孩子根本没可能的,整个假期毁于一旦,还想要搞艺术。”

麦丽丝,代表作《悲情布鲁克》《天上草原》
德格娜的选择和她的母亲有关。
母亲麦丽丝是内蒙古制片厂的导演。小时候,德格娜被放在奶奶家照顾,母亲在剪片子的中间回来看她一次,立刻再去片场,这一去就是两三个月。
“我在缺乏安全感的环境里长大。跟我母亲抱怨过这种陪伴的缺失,也会觉得她时常不够理解我……”
长大了,德格娜自己当导演才意识到,“事业有成的女导演”和“时常陪伴孩子的母亲”,两者不可兼得。而她选择后者。

王一淳
不止一个人有这样的疑惑,在大学的导演系里,男女的比例是差不多的。为什么进入行业后,女性会一个又一个地消失?
很多导演把30岁视为拍出第一部作品的时间,而30岁左右的女性,许多正面临着生育、家庭的重担。在带娃和家务间歇里,挤出创作的时间。
中国影史票房榜前100名,由女性独立执导的,只有两部。除了《你好,李焕英》,还有排名第53位的《后来的我们》。而贾玲和刘若英,都是从演员转型做的导演,一定程度上借助了“演员”身份的势能。

《过春天》剧照
没名气、没投资、没声量,还陷在生活的琐碎里,是很多青年女导演的共同困境。
凭借《过春天》,拿到2018年平遥电影节最高奖的导演白雪,和德格娜同岁。
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她结婚生子,操持家务。因为不愿意把脚步停下来,她拿出破釜沉舟的决心,去深圳口岸做田野,没人投钱也要拍。
在其他媒体采访中,她说自己是“一个写不出剧本的待业主妇”。“我为我孩子的付出,是非常值得的……但是你内心深处是很痛苦的。你会很想拍。”拍完后,她的感觉是“长出一口气,感觉迎来了人生最好的时候。”

王一淳接受“一条”采访
同样在《导演请指教》上大放异彩的王一淳,1977年生,自称“大龄已婚女导演”。日常的生活就是接送孩子,照顾植物,在冰箱上贴家务事的纸条。
当年写完剧本,王一淳发现自己没专业,没背景,没名气,没人给她投钱,得靠家里支持。拍出来又没钱做后期,只好闲置在家里。
“后来那张光盘成了我老公吵架最有力的证据。不管因为什么吵架,只要他一说,看!这就是我们家最贵的东⻄,一张300万的光盘!我立刻就没话了。”

《黑处有什么》剧照
2015年,她38岁,一波三折地交出处女作《黑处有什么》,拿到FIRST最佳导演奖。姜文评价她一个字:坏。“得到这个评价,我很骄傲,打算好好干上一场。”
但等到王一淳交出第二部长片《绑架毛乎乎》时,已过去7年。这些年,她依然是家庭主妇,先花了几年写新的故事,过程中想去家政公司体验生活,但苦于没人给她带娃。
后头几年,她一直在和资方打交道,转了一大圈,还是自己掏了钱拍。“挺坎坷的,总有意料不到的事出现,一不小心耗了这么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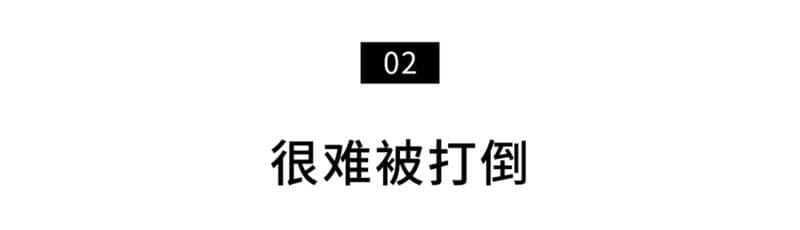

曾赠在拍《明月的花园》
接到《导演请指教》邀请的时候,曾赠、王一淳、德格娜都没有犹豫。这是她们等了平均8年的,被看到的机会。
在节目中里,曾赠第一次出场,被称为“新人导演”。其实她做导演有7、8个年头了。但一开始,没有演员愿意选她的组,因为没有看过她的作品,她是陌生的,不知能耐的。
她2016年就“出道”了, 当年“坏猴子影业”公布了“新人导演支持计划”,有文牧野、路阳、沙漠、温仕培,一排男导演里,1987年生的曾赠是唯二的女生。

《云水》剧照
“有时候导演也没办法掌控一部电影的命运。电影工业是这样深不可测,我只是其中的一个⻮轮。 ”
2021年初,她感觉自己生活在巨大的挫败感之中。“来北京十几年,一事无成,那不如搬回湖南算了。
她借着生日的由头,写了好⻓的告别辞,准备酒过三巡,告诉朋友们,她不干了。“临到关头,我一看大家聊得挺开心。没必要搞得这么伤感。后来想再坚持一下吧,我就赖着没走。”
节目里,她最终一路逆袭,从不被看好到拿下了最高荣誉。

曾赠在拍《云水》
按照《导演请指教》的赛制,两三天就要完成一个短片。
曾赠的运气很不好,每逢拍戏,必下雨。第一支《爱情》在沙漠里拍,竟然也下雨。剧组没有预备,去现场一看,景都成了泥。制作时间因此被大量压缩,曾赠只能熬。
德格娜有一次碰到曾赠,两个人都灰头土脸的。“哪里顾得上妆容精致,都没时间睡觉了。”
德格娜苦笑,跟曾赠说:“我今天早上去洗了澡。”曾赠回道:“我也刷了个牙。”
王一淳遇到最大的难题就是身体。“再让我拍一回,我肯定撑不住了。真是咬牙撑过来的,心里老惦记事,几乎无法睡觉,靠吃药才能躺一会。”

德格娜去牧区拍《巴德玛》
真人秀中呈现的超高压工作,是导演的日常。导演的工作时间,往往比996更漫长。根据“画外”2020年的调查,“近半数导演的日均工作时长都在8-12小时之间,甚至有21%平均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
对女性来说,拼身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剧组一直以来的运作机制,大多由男性来制定,遵照的多是男性的体力、习惯和社交方式。
2022年发布的赛璐珞天花板报告(The Celluloid Ceiling Report) 显示,2021年top250的电影的制作团队中,94%没有女性摄影师,73%没有女性剪辑师,72%没有女性编剧。
一组对比数字是,仅有4%的电影,团队里只有0-4位男性工作人员;但只有0-4个女性的团队,这个数字是惊人的61%。

曾赠在片场
为了取得团队的信任,女性导演必须适应这样的节奏,甚至做得更好。
曾赠说:“过去我拍片是很凶的,非常强势且不好商量。在一个全部是男性工作人员的结构里,我天然想去武装自己的女性身份,担心受到质疑。”
不仅如此,还有古老的规矩横在路中间。曾有一位年轻的女导演,在开机仪式上特地宣布,在她的组里,所有女性都可以坐苹果箱(解决演员或物体高度问题的垫脚木箱)。女人坐苹果箱,被认为会带来晦气,至今仍有一些女性从业者因为坐在一个木箱上遭到训斥。
或许曾赠的一句话,很适合女导演们的心境:“当我知道完成一件事情,要经历困难和绵长的等待时,我会在心里一直攻击自己,对未来很丧,但很难被打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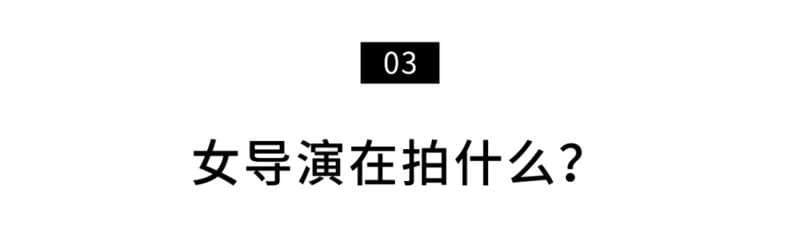

《黑处有什么》剧照
女性导演的视角,因为稀缺,显得弥足珍贵。
因为她们的冒头,我们才有了这样的作品:关注家庭中母亲的处境的《82年生的金智英》、《暗处的母亲》、《平行母亲》……关注性侵、堕胎问题的《从不,很少,有时,总是》、《日本之耻》、《前程似锦的女孩》、《正发生》……
在国内,讲两性、母女之间复杂关系的《她房间里的云》《春潮》《柔情史》《兔子暴力》,罕见又自如地展现中女情感的《爱情神话》,讲婚姻选择的《金都》,讲青春的危险、暧昧与懵懂的《过春天》,和讲生育政策下沉默的“姐姐们”的《我的姐姐》……均出自女性导演之手。
她们从女性的身份出发,对现实的状况,有别样的反思和极强的同理心。

《兔子暴力》剧照
《兔子暴力》的导演申瑜是一位母亲。她做完月子后得了产后抑郁症,买了一辆摩托车,冬天还在山上轧马路,直到后来出了小车祸,才把车卖了。
“那时候我整天就想去外面游荡,过了很多年在育儿公众号上看到,才意识到,哦,原来我当年是抑郁了。” 她体验过那种被鸡毛蒜皮压到绝望的状态。于是她颠覆刻板印象里的母亲形象,电影的主角是一个生下孩子后出走的女性角色,神秘、迷人又脆弱。
“我们这一代人,是看动漫和听摇滚乐长大的,你说这样成长的女孩当妈后,怎么还会跟以往操劳、隐忍的母亲一样呢?”

《我的姐姐》里,父母离世,要照顾弟弟的姐姐
《我的姐姐》收获8.6亿票房,导演殷若昕决定拍这部片,是因为接触过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姐姐”。
“好像重男轻女这个东西,一直是隐隐地流淌在我们骨血里的。4年前,我经历了怀孕生产。有一次我在排队产检,听到前面有一个已经剖腹产三次的女性,为了生儿子,她现在又怀孕了,医生就说我不可能再给你剖腹产了,太危险。但这个女性一定要生,求着医生建档。 ”殷若昕说。
她想揭开困境中的女性会经历的痛,被漠视,没有被良好地对待。《我的姐姐》的开放式结局引发争议,指责姐姐还是要为弟弟牺牲。但这恰恰是女性创作者的珍贵之处,给女性以支持而不是支配。
“告诉女性应该怎么做,是不公平的,因为你没有处在那个女性所处的位置上,没有面对的她的那些矛盾和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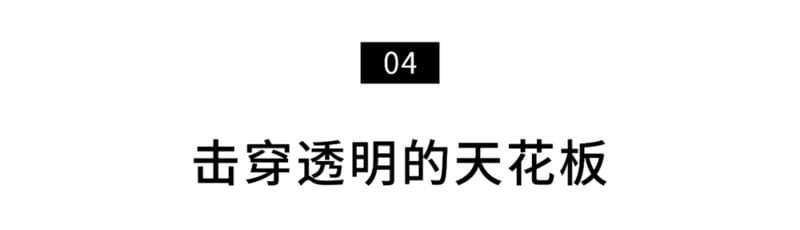

德格娜
在我们的采访里,建立平等和信任的工作关系,是最常被提及的字眼。
曾赠在《导演请指教》拍完4支短片后,每一次都会手写所有工作人员的名字,“我记不住所有人的名字,但想向他们致意。”
拍摄遇到特殊情况,她说的最多的是“还好大家能陪我苦熬”。拍片最骄傲的时刻是“跟我一起工作,大家能感受到开心和平等。”

《爱情神话》剧照
《爱情神话》里中女们反客为主。现实里,导演邵艺辉和制片人叶婷,这两个新生代的女性,也“反客为主”地带领着一群“老炮儿”。
除了一桌跨年饭,她们没有组织过一场饭局用来搞关系。剧组关系融洽,她们讲话细声细语,但没有人会因此轻视她们的意见。
因为在上海市区21点后不能拍摄,他们没有熬大夜,没有赶工,每天都是一早开工,晚上9点前准时收工。休息间歇,大家就到街上喝杯咖啡、吃碗小馄饨。演员们每天像上下班一样来拍戏,收工就骑个车、散个步回家吃饭去了。

《我的姐姐》剧照
我们也能看到女性之间的守望相助。
《我的姐姐》的导演殷若昕、编剧游晓颖、制片人尹露、主演张子枫都是女性。她们在一起工作,源于对女性命运的共鸣。张子枫为了角色剪掉了长发,殷若昕也把头发剪短了,“和她一起同呼吸共命运。 ”她会在监视器前流泪,拍悲伤的戏时告诉张子枫,“今天这场戏,可能会很痛苦。”
《送我上青云》的导演滕丛丛在其他媒体的采访中说,以前在片场,有人问她抽不抽烟,喝不喝酒,唱不唱K,她都拒绝。对方的反应是:“你这样当不了导演的。”她不信,她相信一个好的故事,才能打开这扇门。直到有一天,姚晨看到了她的剧本,决定做她的制片人和女主角,帮她请来优秀的声音、剪辑和摄影。

曾赠的短片《爱情》剧照
李玉在青葱计划做导师,认领了两个女性主义的剧本,其中一个就是《兔子暴力》。她欣赏申瑜的才华,帮申瑜做监制,鼓励她就算不完美也没关系,但是“要生猛”,“任性一把”,“完成自己想要的”。
我们时常提及“玻璃天花板”。在职场中,一个透明的,好像不存在的,但实实在在影响女性的发展的障碍。在影视行业,这被叫作赛璐珞天花板,指女性数量的不足。一种被许多人认可的,刺穿赛璐珞天花板的方式,就是“运用钱包的力量”,支持女性导演的作品。
女导演的存在,不仅提供了重要的、往往被忽略的声音,更有助于从业者的性别平衡。研究显示,女导演的团队中,女性成员往往比例更高。
曾赠总是这样介绍自己:曾赠,导演,女。
“曾赠是我自己,导演是我的职业,女性是我的性别。我希望大家平等地看待导演这个职业,我也非常高兴自己是一个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