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塔门(ID:DT-Tamen),原标题《为什么东北延吉长满了咖啡馆?》,作者:刘丹,编辑:王朝靖,题图来自:受访者
2021年网易数读曾经整理过一份“在中国,哪个城市拥有最多的咖啡馆”的数据,上海作为全球咖啡馆数量最多的城市,毫无疑问排名第一。榜单上除了北上广外,也都是成都、杭州、苏州、重庆这样的准一线城市。有意思的是,榜单后的留言区,出现了好几次这样的评论:居然没有延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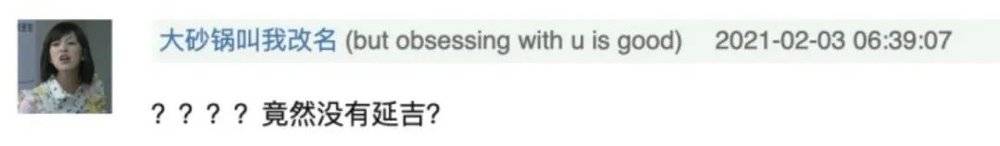

作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首府,延吉相当于一个县级市,全市人口近69万。根据第一财经去年3月的统计数据,上海的每万人咖啡馆拥有量为2.85家。而综合当地店主的说法,四线城市的延吉,目前有800多家咖啡店,算下来每万人咖啡馆拥有量是上海的四倍多。
早在1992年中韩建交前夕,学者季羡林应邀前往延边大学参观访问,就已经用“怪”来总结眼前的延吉,“三十万人口的一个小城,竟有卡拉OK一百二十家,还有二十家在筹建中,另有人告诉我,城中类似卡拉OK的茶馆、咖啡馆之类,有400家。”
当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北上广,四五线小县城也在模仿这些大城市。“咖啡”就是一条这种模仿秀的线索。
这里有两个延吉咖啡店小老板的故事。延吉是个特殊的样本,从咖啡出发,能看到潮流如何随这座城市浮动,又如何反过来勾勒出城市的肌理变化。
以下为正文:
我对延吉的想象由一系列彼此矛盾的碎片拼接成的。印象最深的是“洋气”——有位朋友转述她延吉朋友的话说,延吉女孩绝不穿肉色打底裤。与之相对立的形象是韩国电影《黄海》中如野狗般奔逃的出租车司机久南,以及从延边杀到首尔,挥着大棒骨砸人的狗贩子老绵。
另外则是有关脱北者的悲情传说,有关在韩务工人员的财富密码,以及作为中国朝鲜族人,遥望韩朝两边时的复杂情绪。被我用以构建对这座城市的想象的碎片,毕竟都取材那些存在于过去的东西。当我来到延吉,我是说去年夏天,在社交媒体上以“小首尔”走红的那个延吉,由电影、报道,以及都市传说拼贴而成的延吉就消失了。
眼前是一座由咖啡馆串连起来的城市。咖啡馆中折叠了两种时空。店里,咖啡与落日灯、大叶绿植以及灰白色极简风的装修共同摆出首尔或者北上广都市生活的精致腔调;穿过门口那块小小的人工草坪,街对面的老民居和小电瓶立刻将场景扭转为县城,让咖啡厅变得突兀起来。而城市新故事的产生,就是给突兀找到合理解释的过程。

1. 像韩剧那样喝咖啡
面积100多平,有7个空间,对应7张桌。每块空间的面积远比北京或者上海市区内月租金3500元的合租屋单间大。这是90后朝鲜族青年小崔的咖啡店。
在延吉,类似的空间利用不是稀罕事——目前延吉最大的咖啡厅面积有1500平,去年12月开业,曾邀请韩国男团SuperJunior的成员金希澈等明星拍摄视频站台。坊间传言,店的装修成本高达700万元。在大众点评上,它的人均消费仅为51元。
同龄汉族小孩还在看《还珠格格》时,小崔就在看韩剧了,“人们总在咖啡厅里见面聊天。”潮流来到延吉,卖速溶咖啡的“茶座”和“咖啡座”由此出现。人们在里头喝酒,打牌,比起咖啡厅,所谓的“咖啡座”其实更接近于酒吧。

2008年,韩国连锁咖啡品牌“含旨咖啡”进入中国,并于2010年开设门店。“含旨刚进来,我就吵着要去。它是延吉第一家卖expresso,拿铁、美式这些咖啡的店。”
“含旨咖啡”在延吉发展得最好的那几年,也是朝鲜族劳务输出大规模增长的时候。2008年前后,小崔父亲在韩国的月收入换算成人民币有两万多元——基本相当于当年上海城镇居民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小崔母亲每个月在韩国也能赚一万多元。
高中生小崔在咖啡馆消费的第一杯咖啡要价24元,“好贵啊!但咖啡厅环境好,我乐意待。”他觉得朝鲜族对价格不敏感,“只要店里服务好,大家就觉得这个钱就是可以花的。”
上大学期间,小崔曾在韩国做过一年交换生,首尔的街巷里,每走几步就有一家精品咖啡厅,人们把咖啡当作口粮,“想喝随随便便就喝了。”那时他就盘算着回延吉开店了,“延吉的咖啡行业完全能复制韩国的路线。”
毕业后,小崔先是去上海做建筑设计师。工作快四年,攒下三十多万,来到2020年,他回到延吉。“失败了大不了再去上海打工。”《2020咖啡消费市场洞察报告》提到,受疫情影响,咖啡服务行业的闭店率达到83.3%。
而小崔的店现在已经开到第4家。据他介绍,2020年延边州新开了近200家咖啡店。“我们这是有点奇怪”,小崔说,“在延吉,做咖啡师和做公务员差不多,不愁工作。”
2. 像网红那样喝咖啡
以延边大学对面的大学城为背景——那是延吉最具代表性的“弹幕墙”,双语招牌密集排布于建筑外墙,像屏幕上挤满弹幕——迎着弹幕墙,举起手中那杯印有“延吉”二字的咖啡拍照,配文关键词:小首尔/假装在韩国。
这是近两年在小红书等平台打卡延吉的标准动作。把延吉印在杯套上是“后浪咖啡”店主小张的主意,这个店名来源于2020年五四青年节时,B站推出的演讲视频《后浪》。
“后浪咖啡”的英文是Young Blood,小张希望一切都是新鲜的,“牛奶、豆子,人,做咖啡的方式,萃取的手法,这些都要新。”
除了印有“延吉”的杯套,“后浪”的优势还在于性价比,店里一杯美式14元,用券后不到10元。“我们卖的应该是目前东三省最便宜的SOE了。”有辨识度的杯套叠加价格优势,小张的店很快蹿升为延吉有名的“网红店”。

至少在小张和小崔俩人的了解范围里,“后浪”可能是当地少有的由汉族年轻人经营并且能赚到钱的咖啡店。小张还没听说过其他汉族咖啡店主,“开餐饮的有不少”,而小崔说起自己的一个汉族好友,“他就是不理解为什么要花钱去咖啡厅,就是觉得开咖啡厅不挣钱,我叫他去咖啡厅坐坐,他也不去。”
小张与小崔年龄相仿,但他得等到上了大学才常去咖啡馆。“当时就是喜欢咖啡馆的氛围,还有机器,对味道其实没有什么判别。”
他去的第一家咖啡店叫“头福乐舒”,店名是topresso的音译,也是韩国品牌,2013年进入延吉,2016年前后关店。与“含旨”相比,“头福乐舒”不仅定价稍低,对小张这样的学生来说还有个特别大的吸引力:店里的咖啡可以续杯。
后来对咖啡研究得多了,小张发现,延吉大多数咖啡馆的环境和服务确实没得说,反而是咖啡本身的质量没跟上来。“尤其是很多国外品牌,到中国来都是想赚中国人的钱,卖的是优越感。咖啡说到底就是一个饮料,需要进到人的肚子里。”
小张的店算是“随手”开起来的,本来是自己在家玩设备,越买越贵,越买越专业,完全可以开个店了。“中国人不骗中国人。”他总说这句话。
不同于市里大多数装修讲究、空间宽敞的咖啡店,小张的第一家咖啡店开在居民楼下面,是用阳台改造出来的,面积9平左右。看到央视对延吉美食的报道,他又把“延吉”印在了杯套上,“虽然我们没啥影响力,但也想为家乡加油。”
在人们没办法出国旅游的第一年,延吉以“小首尔”之名成为“网红城市”。背负着城市名字的“后浪”,也成为了被流量随机选中的那个。“后浪咖啡”的外墙上印着几行标语:
后浪青年
敢于尝试新鲜事物
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添砖加瓦
3. 像北上广那样喝咖啡
“我们这确实是个小地方”,小崔说。但他不理解有些人从大城市回来后的优越感,“我还是挺喜欢我家乡的。”尤其让他自豪的是延吉人对潮流的讲究,“很多开店的人会去北上广深找设计师,不管出多少钱都要把最好的设计带回来。”
潮流只在城市内部涌动。有一部叫《延边口技》纪录片记录了世纪初延吉朝鲜族青年对BBOX的狂热。主人公桂晶说,在上海,如果你问年轻人知不知道BBOX,十个人里可能有一个人知道,但在延边,如果有一个年轻人不知道,那就很奇怪了。
另一个可以佐证延吉“时髦”程度的细节是,2015年8月,风头正盛的韩国男子组合BIGBANG曾宣布在延吉人民体育场举办演唱会,同步官宣的其它巡演场次都在深圳、南京,成都等一线城市。不过,延吉场演唱会最终因不可抗力取消。
外地人想象中的延吉往往归于另一套叙事。小崔去上海工作时,跟同事介绍自己是来自延吉的朝鲜族,“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你是从朝鲜过来的,要么就觉得你是韩国人。他们也不是故意的,而是确实不懂,对朝鲜族这个民族还不是很了解。”
民族身份没有给小崔造成太大困扰,回到老家,主要还是“在上海没混明白”。他从没想过去韩国打工,“这几年越来越不挣钱,我爸妈已经回来了。他们也支持我在国内发展。”
小崔觉得,延吉咖啡馆在2020年近乎于“奇葩”的增长势头,与本地“无业游民”变多了也有关系。延吉的机场在2020年3月暂停了飞韩国的国际航班,8月下旬才重启。外出务工受阻,延吉也无力为年轻人提供太多就业机会。“在延吉,你想吃饭只能去做生意。”
延吉曾被寄予“小香港”的厚望,就像与朝鲜第四大城市新义州隔江相望的丹东,那个期待着在朝鲜改革开放后成为“小深圳”的城市,它们连接着同一个民族的不同流向,都有寄托于外部世界的,不知何时能被兑现的,成为下一个某地的梦想。
2016年前后,以“咖啡陪你”破产为代表,曾经迅猛扩张的韩国咖啡品牌败走中国。韩流也在中国退潮。“韩国没什么可学的了”,小崔目标明确,要把上海的开店经验带回老家。“闪电泡芙”,他瞄准这款单品,“我在上海吃过,好吃。”现在这成了他们家店里的招牌。

韩国对于朝鲜族年轻人的吸引力正在消退。他们的父辈曾在韩国从事最为肮脏、危险和困难的工作,而年轻人想要体面,在老家开花店或者咖啡店。选择去上海,选择回延吉,选择开咖啡店。在延吉,迭代的不只是人群,新的咖啡馆也走在新的路上。
小崔对顾客有明确要求:不能在店里打牌,不能在店里喧哗。“以前的咖啡馆会讲究韩国那种前后辈关系,现在20多岁开店的人会拒绝这些。”
4. 像延吉人那样喝咖啡
小张不喜欢外面的人把延吉称作小首尔小韩国,“我们这里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我们弹幕墙上的字是朝鲜语,不是韩语。”
小张和“后浪”是延吉咖啡的特例。现在来店消费的本地人差不多能和游客持平,但就小张的观察,在涌向“后浪”的人群中,大概只有10%到15%是朝鲜族客人,“而且几乎没有回头客。”
从开店之初,小张坚持做口味偏酸的咖啡,他相信这样才能更好地呈现豆子的风味,而且国内一线城市的精品咖啡店基本都在做偏酸的口感。但是,“之前韩国的咖啡比较苦,延吉人的咖啡口味也是偏苦的。”口味上的差异让小张在开店前四个月收到许多差评。
有个客人骂他,说他的咖啡变质了,还好意思带着印字的杯套,简直是在给延吉抹黑。小张打电话反复解释,对方就是不接受,气得小张大哭一场。哭过也就过去了。他的咖啡要塞进写着“延吉”的杯套里,再装进印着“I DRINK COFFEE IN YANJI”的手提袋中,与城市紧紧抱在一起。“文化差异确实存在,但说来说去咱们都是同一个地方的人。”

非要说小崔和小张有什么交集,除了在延吉开咖啡店,还有就是他们都曾被一首歌打动。
歌是《阿里郎》,歌手叫Ugly Z,也和小崔小张差不多大,少年时在延吉、北京、天津等地辗转,也曾去韩国打工。在《中国新说唱2020》舞台上,Ugly Z用这首歌击败了对手。
他在歌词里写到,“不管我选择的是错与对,不管有多难都不退,好像真的只有代表我的同胞站到这个舞台上,我才能安然入睡。”
小张常在店里播放这首歌,他专门为Ugly Z做了致敬海报,还主动跟游客介绍这是延吉出来的说唱歌手。“虽然他跟我不是一个民族,但是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区,我觉得他的说唱很酷,能让更多人了解我们这个地方。”
在朝鲜族颠沛流离的移民史中,《阿里郎》演变出多种版本。不同于国内大部分观众熟悉的婉转曲调,Ugly Z结合了朝鲜族传统曲艺“盘索里”的唱腔,悲怆澎湃。他的微博至今仍置顶出演《阿里郎》的现场视频,文案写到:此舞台,愿望成真,掀起一股“朝流风 ”。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塔门(ID:DT-Tamen),作者:刘丹,编辑:王朝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