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李佩珊,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部讲述止痛药奥施康定如何引发阿片类药物危机的美剧《成瘾剂量》正在流行。这是一个受欢迎的大众故事:它的核心讲述了实现了“美国梦”的萨克勒家族是如何主导一家势力庞大的制药企业——普渡药业,在和医疗系统、政府的沆瀣一气下,在几十年间造成大规模美国普通民众药物滥用、上瘾和一系列相关社会危机。
然而,在受欢迎的大众故事背后,往往有着“月之暗面”:为了加剧戏剧冲突,剧中主要的几位“受害者”,包括一位医师,都被刻画成无辜地按处方服药后上瘾的,这增强了普渡药业的罪大恶极。事实上,根据美国药物滥用和精神健康服务管理局(SAMHSA)2015年度报告,近80%的阿片类药物成瘾者一开始并没有因为疼痛获得处方接触到阿片类药物,而是从家人或者朋友处非法获得的。这些年轻人大半是出于娱乐的目的,阿片类药物可以在大脑中产生大量的多巴胺。
剧中仅仅让“20%的处方成瘾者”的形象被展示了,这当然不能洗刷普渡药业明知奥施康定引发上瘾问题却为了巨大商业利益而频频否认和灭火的罪恶,但对于仍旧需要阿片类药物进行疼痛管理的慢性疼痛患者而言,这种将止痛药和瘾君子形象联系起来所引发的大众恐惧,造成的压力很可能让他们无法再获得药物。对于未寻求诊断和治疗的症状者而言,担忧和羞耻可能会让他们讳病忌医、忍受疼痛,而这对于他们的健康乃至生命而言,都可能是非常糟糕的选择。
未经干预的慢性疼痛患者的自杀率相当之高:在美国2003年至2014年间12.3万人的自杀人群中,9%的人曾受慢性疼痛。(《内科学年鉴》2018年10月)这正是权威医疗专家们对阿片类危机最担忧的问题,人们将因为恐惧,重新回到忍受疼痛的黑暗时代。
而根据《中国疼痛病学发展报告(2020)》,中国慢性疼痛患者超过了3亿人,并以每年1000万至2000万人的速度快速增长,但目前仅有一线城市少数医院开设了单独的疼痛专科。
我们和疼痛之间的距离,像我们与恶的距离一样值得思考和重新认识。
宏观层面看,人类认识到疼痛不是耻辱,疼痛不仅和身体相关,也和心灵相关,并且应当得到治疗,背后正是个体性的萌发和彰显,意味着现代性来之不易的到来。我们不仅应该学习到疼痛是一种疾病,同时也该意识到,这是一种和社会问题之间有着复杂关联的系统性疾病,正如哈佛大学医学人类学者凯博文所说的,权力的“地方场景”是人类心灵痛苦的社会根源,其“躯体化”造成了身体上难以医治的慢性疼痛。因此,要解决大规模的个体慢性疼痛,还要关注个体所遭受的不平等并寻求相应的社会变革之道。
微观来看,疼痛领域的专家们已经用“疼痛管理”取代了“疼痛控制”,这意味着对于疼痛患者而言,忍受或者消除疼痛不再是他们的目标,取而代之的是该学会如何和疼痛相处,找回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权。其中最关键的方法,是主动接受更正确和完整的疼痛教育,另外,体育运动、获得人际交往支持同样相当重要。
大众之怕:因“止痛”引发的“上瘾”
大众对于止疼药的恐惧,是被阿片类药物滥用危机所引发的。这是一场在美国延绵了二十多年,仍未结束的危机。2017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发表讲话,强调美国阿片类药物滥用成灾,宣布全国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但几年后,据统计,2020年4月至2021年4月期间,美国药物过量死亡人数仍超过10万,其中大部分死于阿片类药物。
止痛药和上瘾的历史,曾经彼此交缠在一起。整个19世纪,鸦片制剂是治疗受伤引起的急性疼痛和复发性疼痛(如头痛或牙痛)的标准疗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针筒注射剂和咳嗽药海洛因的发明,让年轻的美国人发现了将止痛药压成粉末吸食或者注射能提供无与伦比的多巴胺快感,出于娱乐目的的滥用和上瘾乃至过量死亡发生了。街头上“瘾君子”数量的爆发,让医学界极度担忧,这促成了《哈里森麻醉品法案》(Harrison Narcotic Act.)在1914年颁布。自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阿片类药物被管制。
潘多拉的魔盒被暂时关闭了。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医学界开始对安宁医疗增加重视,阿片类药物成为晚期病人的最终抚慰并获得了世卫组织的承认。之后,美国疼痛协会发起“疼痛,作为第五个生命体征”的运动,倡导人们重视慢性疼痛。1995年,普渡药业所研发生产的奥施康定(OxyContin)经过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的批准正式上市。它被誉为医学上的突破:奥施康定是第一种羟考酮的缓释制剂,据称药效可以达到12小时,被寄予治疗慢性疼痛的众望。
羟考酮,作为在化学结构上接近海洛因的半合成阿片类成分,其效力是吗啡的两倍。这种强大的效力曾经让医生们对其成瘾性非常恐惧,只愿意将其运用于急性的癌症疼痛和临终安宁治疗中。而奥施康定的药效释放缓慢,它的滥用风险被认为会比其他阿片类药物低得多,因此被批准用于慢性疼痛。
“奥施康定药片所提供的延迟吸收机制,被认为能减少药物滥用的风险。”FDA批准普渡药业在药瓶的标签中使用了这行字,而类似的陈述从未出现在之前类似的麻醉类管制药品的说明中。来自官方的“背书”,预示了奥施康定上市后的一帆风顺。作为“重磅”药物,据报道,奥施康定为普渡药业带来了约350亿美元的收入。
然而,奥施康定拉开了阿片类药物危机的黑暗闸门:上世纪90年代末,大量的上瘾和滥用就已经出现。这场危机最先出现在阿巴拉契亚地区。这片地区包括佐治亚州北部、亚拉巴马州北部和密西西比州北部一带,是美国传统的煤矿和林业区,拥有大量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工人们。
阿巴拉契亚地区正是普渡药业拿到FDA“背书”后进军的第一站。普渡从连锁药店、保险公司购买了处方档案,获取了在哪些城镇医生开出了最多止痛药处方的信息,寻找那些贫困程度严重、缺乏教育和机会的社区,资源接近耗竭、有大量受工伤长期折磨的患者的阿巴拉契亚地区无疑正中红心。
一旦确定目标,普渡的医药代表们便会殷勤地去拜访这些乡村医生,说服他们多多开出奥施康定的处方,如《成瘾剂量》中芬尼克斯医生(Dr. Samuel Finnix)所经历的那样,他们会为医生提供免费的餐会派对,以及剧中未提到的数不清的小好处:感恩节的火鸡,甚至给油箱加满油。
奥施康定的效力强,满意度很高,短期处方的价钱也很便宜,这些乡村医生开始相信他们在帮助缓解贫穷的人们的疼痛。很不幸,“奇效”伴随着耐药性而来,从药物依赖再发展到上瘾。后来的政府调查文件中揭露了这种上瘾机制:奥施康定的药效并不能维持宣称的12小时,即使遵医嘱服药的病人也不得不缩小服药间隔,不然就会承受巨大的疼痛感波动,间接使得剂量提高,促使上瘾的风险增高。
普渡发明了“假性成瘾”一词来应对,意即,病症没有根治才让病人仍旧需要药剂,顺势便推出了加大剂量版的药片:从10mg、20mg直到80mg、160mg。
这样的滥用在阿巴拉契亚地区蔓延开来。《成瘾剂量》的原著,《毒瘾:让美国成瘾的毒贩、医生和制药公司》(Dopesick: Dealers, Doctors, and the Drug Company that Addicted America)的作者贝丝·梅西(Beth Macy)写道,她采访的第一个小镇警察说,他很容易在走在街上的镇民们的衬衫上,发现橙色和绿色的污渍。橙色是奥施康定40mg的释缓层的颜色,绿色则是80mg释缓层的颜色。
这些滥用药物的人们将药品含在嘴里来软化释缓层(让人联想起《鱿鱼游戏》中椪糖游戏的小技巧),然后将软化了的释缓层在衬衫上磨蹭掉。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快地一次性获得整片药品能够提供的快感。这些滥用者也学会了将奥施康定研磨成粉并且吸食它——和吸食海洛因的方法异曲同工。
奥施康定成为了“乡村海洛因”。而人们真正认识到这发展成为了一场危机,来自犯罪率的直线上升。在犯罪率相当低的平静小镇上,人们开始抢劫、毁坏公共设施,甚至出现了谋杀。上瘾者闯进了摆放着奥施康定药瓶的房屋,甚至不惜杀死房屋主人。
对奥施康定这类处方阿片类镇痛药的上瘾,很容易升级为毁灭性更高的阿片成瘾,例如海洛因上瘾。根据2014年发表在美国医学会的期刊《精神病学纪要》(JAMA Psychiatry)的一篇论文,75%接受了海洛因戒断治疗的人,是从滥用止痛药开始的。这篇论文也指出,促使人们从处方类阿片类药物转向海洛因的重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后者能提供更强烈的快感体验,而是因为它比处方阿片类药物更容易获得。两者的混合使用,也让死亡更容易发生。
这几乎正是《成瘾剂量》中小镇年轻矿工贝琪(Betsy)悲惨生涯的写照:对奥施康定的上瘾,让她不惜倒卖奥施康定以贩养吸,并在缺乏中开始吸食海洛因,陷入到各种犯罪之中来换取毒品,最终死于过量。现实中,来自墨西哥的毒贩用劣质的容易致死的黑焦油海洛因,接管了“奥施康定地带”,农村白人成为了新的瘾君子群体——在美国记者山姆·昆诺斯(Sam Quinones)的纪实著作《梦瘾:美国阿片类药物泛滥的真相》中有着详尽的记录。
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上瘾”并非是止痛药的原罪。诚然,普渡药业一再隐瞒奥施康定的上瘾和滥用问题确实罪大恶极,但长期慢性疼痛患者的上瘾率并非像故事中那样耸人听闻。2016年,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所长诺拉·沃尔科夫(Nora D. Volkow)在他的论文中指出,当患者得到的适当诊断时,长期服用阿片类药物来治疗慢性疼痛的成瘾率低于 8%。对于晚期患者和一些慢性疼痛患者而言,阿片类药物可能是他们唯一的缓解疼痛的来源。
因此,权威的医学专家们,例如斯坦福大学的疼痛专家肖恩·麦基(Sean Mackey)更担忧的是人们出于恐惧,被“反事实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所统治,不再认为疼痛是一个需要治疗的“真正的问题”,倒退回将忍受痛苦视为理所应当的时代,这无疑是将美国高达一亿的慢性疼痛患者丢入了黑暗之中。
从身体到心灵:疼痛,作为一种系统性疾病
什么是疼痛?
疼痛是一种被世卫组织认可的疾病。世界卫生组织将疼痛列入了国际疾病分类(ICD)之中,并按病程在三个月内外分为了急性疼痛和慢性疼痛。国际疼痛学会目前将疼痛定义为:“疼痛是一种与实际或潜在的组织损伤相关的不愉快的感觉和情绪情感体验,或与此相似的经历”。
事实上,能够认识到痛苦不仅和身体相关,而且和心灵相关,是人类文明进步来之不易的结晶。在人类过去的历史上,无论东西方,表达痛苦和羞耻一直高度关联。在西方,痛苦被认为是一种宗教性质的受难;在东方,忍痛则被认为是一种高尚的美德,关羽“刮骨疗伤”的故事一直被颂扬。
直到近代,人们仍旧对于找不到具体身体病灶,却声称自己疼痛难忍的患者报以高度的怀疑和不屑:一个极端的案例是,1862年,一名美国士兵在铁路事故中被压断了腿,在截去了一小部分肢体后仍旧声称自己有着强烈的疼痛,在找不到病灶的焦虑和怀疑下,当时著名的外科医生们接连把他的腿部往上截肢——一直截到了臀部,最终声称是因为病人渴望鸦片治疗才在装病。
直到关注个体性和个体经验的现代性出现,人们才开始认为,疼痛是个人的体验,为个体减轻痛苦是一种有道德感的行为。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护士西塞莉·桑德斯大力在英国推行晚期安宁治疗,并且建立起了一个示范性的临终关怀机构,用包括强效镇痛剂(“海洛因、吗啡和杜松子酒的混合物”)在内的种种手段帮助病人度过最后一段难熬的时光。
在临床上,人们越发意识到,痛苦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仅包括肉体上的和精神上的,并且和生活质量、社会系统有着密切的联系,以病人个人为中心的“痛苦管理”概念开始出现。找不到具体病灶的慢性疼痛是这一复杂问题的最复杂体现。阅读哈佛大学医学人类学者阿瑟·克莱曼(Arthur Kleinman,有时也译作“凯博文”)基于二十多年临床诊疗经验写作的《疾痛的故事: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一书,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问题。
凯博文认同当时美国社会对慢性疼痛的观点:即慢性疼痛是个重大的大众健康问题,越来越成为导致病残的常见原因。但他在这本出版于1989年的书中,预言了医学对于治疗慢性疼痛是“危险的”:医药行业制造使患者上瘾的麻醉性镇痛药,生产含有严重副作用的复方药剂;医生给患者过度使用昂贵的、且有风险的检测,施行不必要的、会造成严重伤害的手术。他认为这只能让病人对医学产生对立愤慨的情绪,并且挫折而沮丧。
在凯博文看来,躯体化(somatization)是慢性疼痛的主要作用机制。医生之所以难以找到病灶,是因为慢性疼痛更多的是来自于心理动因中的痛苦,投射到躯体之中产生的疼痛。而要理解这一点,必须要全面地了解病人自身的个案,以及他的境况和他所处的社会关系。
凯博文用他的临床案例详细地说明了这一点:他接诊了一位长期腹痛的肄业博士,通过详细的对话式访谈,了解到让这位病人产生痛苦的深层原因,是阶级滑落和身为少数群体的压力。由此凯博文引出了他所理解的慢性疼痛的更深层产生机制:本就在社会中承受了更大压力和缺乏支持系统的弱势群体,不得不承受不公平和无法改变恶劣处境的恶性循环,并对此只能无能为力。
“这些地方场景造成或加深了绝望的感觉,并使这种感觉普遍化,从特定的问题扩展成整个人生,制造痛苦、消沉和绝望。”凯博文写道,“本来由生物性损伤或疾病引起的慢性疼痛症状,因这些不幸的恶性循环而加重和延长。”
所以,他认为要医治慢性疼痛,重要的是要把其当做一种生活方式来研究。因为“对有些慢性疾痛患者来说,疼痛和苦难与生活——尤其是与生活的黑暗和恐惧,并因此加以否定的方面——比之与疾病本身有更大的关系”。医生更需要去倾听和寻找到患者在疼痛背后的人生之痛,改变这种对人生意义不断循环的悲观诠释。
凯博文的观点无疑是极具洞见性的。将近三十年之后,医学专家们发现,一线医生们对于慢性疼痛患者的心灵痛苦的忽略,助长了阿片类药物处方的滥发。2015年,来自华盛顿大学的简·巴兰坦(Jane C. Ballantyne)和马克·沙利文(Mark D. Sullivan)两位医生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一篇题为《慢性疼痛的强度——错误的衡量标准?》(Intensity of Chronic Pain—The Wrong Metric?)的论文指出,降低病人的疼痛强度的评分成为了如今美国医生医治疼痛的主要目标,这直接促进了阿片类止痛药被广泛使用和剂量的不断上升。
而他们质疑,降低病人的疼痛指数,并不一定对病人来说是更好的选择。“疼痛强度评分不一定是慢性疼痛患者的组织损伤或感觉强度的反映。”他们指出,人类(比如运动员)在追求重要目标时可能忍受极度的痛苦,但对于长期经受较小疼痛的慢性疼痛病人而言,疼痛或许是更加难以忍受的,因为持续的无助感和无望感造成的痛苦,可能才是慢性疼痛患者疼痛的根源。
和凯博文的观点一致,这两位医生认为,医生更应该关注病人的心灵痛苦,而非疼痛。更进一步地,他们用神经科学的前瞻研究解释了其生物学机制:疼痛的感觉最初和大脑中“疼痛矩阵”的脑区有关,但之后又会和涉及情感和奖励的脑区有关。随着时间的推移,疼痛的强度与痛觉的联系减少,而与情绪和社会心理因素的联系增加。
这能解释对于既往存在精神健康和药物滥用问题的慢性疼痛患者而言,阿片类药物治疗是让他们最不可能获益的“不良选择”。这些本就有着心理健康问题的患者,很容易长期接受阿片类药物治疗,进而滥用药物,并经历不良药物影响,导致急诊就诊、住院和死亡。
因此,他们也指出,治疗慢性疼痛,最重要的是帮助病人理解痛苦的来源,当病人能够理解痛苦并由之产生的疼痛不再是一种无法战胜的威胁时,病人的焦虑就能减少,并能重新参与有价值的生活活动。“没有什么比病人和临床医生之间的沟通更有说服力和治疗性”,这两位医生鼓励临床医生倾听病人的心声好理解病人的经历,并给予“同情、鼓励、指导和希望”。
但正如前文所述,疼痛作为一种复杂的系统性疾病,更有效的治疗疼痛的方法是真正改善个体所处的社会建构,即凯博文在分析那位肄业博士的慢性疼痛时所指的“地方场景”。在他2008年出版的《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和病痛》一书中,他更精细地解释了为什么在他看来,权利的“地方场景”正是人类苦痛的社会根源——这导致了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大规模的社会政治、经济和生态力量的影响传递的不公平,这让“特定的人群置于了最大的社会压力之下”。在这个由家庭、社会网络、工作和社区组成的多重等级系统中,疾病和精神苦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个体在地方文化系统中的位置,特别是关系网络造成的后果。
虽然凯博文认为精神病学、公共卫生和社会工作的介入,有可能缓减甚至打破这种“地方环境”的恶性循环,即,系统性地治疗个体疼痛,但这种介入最终“必须伴随着社会的变革才能奏效”。
凯博文预见性地指出了人们的疼痛和社会问题之间关联的紧密性。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和妻子安妮·凯斯(Anne Case)在2015年的一篇颇有影响力的论文中提出了“绝望之死”一词。他们发现,除了战争和流行病时期,几十年来全世界人口死亡率一直都在下降,而在这个背景下,美国中年白人的死亡率自1999年就开始急剧上升。
没有大学学历、处于工作年龄的白人男性和女性死于自杀、药物过量和与酒精相关的肝病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美国人口的预期寿命连续三年下降。他们将之称为“绝望之死”,并将其归因为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和工作的不稳定性所造成的社会资本的丧失。迪顿和凯斯也将之和疼痛关联起来,认为这解释了为什么通过数据调查显示,在过去的三十年中,美国的中年白人比其他30个富裕国家中的人们有高得多的疼痛率,并最终为如此多的阿片类药物过量死亡提供了一种解释。
管理疼痛:今天的我们如何和疼痛相处
实际上,在中国疼痛不是矫枉过正的问题,而是一个没有被足够重视的问题。根据《中国疼痛病学发展报告(2020)》,中国慢性疼痛患者超过了3亿人,并以每年1000万至2000万人的速度快速增长。然而,大多数人甚至医生,没有认识到慢性疼痛本身是一种疾病。疼痛医学在中国的发展,尚不足二十年。
在2006年,包括韩济生在内的18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上书中央,呼吁在国内成立疼痛科。次年,卫生部下发了227号文件,符合条件的二级以上医院可以申请增设疼痛科,中国由此有了疼痛医学。然而,时至今日,中国的医院中开设疼痛科的仍旧是凤毛麟角。根据《中国疼痛病学发展报告(2020)》,只有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少数医院开设了单独的疼痛科,占比不足40%。
国际疼痛协会强调,未缓解的疼痛之所以普遍存在,不是因为镇痛技术的缺乏或者落后,而是缺乏完善的疼痛管理体系。也因此,《中国疼痛病学发展报告(2020)》呼吁,要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疼痛管理体系,让疼痛专科可以和其他科室组成医联体,并通过分级诊疗下沉到社区,从疼痛的筛查、诊断、评估、治疗、康复等各方面,对疼痛患者进行全周期的管理。
在国际现有的疼痛管理体系中,对于疼痛的治疗手段也早不限于止痛药的镇痛治疗,从神经阻滞的介入治疗、物理康复、疼痛心理学、瑜伽等补充替代疗法到了自我管理。
疼痛的自我管理,并不意味着自我学会忍受痛苦。忍受痛苦实际上是一个极不利于健康的选择。“持续的疼痛刺激能够引起中枢敏化,中枢敏化后,神经元对于疼痛刺激的感觉阈值降低,使疼痛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增加。”《中国疼痛病学发展报告(2020)》中如此写道。疼痛的自我管理不能帮助疼痛患者消除疼痛,但能够学习管理所面临的痛苦的技能,帮助其过上更有成效、能够正常工作社交的生活,重新找回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权。
前文提到的斯坦福大学的疼痛专家肖恩·麦基,在他代表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撰写美国国家疼痛战略(National Pain Strategy)时,强调了自我疼痛管理可以改善生活质量,因而是急性和慢性疼痛预防和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治疗者的身份从医生更倾向成为了引导者,帮助疼痛患者确定明确的功能性目标,比如重返工作岗位,监督并且帮助他们逐步实现目标。麦基认为这是帮助打破慢性疼痛恶性循环的重要办法,人们就像重新蹒跚学步的孩子一样,了解自己的身体,逐步调整和控制自己在疼痛中部分恢复的能力。
他指出,疼痛教育和健康教育是其中的关键。人们通过学习有关于疼痛和健康的知识,能够更好地了解和接受自己所处的状况,实际感受到的疼痛会变得低得多,同时生活质量也会得到更大的提高。但麦基同时强调了自我疼痛管理不意味着完全排斥药物治疗,而是坚持科学地用药:按时服药,而非只在感到疼痛时服药,后者只会带来身体内“过山车”般的药物水平变化。
运动也是一个帮助管理疼痛的好选择。有研究指出,运动对于缓解疼痛的好处远远超过其他的协助治疗方式,比如按摩和压力管理。和大多数人认知不一样的是,不运动“静养”往往会增强疼痛的敏感性通路,而运动之后往往会立刻带来疼痛感的减轻,并且提高人们所感受到的疼痛的阈值。
人们不需拘泥于具体的运动种类。游泳被很多慢性的关节疼痛患者认为是相当有助于缓解他们的疼痛的,这对于他们的关节相当友好。瑜伽、太极拳也被一些疼痛患者认为是相当有用的。找到合适自己的运动是最重要的。
但注意,必须不要过于心急。对于慢性疼痛患者而言,疼痛容易让人精疲力竭,每天可以用来日常生活的精力带宽会相当受限。正如作家克里斯蒂娜·米塞兰迪诺(Christine Miserandino)为了解释慢性病是如何影响她的日常生活而提出的“勺子理论”,慢性病人一天的精力总量很可能只有12把勺子,小的任务如穿衣服会花去一个勺子,而大的任务如烹饪则会花去三四个勺子,因而必须非常精打细算地使用自己的精力。
所以,对于慢性疼痛病人来说,过度运动意味着透支精力,甚至会增加他们的疼痛。疼痛专家们的建议是,尽量不要运动超过两个小时,也不需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即使是遛狗或者散步都是有益的。
获得更多的人际交往支持也很关键。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精神病学家兼疼痛治疗项目主任迈克尔·克拉克(Michael Clark)指出,大约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三的慢性疼痛患者会经历中度至重度抑郁症。疼痛与抑郁的结合,会让患者更容易经历人际关系的破裂,甚至和亲人的关系也会变得紧张。
对于这些疼痛患者,抗抑郁药是有用的,但专家们更鼓励他们更主动地解开心中障碍,去寻求更多的人际交往支持,甚至是开始一段新的恋爱。由麦基主导的一项研究表明,一段新开始的强烈、热情的爱情关系甚至能像阿片类药物那样调动伏隔核,提供惊人的镇痛效果。
参考书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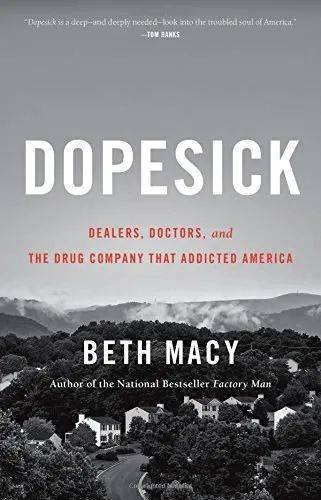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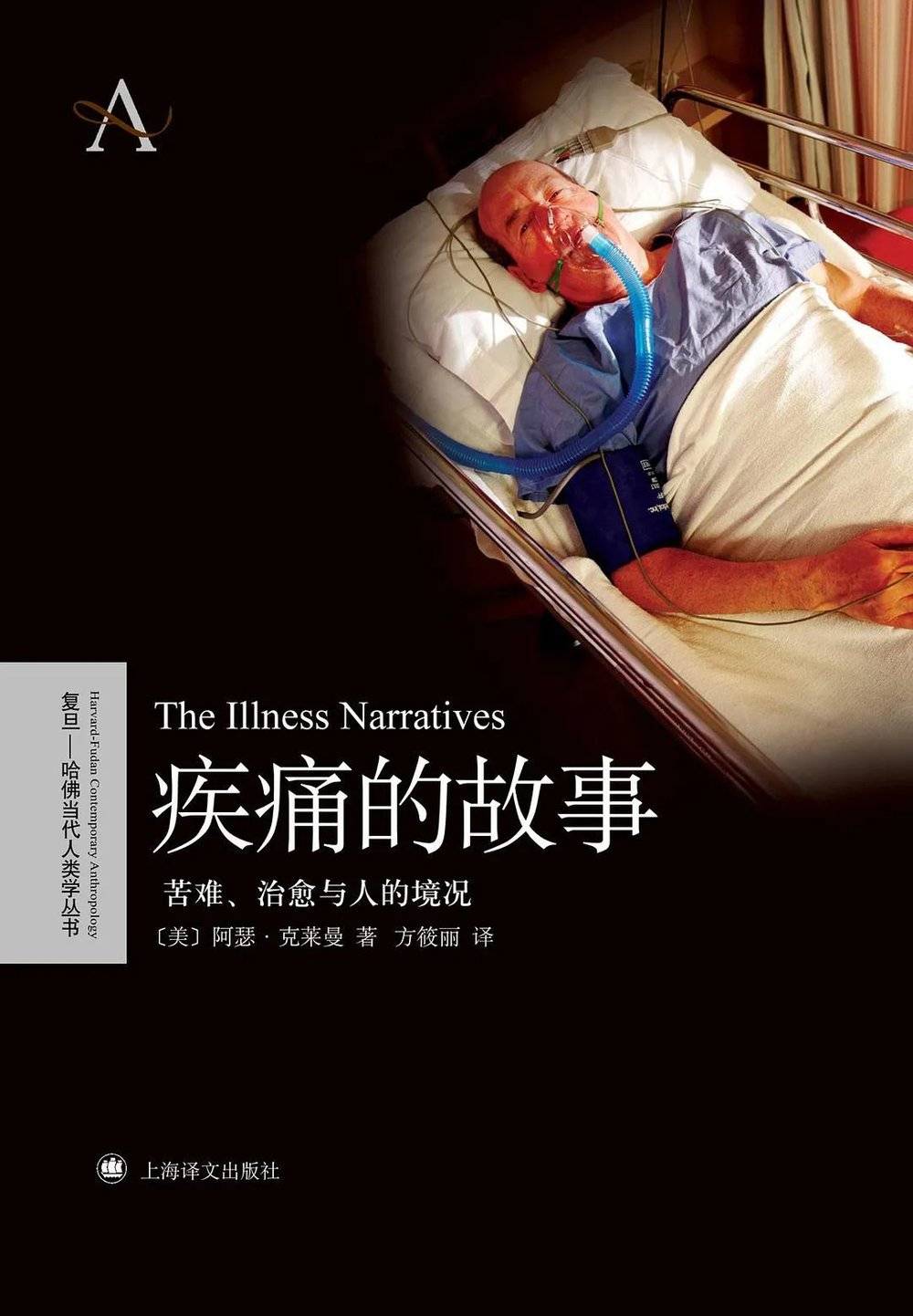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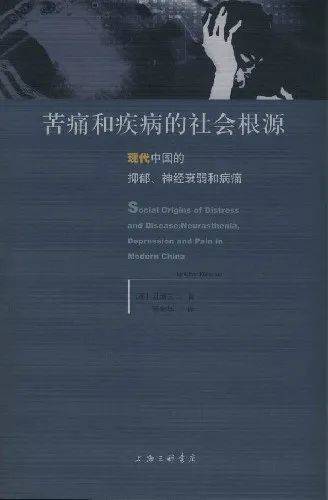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李佩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