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网(ID:eeojjgcw),作者:韩明睿,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有时候,拯救世界的壮举反而会让人爆得恶名。由乐施会(Oxfam)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等组织发起的“人民疫苗联盟”(The People’s Vaccine Alliance)去年公开抨击全球几家药企的共9位高管或投资者靠新冠疫苗牟利而跻身亿万富豪行列。批评者们控诉大药企(Big Pharma)垄断专利,让非洲和印度数以亿计的未接种人群无法以最快速度获得疫苗保护。
这显然不是大企业(Big Business)第一次被指责昧着良心赚钱(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在此之前,类似批评即便在商业气氛浓郁的美国社会也已司空见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伯尼·桑德斯和伊丽莎白·沃伦言必谈大企业和富人的“贪婪”;而在共和党一边,特朗普上台前后一贯宣称,国际化的大企业把本属于美国人的制造业岗位转移到了中国等国家,让几百万美国蓝领陷入了长期失业的困境。而国会中少有的能让两党议员枪口方向一致的监管问题,是限制以脸书为代表的大型社交网络管理其用户的权力。
眼见21世纪第二个十年里大企业遭受的攻击愈演愈烈,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博客“边际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主要作者泰勒·考恩(Tyler Cowen)坐不住了。作为一个有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倾向的反向思考者(contrarian),他决定逆时代潮流而上,写一本赞美大企业的书。2019年,该书正式出版,题为《大企业:给美国反英雄的情书》(Big Business: A Love Lettertoan American AntiHero,反英雄即用反派的手段做类似英雄的事情)。
考恩当然不是说大企业是完美的。毕竟,企业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组成,企业的每个行为说到底也是人的行为。既然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美,企业也就必然有其阴暗面,或力所不能及之处。考恩在自己主持的播客节目“与泰勒对话”(Conversations with Tyler)中每期都有的一个环节,是抛出一些人物或事物的名字,请嘉宾回答他/她认为这些人物或事物是被流俗之见所高估还是低估。考恩想通过本书做到的,其实也就是向读者证明,大企业被他们过分低估了。
低估的偏见可能来自两方面。一是轻视其优点,二是放大其缺陷。就前一个方面来说,大公司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臃肿”、“官僚”、“低效”等说法,就好像它们更容易陷入管理的泥淖。但至少从员工人数来看,公司越大,管理越有效。书中引用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企业的管理质量指标每提高一个标准差,平均来说就会多雇佣268名员工。
另外,大企业的平均工资更高,工作场所条件也更优越。数据表明,最近几十年美国收入不平等程度有所提高,主要驱动力不是各家企业里高层与普通员工收入差距拉大,而是更成功的企业——往往也是大企业——从上到下所有人的收入都随着企业盈利提升而水涨船高,与这些企业之外的同侪拉开了差距。另外,本书出版后也有更新的研究发现,亚马逊等大型零售商主动提高本公司基层员工的最低时薪后,在它们营业地点附近面对相同劳动力市场的公司,也为员工涨了薪。
这些都意味着,如果要改善中低收入者的经济状况,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大企业出现,带动更多的普通员工致富。大企业不仅给的薪水更高,与一些刻板印象相反,它们对员工的管束一般也并不更苛刻。对员工在着装、行为、礼仪乃至8小时外生活方式等各方面提出更多要求的,恰恰是员工持股的合伙企业,如老式投行、律师事务所等。多人持股,则老板无处不在,合伙人的相互监督和对普通员工的监督自然也就更多。
美国大公司也比处于同一社会的大多数其他主体更包容,更善待人。联邦最高法院2015年的判决,在美国全境实现了同性婚姻合法化。而在此之前,《财富》杂志500强中就已有三分之二的企业参照对员工异性配偶的待遇,为同性伴侣也提供健保等方面的福利。大企业也比小公司更不挑剔客户。出于保护品牌价值的动机,它们不希望自己的任何客户群体感到被冒犯。一旦有来自少数群体的顾客受到了明显歧视,就算最终没有闹上法庭,如今的社交网络和媒体环境也会将涉事公司在舆论场中判处死刑,并令其付出惨痛的经济代价。
大企业也更欢迎移民,因为移民可以是它们实际或潜在的员工及顾客。和气生财的道理大家都懂,需要持续吸引人才和客户的大公司尤其如此。这也可以视作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发展:与大公司打交道的人们被平等相待,不完全是出自商人们的良心,更多地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心。
相比之下,本应更能代表公共利益的政治领域却充斥着戾气,政治极化已成顽疾。不仅政客们每天在国会发言席、记者会和推特上彼此攻讦,两党选民也互相觉得对方支持的政策正在祸害国家,其中大多数人甚至不愿意自己的子女与属于另一党派的人士结婚。如果人人都能多学习一点大公司们所秉持的“来的都是客”的宽容精神,社会应该会变得更平和。孟德斯鸠有云:“有商业的地方,习俗必然温良,商业能医治破坏性的偏见。”此言历久弥新。
说到大企业被放大的缺陷这一面,首当其冲的很可能是欺诈的倾向,因为现实中大多数人得知自己被欺骗时都会怒不可遏。大众汽车排放门之类的丑闻让舆论惊呼“你这浓眉大眼的也背叛社会信任了”,并进而给人以“没几个大公司真能靠得住”的印象。但反过来想,排放门等事件让人震惊,恰恰说明其并不常见。消费者在大品牌和小品牌之间,通常还是更信任前者,迫使小品牌必须在价格等方面让步,方可保住生存空间。而消费者的这种习惯并非全然不理性。不管人们是否把“店大欺客”挂在嘴边,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是,要说欺骗顾客的可能性,小杂货店比沃尔玛要大得多,街边摊卖的食物也远比麦当劳更容易让人拉肚子。同样,大公司为了保护自己金贵的品牌价值,会更诚信。
前面说过,企业的行为归根结底是人的行为。所以,企业如果有欺诈倾向,其实是企业中人的欺诈倾向的延伸。企业的每次背信行径都是由具体的人计划并实施。这并不是说,如果出现欺诈,只有自然人应承担责任,企业不能成为责任主体。企业作为法人,当然可以承担法律乃至道德上的责任。不过既然企业作为自然人的联合体,可以有超出其中全部个体的能力和责任,那么也就可以合理地发问,企业将人们聚在麾下,施以规训后,让他们以其名义行事,是比他们散沙一般各行其是时更具欺骗性,还是相反?
回答这个问题,要求我们不能戴着玫瑰色眼镜来看待个人仅代表自己时的欺骗倾向,以为大家只是偶尔为之,无伤大雅。事实上,人骗人是生活日常,且程度堪忧。一份重要研究的估计是,每人每天平均要说两次谎。后续研究进一步表明,人们说谎的对象更多地是亲近的人,而不是关系疏远者。
考恩写道:“我很难找到哪家大公司比我的朋友、家人和关系最近的同事骗我骗得更多。”有多少人在扪心自问之后会不这么认为?也许对朋友和家人说谎在多数情况下并不直接与狭义的个人利益相关,但职场上不做到有一说一,无疑至少部分是出于自利的动机。另有针对人们投出的求职简历所做的研究发现,简历中有31%捏造信息,76%美化事实,59%隐瞒了相关重要信息。企业蒙受不轨的员工和客户造成的经济损失,也丝毫不罕见。
2015年的一项研究估计,即使不考虑批发环节的偷盗行为,前一年度零售业也被雇员和顾客顺走了价值总计320亿美元的商品。个人比公司更值得信赖的直觉,看来只是个迷思。现实中,恰恰是公司会更经常地遭受其员工和顾客这些合作伙伴的欺骗。而如果要继续比较小企业和大公司的诚信度,无须再引书中的例子,从淘宝和亚马逊近来对商户刷单的打击行动中我们已可窥见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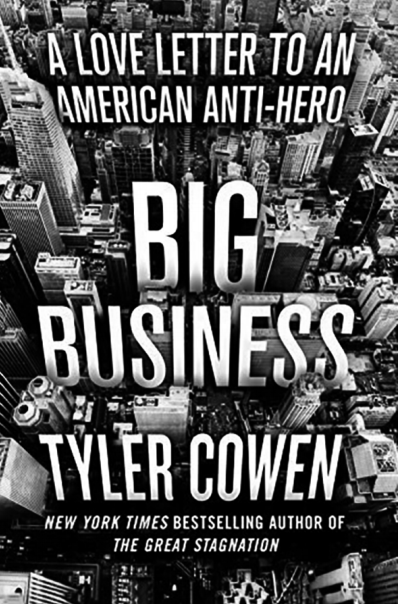
Big Business :A Love Letter to an American Anti-Hero
Tyler Cowen/著 St.Martin's Press/出版 2019年3月
某些社会科学学派的学者喜谈凌驾于个体之上的“结构”和不自然的“社会建构”,也常常批判它们造成了不可欲的结果,或对其中的个体实施了控制乃至压迫。公司当仁不让地属于“社会建构”出来的一种“结构”。但当我们意识到公司以外的个人并非多么可信的善类之后,相反的命题似乎才更能成立:公司,尤其是大公司,作为一种制度结构,在多数情况下尽可能地约束了管理者和员工作为个体最坏的欺骗性,让他们彼此之间以及面对客户,能够存在基本的信任,并互惠合作。
行业头部大企业尤其难以逃过的指控是关于垄断。然而多年以来一直纠缠着反垄断理论的争议是,所考量的市场范围如何客观划定。不妨举一个本书虽未提及,但近年来争讼日盛,屡屡进入大众视野的案例。iPhone用户如果不自行破解手机(越狱),就只能从苹果官方的App Store安装应用。那么,是否可以判定AppStore构成了“iPhone应用市场”这一市场中的垄断,一家的市场集中度就已是100%?
抑或,像苹果CEO库克去年所说的,常用的手机应用都同时有iOS和安卓版,消费者如果不满于App Store的定价策略或权限管理,完全可以使用安卓手机,而从全球范围来看iPhone的智能手机市场份额明显小于安卓系,所以苹果AppStore论市占率只是少数派,离垄断地位还差得远?如果接受前一种逻辑,再把目光从软件转向硬件,似乎也可以说,苹果公司100%地垄断了iPhone的整机硬件市场。不过我们极少见到有人沿着这一逻辑,走向后面这个基本必然会推出,但实在难以让人觉得不荒谬的结论。
甚至有些显然并非同类的产品或服务之间,也会形成竞争。体育馆、电影院、流媒体和社交网络都在争抢人们的休闲时间。每个犹豫过“这周末干点啥”的人都能意识到这一点。这还没有算上旅游景点。当然,这些竞争者彼此的可替代率不是100%,但很明显也不是0。
即便我们认可一些反垄断人士对市场范围多少有些武断的界定,只要把眼光略放长一点,上溯二三十年,就很容易注意到,所谓的垄断优势消散得比他们想象中的要快得多。柯达、IBM、微软、黑莓、雅虎、美国在线等企业都曾被认为有坚不可摧的垄断地位,而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这么谈论它们。无论是由于长成巨头后变得更加官僚,没能预见到新市场的潜力,还是竞争者携着颠覆性的技术进场,这些公司都因为反垄断司法行动之外的原因,失去了当年看似牢固的市场壁垒。
大公司多已公开上市。而上市公司经常被批评为过分看重短期表现以推高股价。在这个问题上,考恩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反向思考精神,试图为“短期主义”一辩。他指出,企业如果更看重短期,很可能不是因为短视,而是由于预见未来实在太过困难,不得不如此。毕竟商业环境瞬息万变。企业领导层对十年或二十年后的市场状况做出预判,并据此自信地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把诸多资源锁定在相应的长远规划中,对大多数企业来说恐怕这才是冒险之举。何况,很多行业特定的固定资产的寿命只有十年左右,甚或更短,届时需要更新换代,而又没有人能准确预测到十年后的行业技术状况。企业因此并没有很好的理由对太过长远的长期有效布局。反过来说,为所谓长期主义所害的事例其实屡见不鲜。
上世纪末美国科技股之所以出现泡沫,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投资者们正确地意识到互联网未来几十年光明可期,但忽略了其中很多公司在中短期并没有足够收入以持续运营。类似地,过去若干年中,一些跨国公司对新兴市场的潜力充满想象并大举进入。但这些第三世界国家不稳定或不健康的营商环境,最终让它们卖掉当初重金投入的资产,黯然退出。总之,企业着眼于短期,往往是理性行为。短期主义被低估,甚至被污名化了。
书中单辟一章讨论金融业。如果一定要给这本书挑刺,最有得挑的就是本章。考恩为了说明金融业的社会效益,用其中一节来强调美国的风险投资体系如何推动技术创新。由风险投资支持的上市公司,市值占整体的20%,研发支出则占44%。医药、生化、信息技术、绿色能源等重要行业,如果少了风险投资,将寸步难行。这些论点没有任何问题。但风险投资基金并不是金融业中大企业的代表,大银行才是。而考恩在这一节中恰恰是用银行的保守来衬托风险投资的活力。本书主角在这里忽然被抢了戏。
银行业当然也与2008年金融危机脱不了干系。尽管复述“贪婪导致危机”之类的道德说教没有必要也没有帮助,然而考恩没有写到但谁也不可否认的是,美国银行业在危机前的几十年中不再着重对工商业放贷,而是大幅加码住房按揭贷款,让房贷与GDP之比在三十年间就从 10%左右蹿升至超过25%,为次贷危机做了完美的铺垫。
不过这一章后文也明智地指出,不能简单地认为大银行之大这一事实本身就不可容忍。大而不能倒(toobigtofail)确实会带来监管成本。但仅仅因为此,就主张把大银行拆分为多个中小型银行,会让本已枝蔓丛生的银行间网络愈加复杂,并迫使美联储等监管机构在危机爆发时监测和应对更多的风险节点,让危机管控更为繁难。大萧条时,美国就是吃了立法保护下小规模单体银行(unit banks)主导银行业却纷纷倒闭的亏。而同时期拥有全国性大银行的加拿大,由于银行分支机构分布广泛,分散和缓解了局部冲击,并未爆发银行危机。
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大企业是否有权力把政治玩弄于股掌之上。企业影响政治的主要手段是游说,每年游说联邦政府的开支约30亿美元。仅仅列出这个金额,似乎已是天文数字,但企业每年的广告开支达到了2000亿美元左右。绝大多数公司每年的游说费用不到25万美元。全部企业花费的30亿美元,只相当于通用汽车公司一年的广告费,且少于宝洁公司每年花在广告上的49亿美元。企业选择宣传影响对象时更侧重政府还是消费者,一目了然。提出寻租理论的经济学大家戈登·图洛克曾经对此迷惑不解,问过一个经典问题:为什么投入美国政治的钱那么少?
不过也许,游说业可以四两拨千斤?并不然。书中引用的两项综合性研究表明,游说没有增加有利于企业的立法通过的概率,也不能让企业得到更多的政府合约,给政治行动委员会(PAC)捐款也起不到什么效果。美国政府的主要开支项目,如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都是因为极受选民欢迎而非由商界推动,才有了如今的惊人规模。企业获得的各种补贴相比之下可以忽略不计。州一级财政与此类似。
在监管方面,美国商人们总是在抱怨监管过于繁重。客观上他们确实也所言不虚,有研究估计监管在一年中造成的经济成本高达4万亿美元。换个角度来看,如果游说的投入产出比很高,企业理性的做法是继续加大投入,直到边际收益递减到无利可图的境地。所以,对图洛克问题一种完全合理的解释是:花钱没多大用处。
跨国公司也很难像传说中那样在随便哪个弱小国家呼风唤雨。的确,外国公司贿赂本国政客的事情时有发生,但每个这样的例子背后,都有更多的外国公司受够了糟糕的司法体系、社会治安和基础设施而离开,还有无数的企业压根就不愿进入。海地就是个贫弱的国家,离美国也足够近,可以说就在美国后院这一势力范围内,但美国公司还是纷纷撤出。美企更愿意在加拿大投资,而不是去海地,或者不丹、喀麦隆,这很说明问题了。
看到这里读者可能会想,行吧,如果大企业这么好,或至少没有很多人以为的那么坏,那为什么它们总是被人嫌厌?考恩的猜想与哈耶克晚年对人们常见的反市场本能的解释几乎相同:大企业(或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是相当晚近的发明,而在此之前数以万年计的历史中,人类生活在家庭、氏族、部落里,在演化过程中形成了高度适应小群体内交往的心智模块,导致现在的人们对大企业(或市场)这种主要由陌生人组成的新生社会结构多少有些无所适从。
同时,演化让人具备将所考虑的对象过度拟人化的倾向,哪怕对象是员工达万人以上的大企业甚至数亿人交互形成的复杂市场,很多人也会觉得与其打交道的结果最终是某一个高高在上的意志有意所为。于是,当大企业的所作所为达不到完美的期望时,就会有人把它当作没能做个好人的个体来批评,乃至于搬出阴谋论,而不去想这是不是给定的资源约束和管理架构下其实并不能轻易改进的现实结果。至于那些过高的期望,很可能是一种节省脑力资源的启发式思维。
例如,普通消费者购物前不会花费精力去思考,既然绝大多数种类的商品出厂时是抽检而非全检,从出厂到入手之间的各环节还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自己总是有一定的概率拿到不完全正常的货品。每天都意识到这些可能性,是生活中不能承受之难,就像为了好好活着,不能在每一刻都沉溺于人之必死的事实一样。
牛津大学学者,著名数据资料网站“数据化我们的世界”(Our World In Data)创始人马克斯·罗瑟(Max Roser)2016年有一句名言:“过去二十年中每一天的媒体头条都应该是‘自昨天以来全世界赤贫人口减少了13万人’。”这句话被史蒂芬·平克在《当下的启蒙》中赞许地引用,以呼吁大家理性看待长时段中世界不断改善的重大趋势,避免过度渲染最新发生的负面新闻,因为后者尽管可能是真实的,但不可能比前者的意义更重要。
与此类似,考恩写道,大企业每一天都基本能满足人们衣食住行各方面绝大部分的需求,并保持大量员工就业,这虽然是它们多数情况下所达到的成就,但媒体不会去报道,而是会紧盯着它们的下一个丑闻。他总结说,对大企业的大多数批评是出于对事实的误解,或对其强加了不合理的判断标准。因此,可以对大企业有一定的怀疑,以促使其自我改进,但不必对它们抱有敌意。
至于文首说到的疫苗,针对其授予专利本就是为了激励制药公司研发。而研发失败的风险不容小觑。2020年加入新冠疫苗研发赛道的有超过一百个竞争者,但只有少数几家成功。如果不允许药厂赚取利润,没有谁会去冒这个风险。历史经验也表明,疫苗的利润率其实比不上治疗性药物。大药企生产新冠疫苗的利润动机可能还不如公关宣传的动机强烈。并且有研究估计,新冠疫苗诞生一年来,预防的死亡人数以百万计。如果说给药企写“情书”在隐喻意义上也略显肉麻,公允地说,它们至少应该得到些更高声的喝彩而非谴责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网(ID:eeojjgcw),作者:韩明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