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风洞VORTEX(ID:ifengdxw),作者:陈直,编辑:措雪,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2021年11月,因为在豆瓣上一个关于海德格尔的冷门小组里透露了自己“农民工”的身份,31岁的陈直出名了。媒体称他为“工厂里的海德格尔”,并开始讨论“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不是一件正常的事”。如今,两个多月过去了,是时候听听陈直自己来讲讲他的人生了。
在独家授权风洞的这篇自述中,陈直回顾说,“对自身处境的惶恐与不安让我走向哲学。”至今,这份惶恐与不安仍然陪伴着他。也始终陪伴着他的哲学思考与艰辛的打工生活。
一、出生
我在1990年代出生于江西赣南山区的一个农村。江西在很多时候被认为是“山清水秀”的地方。我所在的村子就在山谷之中,那里没有多少工业化的影响,依然保留着“古代中国”的样式。实际上,我出生时,我们那里甚至还没有(完全)通电,依然是前现代的中国农村社会。
但这种“山清水秀”在极大程度上也意味着“山穷水尽”——当地农民,除了少数稍富有的人,绝大多数都处在非常贫困的状态之中。农民主要的收入是种植几亩水稻,一年到头就指望着收割后的稻谷换点钱来过活。这是“靠天吃饭”的工作,可能因恶劣的自然天气导致颗粒无收,那样不但赚不到钱,还会倒贴钱。事实是即便在收成最好的时候,也无法赚到什么钱。
那时,由于“改革开放”,沿海地区(比如广东、福建、浙江等)更为发达,有更多就业机会,不少农民开始出去打工。记忆中,我们那里的农民主要去向是广东的汕头、梅州,或者浙江温州等地方,在鞋厂、制衣厂、造纸厂、家具厂等,而很少去后来的“电子厂”打工。打工赚到的钱依然很少,一个月有两三百块钱,甚至更少。
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会出去打工,我父母就没有(除了很短暂的时间)。我并不知道具体原因,但是想来在外面打工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他们宁愿回来种水稻。当20年后我自己出去打工时,我所遭遇的境况似乎也证实了这点,社会在20年中发展了很多,不过对于最底层一些民众的“工作”而言,并没有多少“发展”。
我在当地的农村学校读小学。我家庭贫困,而那时我们小学的学费很贵(以农民的收入来说),因此我时常会欠学费。我经常受到老师以及小学校长的公开“催债”,记得有一次,在早上“升国旗”后,小学校长在全校人面前通知我学费还未交,让我尽快催促家长交钱。
读小学五年级时,我要去乡里的“中心学校”了,并开始住校。住宿以及伙食条件可以说非常差,几十个人挤在一个破败的房间里睡觉。几年后,这些破败的房间被作为“危房”而拆毁。吃饭是自己从家里带米去学校蒸煮,然后吃一到两毛钱的蔬菜(肉肯定是没有的)。上五年级之前,我哀求那个不搭理我、总是责骂我的父亲“在乡里读书不要再欠学费了”。我担忧校长会面向更多的人向我“催债”,让我受到更多羞辱。

说起父亲,我似乎从来都达不到他的“要求”——如果他确实对我有“要求”的话。我小学初中的成绩一直相对来说比较好。如果我考得不好,他就会破口大骂——至于骂的内容是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是我总是会在大骂中强烈恐惧与害怕。
小学三年级时我去县里参加了一次数学竞赛。那是我第一次去县城,也是第一次吃到比较好的饭菜。我现在不记得竞赛考试的内容了,老师也没有告诉我后续的结果,只是发给我一本小型的成语词典,这本小成语词典可能是我小学与初中唯一的“课外书”,也是唯一的词典(我没有《新华字典》等这样的字典)。
二、“起源于惊奇”
也就是大概这个时期,10岁左右?我首次自发地触及到与“哲学”有关的问题。即在某个下午前往学校途中,我突然想到“死亡意味着什么”。亚里士多德说“哲学起源于惊奇(wonder)”,或许亚里士多德的“惊奇”来自于作为有闲阶层的他在闲暇时候的某些惊奇(比如惊奇为什么鸟会飞),但我那时的“惊奇”更多是来自于焦虑、不安、惶恐。我在想,如果生命或者活着对我来说是那么的残酷与无情,那么死亡又意味着什么,生命又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那时我是否想过自杀,但即便想过,也很快就否定了这个想法。
直到我高中毕业或在这之前一段时间,我遇到了第二个与“哲学”有关的问题,那就是身份同一性(self-identity)问题,我也是好像突然问自己:为什么我是我?为什么我不是他?为什么他不是我?为什么我出生于中国而不是美国?为什么我活在现在,而不是科技更发达的未来?为什么我存在(不是生物学的存在,是存在本身存在),而不是不存在?但是我之所以会问这样的问题(大概很多人都曾经有过),也是基于我对于自身处境的惶恐与不安,至少是疑惑或困惑,而不是“有闲阶层的哲学家”那样纯然的“惊奇”。
2008年9月我去了一个二本学校读数学系,但两个月之后,我就开始对数学学习产生了动摇,或者更准确地说,产生对专业学习的“出离”,我不再只读数学。
一开始我是思考数学基础的一些问题,去找了些集合论(set theory)、数理逻辑(mathematical logic)的书看。同时我也开始对心理学的一些问题感到困惑,比如意识是什么,感觉、感知是什么,言语是什么等等。因此我就去找了些心理学、语言学的书看。我同样发现,很多语言学的书是影印版(英文版)的,心理学的书就几乎全是中文版的了,我好像没有在哪个二本学校的图书馆看到过英文版的心理学著作,这或许也表示心理学在中国获得了更大的关注。
然而,最终我还是转向了哲学,或许是因为我越来越感觉到最终的问题还是哲学问题,而不是语言学、数学、心理学的问题,在我转向了哲学后,我就不再关注具体的心理学、语言学这些学科(虽然这两门学科也是在19世纪左右从哲学本身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学科的)。

三、自学哲学以及从大学退学
我记得我看的第一本哲学书是由香港浸会大学哲学教授庞思奋(Stephen R. Palmquist )写的《哲学之树:西方哲学基础教程》。这是一本哲学的导论性书籍,面向哲学初学者的书。尽管如此,这本书我当时也看不太懂,但也不那么难以进入。
在这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主要就是自己在图书馆读哲学书,我越来越对于自己被要求上的课程感到“不耐烦”与“无兴趣”,最终我几乎完全放弃了所有课程的学习(不仅仅是数学,也包括英语课,物理课等),从而也导致我在学校处在非常边缘的状态,我甚至感觉我已经不是那个学校的学生了;这也导致我在学校处于随时可能被开除的状态。
学校图书馆的哲学书并不少,一些主流的哲学书在图书馆都有,我多多少少都翻阅过,包括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甚至日本哲学、印度哲学(主要是佛教哲学)等等,当然我主要还是阅读西方哲学的书。在那一年多时间“自学”哲学的时间里,我主要是读20世纪以前的哲学家,比如黑格尔、亚里士多德、笛卡尔、休谟、康德、费希特、谢林、叔本华等等,尤其是黑格尔的哲学,应该是我读的最多的。
这期间甚至让我走向了“民哲(民间哲学家)”的道路,就是“创造”自己的一套宏观的“理论”。但后期我逐步放弃了,因为我意识到这些东西根本就是不值一提的,是纯粹的胡说八道,哲学没有那么简单。如果哲学那么简单,我就不应该看不懂那些哲学著作,我看不懂恰好说明哲学的深度。我意识到我应该更多地阅读,而不是自己做所谓的“思而不学”活动。
以上就是我在2008年末到2010年9月时的一些关于哲学的自学行为。另外,在日常活动中,由于我从小开始就是那种所谓“内向”的人,所以没有参加过任何的社团活动,甚至我也不知道它们的存在。我与同学的关系也比较生疏。并且当我主要专注于哲学后,我就更加少地与人接触,几乎每天早上起来后就独自去图书馆,然后晚上回到宿舍。这也导致我显得有些被孤立,处于非常边缘的状态,加上我的“内向”性格,总是感到非常压抑。
基于各种原因,尤其是我的考试成绩不及格(甚至有时我没有参与考试),学校在2010年9-10月劝退了我。我自己本身也乐意接受这个结果,因为一来我觉得我不会再受到学校的约束,二来可以从我由于“内向”导致的各种社会交际的压力中解脱出来,三来我认为我可以真正地自学哲学了。
我原计划是退学后回家自学哲学,但是结果可想而知,我无法回家去自学哲学。我出生于农村,没有多少见识,视野比较狭窄,加上我在退学后也只有“高中”学历。因此我只能按照我从小就听闻的打工农民的方式去找工作。我在农村读小学、初中的不少同学就是去城里打工的,我在退学后,马上想到的也是去城里打工。
四、打工
我主要是通过“劳务中介”或者“职业介绍所”找工作。我清楚记得,在找第一个工作时,那个中介老板当众侮辱我为“傻子”,或许我确实看起来是比较“傻”的那种人,“不灵活”,“不机灵”。所以那个老板就随便叫我去了一个工厂,是浙江诸暨市的一个服装厂。那个老板如此侮辱我,我也没有去对骂他,甚至都没有去反驳或离开。我接受了这个工作,因为我那时已山穷水尽,几乎身无分文(这种极度的贫穷在后来十几年中,包括现在都持续地萦绕着我),因此就很急迫地接受了,甚至都没有问清楚工资,工作时间等。
在诸暨市的那个服装厂中,我确实表现的比较“傻”,当其他同时去的人都学会了如何做衣服时,我依然不会,而且还“笨手笨脚”。最终我被辞退了,在那里干了一两个月,最后只拿到500块钱。被辞退后,我再次被介绍进入一个制作方便面桶的工厂,但也很快被辞退了。因为我在晚上加班时接了一个电话,“工头”没有多说什么,就叫我明天不用来了。我没有为自己“辩护”,更没有向他“求情”,更不用说维护自己的工作权利,我那时(并且在未来很长时间内)没有劳动法的意识。干了半个月左右,最后拿了不到400块钱。
离开后,我去了一个快递中转站,那里一般晚上干活,分拣不同的快递,然后装车。但我依然显得比较笨拙,第一天分拣快递时,我搞错了一些快递,让“工头”很快就厌恶我,然后这个“工头”让我干各种很累的事情。几天后,我就提出离职,他直接说“你走吧”,我问“工资哪里拿?”。他说我只干了几天(好像7-8天左右),没有工资。他这么说,我也没有继续跟他说下去了。当他说“没有工资”时,我好像感到一种强烈的悲哀。因为我完全不知道如何才能拿到自己该有的工资。好像他们是“赏赐”工资给我的。第二天我就自己走了。
这个快递中转站的住宿与伙食条件非常差,是我这么多年打工生涯中遇到的最差的那种。住宿是一个有10多个人的房间,很多是中年人,我那时作为一个20岁的“小伙子”非常少见。吃饭是用自己个人的碗(自己购买)去打大锅饭菜。

我从这个快递中转站“离职”后就回家过年了,因为我妈叫我回去,我妈认为即便我再如何“没用”,过年还是要回去的。在2010年退学后的几个工作中,我一直带着我的一个装了很多书的大旅行箱,这些书主要是数学书与哲学书。那时,我似乎不太在意别人发现我读这些书,我甚至会当众拿出书来看。但在后来我竭力去隐藏自己的阅读。
似乎就是在这个时期(即2010年末或2011年初),我发现我变得口吃了,而且在以后的时间里变得越来越严重。在这之前,我虽然普通话说得不太标准,但是没有口吃的现象。这种严重口吃的现象(几乎任何一句话都无法流畅说出来)持续了很多年,直到2020年的7、8月份,我的口吃现象才稍微缓解,2021年以来,我的口吃现象进一步得到缓解,不过并没有彻底消失,即便现在,我有时也会有口吃的现象。
也就是大约有10年时间里,我是严重口吃地在社会中工作与生活的。我的这种严重口吃让我在社会中遭受非常多的困境。比如我主要去工厂打工,但入职时也会有些“面试”,这就需要说话,导致我经常会被拒绝,让我甚至连最底层的工作都无法获得。这种严重口吃也让我遭受到了更多的嘲笑,加剧了我“内向”、“孤僻”、“不合群”的性格,也是我不得不频繁离职、找工作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2011年过完年后,我在58同城找了一个厦门的工作,随后去了义乌,又最终去了北京。原因是我希望能够去国家图书馆。我在网上查到国家图书馆是中国最大的图书馆。如果不是这个原因,我想我不会去北京,因为那里冬天比较寒冷,我从小就惧怕冷。
我在北京通州一个组装电脑的工厂工作。整天站着工作,但是工资高了不少,第一个月拿了接近3000块钱。住宿与伙食条件也都明显好很多。尽管如此,两个月后我还是决定离职,因为我来北京主要是为了可以获得更多的阅读条件,而不是专门打工的。除了每天工作12个小时外,周末最多放一天假,我感到自己的时间太少了。
我看到有不少“日结”的工作,就打算自己租个房以“日结工”来生存,这样可以获得更多的时间来自己阅读。我在北京的时间持续到了2013年初。我那时做的“日结工”主要是在印刷厂,每天的工资七八十或更低,一般也是12小时。我住在通州地下室(或“半地下室”)的房子里,一个月房租三四百块钱。通常每个月工作10多天左右,因此一个月就只能赚到约1000块钱,仅仅能够维持基本生存。
在做“日结工”的这段时间,我阅读了更多的书。在工厂打工期间,由于工作时间长、休息时间很少,而且住集体宿舍,几乎没有看多少书。实际上,在2011年,我都不清楚我对于哲学有多少的阅读。现在回想下,除了在打工外(“打工”对我来说总是次要的、没有太大价值的东西),我都不清楚我还做了什么,因此可以说是“失去的一年”。
从2011年底到2013年初,我主要读了些人类学的著作,尤其是结构主义人类学的著作,也更多读了现象学(比如胡塞尔、舍勒、海德格尔等)的著作。在这时,我已经不再被“读二十世纪哲学的前提是掌握德国古典哲学、英国经验论、欧洲唯理论以及更早的古希腊哲学”这个断言所“禁锢”。虽然这个断言确实也有道理,但是也未必一定要这样,未必一定要完全掌握康德、黑格尔、笛卡尔、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才能阅读海德格尔、胡塞尔等这些二十世纪的哲学家。
我那时对于人类学(Anthropology)的兴趣看起来是比较出乎意外的,因为我在2008年转向哲学之后,对于“具体”的学科,比如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等都没有了多少兴趣。比如康德的“三大批判”,除了《纯粹理性批判》,另外两本《判断力批判》与《实践理性批判》我都没有太多的注意。
那么为什么我那时会对人类学这门学科有浓厚的兴趣(即便现在,我对人类学的兴趣也没有消退,只是由于时间精力的关系,不再阅读人类学的书了)?我想其原因也是出于对“根源”或“本源”的要求。因为人类学(至少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旨在探索原始社会中人的思维与行为及一些“为什么”的问题。我认为对于原始社会中人思维与行为的探索能够挖掘出哲学或思想本身的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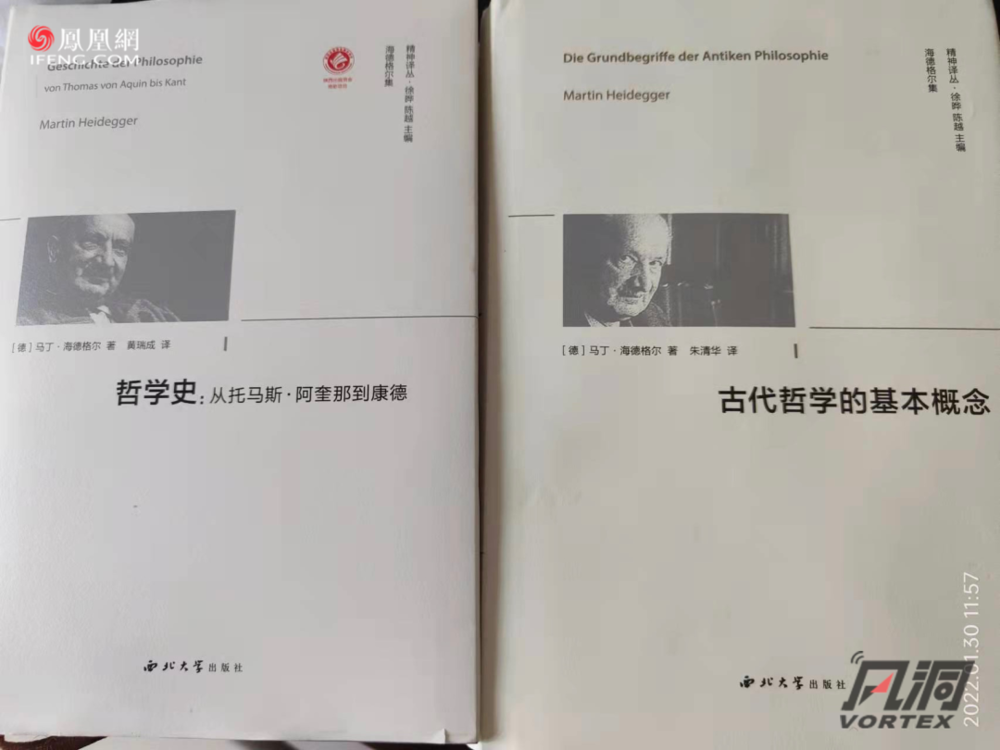
后来我看到一位德国的哲学家Ernst Tugendhat说,人类学应该取代形而上学或存在论来为哲学(以及其他学科)建立基础。这让我感到这位哲学家的看法与我那时对人类学的理解有些类似。
我在这段时间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在读现象学,尤其是胡塞尔的现象学,主要也是读中译本。但是坦诚说,我那时对现象学理解得很有限。比如现象学的口号是“回到事情本身(back to the things themselves)”,“意识的本质是意向性的”,对“本质直观”,“现象学还原”诸如此类的现象学概念与解释,我一头雾水,并没有理解到多少。
2013年过完年后,我去了汕头打工,在汕头一共待了4年左右。在这期间我找过很多不同的工作,但是在汕头我没有找到“日结工”的工作。通常我一个工作只做几个月,主要是因为“口吃”、“不合群”,干久了容易遭到孤立等状况,不得不离职。我会自己租个房子不工作一段时间,主要进行阅读。
从2013年-2017年之间,我并没有非常专注于哲学,如我2021年那样对海德格尔的专注。有段时间我尝试自学编程(主要是Python),但没有成功。我的工资也就2000来块钱左右,无法省钱来报班。
大概2014年开始,我非常希望可以写作哲学论文出来,希望通过发表论文获得一些认可。但我的哲学水平无法让我写作一篇论文出来。除了“内在原因”,我想也有外在原因,比如资料的匮乏,恶劣的生活与经济状况等。持续多年都无法完成论文写作,2017年年末时我感觉非常绝望,对于哲学本身的绝望(对于日常生活,我可以说几乎天天处在绝望的状态)。尤其是我想到自己已读了那么多年的哲学,但是却什么结果或成果都没有,我开始想放弃哲学。在后来3年左右时间里,我几乎完全放弃了哲学。
在这期间另外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是佛教(Buddhism)。2016年左右,我在读黑格尔的哲学中,意识到黑格尔的哲学可能与佛教有些关系。黑格尔说“纯存在是无”,而大乘佛教的核心被认为是“缘起性空”。因此我就简单联想到黑格尔与佛教的关联:他们都谈到了无(或空)这个概念,并且认为是很核心的概念。对于佛教的兴趣可以说至今我都还保留,虽然我现在没有时间精力去读更多佛教的书。
2018年到2020年期间,我主要在江苏无锡、广东深圳(比如富士康等)打工。其中江苏无锡的打工经历是最让我感到痛苦与痛恨的,那是我多年以来最累的工作。在深圳相对而言还好,富士康尽管有些丑闻,却是相对规范的企业,对于我们这样底层的员工来说,这点很重要,可以更具有安全感。这里的“规范”主要是不拖欠工资、不克扣工资、离职容易、旷工也不罚款等等。
2018年到2020年期间,我几乎没有读过任何的纯粹哲学,不过我觉得即便不读哲学了,那么我也应该读点别的书,否则如果单纯厂里打工的话,那么我的个体本身就太缺乏价值。因此这两年之间,我读了不少的英文小说、传记与历史类的在我看来不如哲学那么困难的书。
五、结婚
2018年、2019年这两年可以说是我平生以来读小说最密集的时期,尤其读了不少女性主义小说。比如赛珍珠(Pearl S. Buck)的“土地三部曲”;邝丽莎(Lisa See)的大部分历史小说;基督教小说家 Francine Rivers的几部小说。当然类似丹·布朗(Dan Brown)的那些很紧张、有趣的小说我也读一些。
我结婚是在2020年的春季。关于婚姻,我始终认为我是不可能结婚的,最重要的原因或许是“现实的理由”,也就是我家境条件差,以及我自己也没有赚钱的能力(江西的彩礼是出了名的高,除了彩礼,还需要房子、车子等等这些,这些我都没有),加上我其它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差(“内向”、“不合群”、“口吃”等等)。从非现实层面上说,很多哲学家也都是终生未婚的,比如康德、莱布尼茨、笛卡尔、克尔凯郭尔、尼采、维特根斯坦等等这些几乎所有“西方哲学史”都会谈及的哲学家都未婚,那么我很有理由地确信,我完全可以不用结婚。
但我所在的江西农村对于结婚非常重视,如果一个男人年龄很大都没有结婚,那么不但自己会被周围人看不起,父母也都会被周围人看不起、嘲讽甚至侮辱。当然我父母也不仅仅是因为这方面才急迫我去结婚。
另外的理由包括“传宗接代”的观念,使得我父母很迫切地要求我去结婚,尤其在我30岁这样的年龄。其实我母亲在我23、24岁左右就希望我可以结婚,但我一直都没有同意。在我30岁左右时,母亲对我的婚姻有了强烈的急迫感,她自己本人也被周边的人风言冷语地指摘,别人说她不可能有后代了,会断子绝孙。2020年,我基于对母亲的承诺与愧疚,同意结婚,并且也很快就通过相亲的方式结了婚。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腾讯谷雨的报道中说“ 我也不清楚我们(我和我妻子)之间有没有真正的感情”的原因。我这里指的“真正的感情”是很深厚的感情那种,显然由于这样的相亲式结婚,我们很难有这样的感情。不过我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我也不清楚我们(我和我妻子)之间有没有真正的感情”,但是我和妻子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发生,我们几乎是比较和谐相处的状态。我母亲也经常“耳提面命”地告诫我一定要对我老婆好。
六、从克尔凯郭尔到海德格尔
2021年1月,我重新开始读哲学。最开始我是读了点克尔凯郭尔的书,然后最终还是专注到海德格尔中,可以说,2021年我的几乎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海德格尔上。
关于克尔凯郭尔,虽然早在2008年我可能就翻过他的书,但是我可能直到2012年才粗略读了他的《非此即彼》。在当时克尔凯郭尔的书也是非常少,除了《非此即彼》,还有《重复》,《哲学片段》等等这些,我也粗略读了些。2021初,我在“放弃或遗忘”哲学三年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读他的书。
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2021年我开始意识到需要读英语世界关于他的著作了,而不仅仅是读中文,因此我从网上下载了不少研究克尔凯郭尔的二手文献。
但是在读了克尔凯郭尔不久后,我就转向了海德格尔。至于原因,可能也是感到海德格尔的哲学更深更广,克尔凯郭尔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或者推广为: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而海德格尔的核心问题是“存在问题”。显然海德格尔的问题更为根本、也更为宽广。
2021年5月,我在知乎上发了一篇名为“关于哲学13年”的回忆文章(由于这篇回忆文章有很多隐私信息,因此在11月我受到关注时就把它删除了),那里的主题就是“回顾下我对海德格尔的自学历程”。2021年是我对海德格尔阅读最为集中的时段。
由于海德格尔著作文本的困难程度,因此我是从读二手文献开始。虽然今年我也把《存在与时间》、《哲学论稿》、《林中路》、《路标》以及其他一些海德格尔的中译版原著读了些,但是我对海德格尔的理解主要来源于英语学界对海德格尔的研究。英语学界主流的海德格尔学者的著作或观点,我基本上都读过一些。
或许要说明下我翻译的Richard Polt《海德格尔导论(Heidegger:an Introduction)》这本书以及其它我计划和正在进行的著作翻译,这也是人们所知道的我的主要“工作”。这本书我早在2021年2月15日就获得到了,但那时我也没有去读,只是作为备用(我拥有的几百本关于海德格尔的电子书大部分都是处在“备用”的状态,我读过的只有几十本)。
我第一次读这本书应该在2021年的3月甚至4月左右,读后,我感到这本书清晰易懂,把海德格尔晦涩的概念与思想都用清晰的语言来解释。这本书讲得如此清晰易懂,让我感到有必要把它翻译出来,从而让更多中国的海德格尔初学者更加容易进入到海德格尔的思想中。我在各大网站查找,发现这本书没有中译本,因此在2021年4月中旬左右,就开始翻译这本书。
我原来的计划是半年甚至2021年底能翻译完成就可以。在翻译过程中,我遇到了不少困难,但翻译进度比我原来计划的要快些,在8月底我就把这本书翻译完成了。原来我打算把初译稿自己再重新校对一遍,但在翻译过程中,我也时常感到厌烦,感到翻译耽误了阅读。因为阅读与理解海德格尔对我来说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因此就没有重新校对全书。除非书真的要出版。
虽然我翻译的初衷只是为了分享这本好书,但是在翻译进程中,我也想过出版的问题。甚至想可否把这个翻译作为我哲学初步水平的“证明”。所以初译完成后,我就在豆瓣中找了几个出版社,并且去咨询是否有出版可能,但结果可想而知,我的“咨询”未得到回应。后来我才了解到,哲学翻译的出版一直很困难,更不用说我这个nobody的译作出版了。
后来我打算翻译《海德格尔导论》的作者Richard Polt的另外一本书《时间与创伤(Time and Trauma:Thinking Through Heidegger in the Thirties)》,因为我认为这本书也很不错。在我转到《时间与创伤》的翻译时,我做了如下的解释:“我在2021年7月打算翻译的《剑桥海德格尔辞典》现在看来需要暂停,因为目前我还无法胜任这项翻译。而且这本《辞典》的很多英译术语都与通常的译名不同,这导致我不知道如何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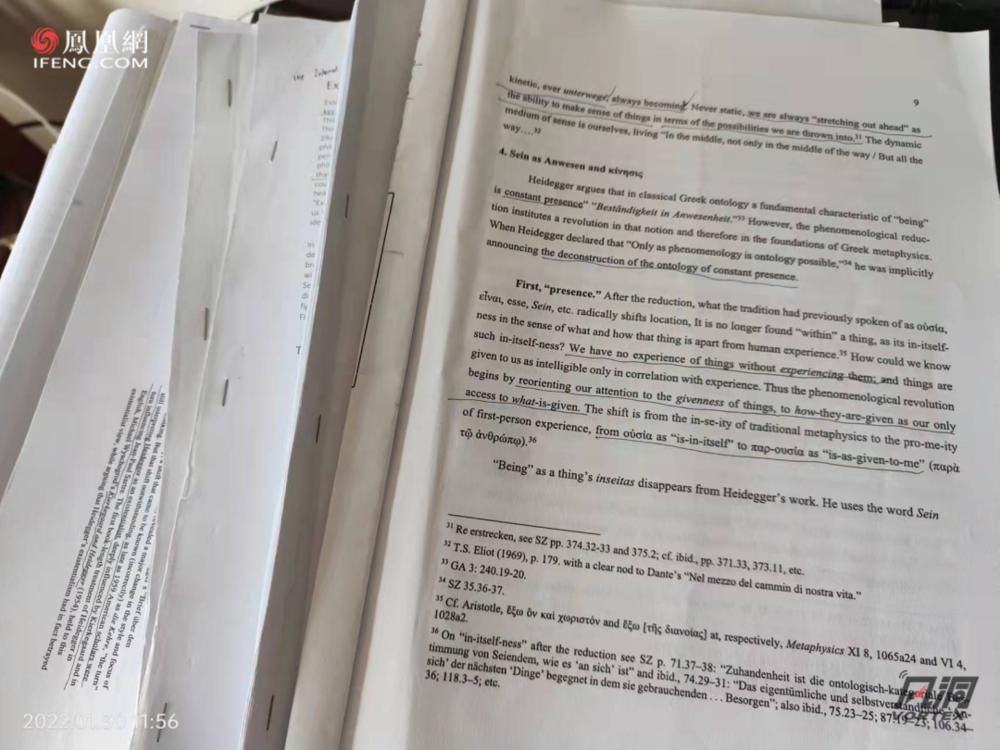
不过在我转到翻译《存在与创伤》的几天后,我就转向另一本书的翻译,从而放弃翻译《时间与创伤》这本书。这另一本书即为《寻找本真性:从克尔凯郭尔到加缪(In search of authenticity: from kierkegaard to camus)》,这本书我在2012年9月底开始翻译,目前翻译进度比较慢,我打算预计在2022年3月份翻译完。之所以最终我选择翻译《寻找本真性(In search of authenticity)》这本书,其原因是这本书在我看来很好地阐述了“本真性”这个概念从克尔凯郭尔以来的研究,而“本真性”是我从那时开始非常重视的一个概念。
七、“出名”
最后谈下我以匿名或化名的方式“出名”这件事情。
2021年11月7日我在豆瓣的“海德格尔小组”发了一个“求助帖”。因为我自己联系出版无望后,希望可以向“海德格尔小组”的网友寻求一些建议或帮助。我在这个“求助帖”上有意识地加上了“农民工”这个词(在这之前,我从未透露过我的“农民工”身份,因为这个身份并不是很好的身份,而且还会引发别人的质疑与否定),因为我想这个身份可能有助于得到“海德格尔小组”的更多的建议或帮助。
没想到,这个“求助帖”在未来几天后获得了很多人的关注。好像有些豆瓣的“大V”转发了我的这个“求助帖”。在后来几天里,有记者来找我,说希望采访我,这完全超出了我的意料之外。我发在这样一个冷门的豆瓣小组的帖子竟然会受到媒体记者的关注,我感到有些“受宠若惊”,因此我就积极回复了这些记者。但是我受到了关注这个事情,我感到有些惶恐,我怕这成为我的一个“丑闻”,因此我希望记者对我匿名。
腾讯谷雨公众号的报道发布出来后,很快就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尤其是哲学学生与学者的关注,有一个哲学系同学对我说“这篇报道在哲学学界引起广泛的谈论”。腾讯的记者也发给我一些哲学教授在他们朋友圈转发这篇腾讯谷雨报道的截图。
在腾讯谷雨报道发出几天后,有不少对于我这个现象的评论文章,好像很多是从社会批判、阶层分析角度来评论我的,我对于这些兴趣不大,因为我更多是关注个体的生存本身,而不是社会层面的一些问题,虽然后者也重要,但是对我来说前者更为重要。
我还是认同亚里士多德说的话,即“哲学起源于惊奇、好奇以及对知识与理解的渴望”。我认为我主要是基于对思想的热忱来学哲学的,而不是其他什么社会层面的原因,比如不是我想进行“社会批判”或想对“技术批判”而去阅读哲学。

同时在互联网的舆论中,除了支持与鼓励我的评论外,还有不少责骂我的评论,尤其是指责我“记不得自己儿子的生日”、“自己请假读哲学,自己老婆天天干活”、“逃避现实、不会赚钱的废物”等等。
有些“女性主义者”对我的指责与批评尤为尖锐,虽然我也自认为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但是那些女性主义者从她们的角度对我的批评、指责让我感到很“难堪”,因为她们的这些批评、指责也是正确的。当然有些“极端”女性主义者对我的辱骂、羞辱让我难以接受,我认为这是对我的恶意批评,是在发泄他们/她们的情绪。
对于那些批评、指责甚至辱骂、羞辱,我当时很恐惧、很焦虑,因此我在自己的豆瓣上既为我自己辩护了一些,但也进行了道歉。我害怕这些对我的辱骂在未来持续下去,甚至更加严重(比如挖掘我更多的隐私,从而让我更加的“出丑”)。但是在那篇报道发出去一个星期左右后,似乎我这个事件的新闻也就冷却了,那些对我的辱骂好像也骂完了。这让我意识到,我在那时的恐惧、担忧与焦虑并没有那么严重。11月末开始,我的这个事件应该就成为一件“往事”了。
我在上面几乎没有谈及我母亲,之所以没有谈及,只是不想把我母亲所遭受的众多困苦(包括我退学后她遭受的周边人的态度转变的痛苦、我不会赚钱带给她的痛苦)刻意地公开出来。我也不想刻意说我母亲对我如何如何的好。我母亲是那种宁愿自己受苦与受罪,也要让家人过得更好的人,对我更是如此。在我遭受所有人的瞧不起之后,唯有她才真正不断地肯定我、关爱我。
自从我去年(2020年)结婚后,我母亲反反复复、不间断地对我说一定要对我妻子好,不能让我妻子如她遭受那样的困境。我自认为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因此我认为我不可能对我妻子不好,我母亲依然反复告诫我,这有时甚至让我感到厌烦。但是事后回想下,她的告诫确实是有道理的,因为她是从她自身的经历来对照她儿媳妇的,她希望她的儿媳妇能够有一个好的丈夫。
或许我还要谈点2021年12月后的一些事情。
腾讯谷雨文章发布后,有一位学校的老师联系我,说可以为我提供一个在学校(高校)的工作。我当时感到非常惊讶,也不太敢相信。因为在我的印象中,高校的工作一般都是要求有博士的学历,而我这样没有学历的人,怎么可能获得在高校工作的机会?但是当这位老师进一步解释时,我才知道,高校也并不仅仅只有教师这么一种工作,高校是一个很大的机构,非教师的工作也有不少。
他说如果我翻译的《海德格尔导论》的译文还不错的话,可以推荐一个合适的工作给我。几天后,他表示可以请我去他所在的学校面试,并且承诺我,即便我面试不成功,交通费、食宿费用也不需要我花钱。因此在12月初,我前往这个位于北方的学校面试。
面试的过程并不复杂,原则上同意了我可以在学校里工作。这个面试结果是超出我的期望的,我在去面试之前,并没有太大的信心会被录用。由于当时还没有签合同,因此我就在学校里自行阅读。这个面试是我在2010年之后首次走进高校,也是第一次走进高校图书馆、教室。这让我感到既陌生又有些熟悉。这个成功的面试让我有更大的机会进行更为持续性的阅读、理解与写作,我很感激这所学校提供给我这样的机会。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风洞VORTEX(ID:ifengdxw),作者:陈直,编辑:措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