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陆续续迎来了七八个年轻好友,
他们大多从北京、杭州等大城市,
搬到山上居住,生活,创作。

有用传统大漆材料做艺术作品的90后雷禺和群生,
做陶艺雕塑的嘉恺把全家都接来了山里,
文文年初刚辞职搬来山居,
何谐和剑斌夫妇已山居数年,
尝试在山里养育自己的下一代。

在后山喝茶的文文、雷禺和群生
相比起在城市,
他们的山居生活成本极低,很少消费。
山的资源让他们可以自给自足,
天暖时一起种菜,天冷时一起砍柴烤火。
开阔安静的空间,
给了他们更多的创作灵感。

一群年轻人在冬日的茶室一起喝茶
12月初,一条来到北峰山,
拜访了其中几位年轻人,
住在同一座山里,
他们常常相聚、互相照顾,
抱团群居,又相互独立。
他们说,这种生活里,
很少会感到焦虑。
编辑 周天澄 责编 陈子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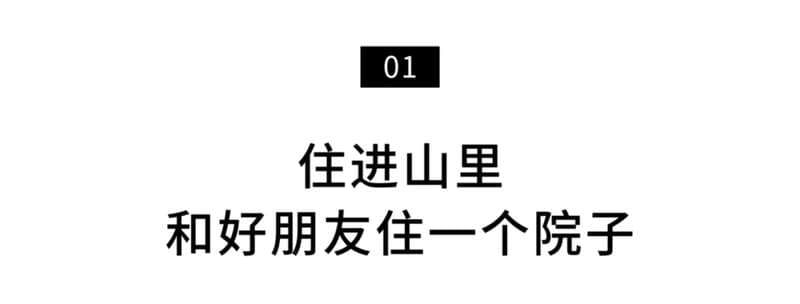
福州北峰山里的冬天,昼夜温差大,四点太阳早早落山,天骤然冷下来。
山里的年轻人们开始张罗着一起去雷禺和群生的院子烤火,他们生起火盆、吃水果、聊天,火势将尽的时候,在炉灰里埋进几个红薯,又在火盆上摆了网架,架了茶壶煮茶。又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山上住了大约八九个这样的年轻人,在这里生活,在这里搞创作。


雷禺、群生在工作室
雷禺和群生是大漆艺术家唐明修的学生,2015年从国美毕业后,就跟着导师到山里生活;


文文辞职后回到山里,和雷禺、群生住在同一个院子里。她新建了一个正对着后山的空间,并修缮改造了自己的工作室
文文是雷禺的朋友,美术学院毕业后,在北京做设计师,2021年初,辞掉了经常10点以后才能到家的工作,清退了租的房子,搬到了山上;


嘉恺的工作室,堆满了他的作品
嘉恺做柴窑、陶艺雕塑创作,原来的工作室面临搬迁,于是带着全家老少上山生活,也建起了自己的工作室;


何谐、剑斌夫妇带着孩子,在山中的旧宅生活
何谐和剑斌是学者何连的女儿女婿,毕业后回到了父亲在山中的旧宅。
九十年代,曾有一批知识分子来到山里生活。唐明修、何连、吕德安,都是当时来到了这里。如今,他们的这些学生、子女,也回来了。

雷禺、群生的工作室在一个山间的老式院子里
雷禺和群生的院子是一个典型的福州老宅。房子是清末的旧居,房东是一个当地的木匠,顾念到他们学艺术,经济并不宽裕,于是以修缮代租金的方式租给了他们。
门前的小花园是他们自己攒起来的,12月头上,绣球已经凋谢,菊花正开得茂盛。除此之外,还有石榴、茶树、美人蕉、蓝雪花,依照不同季节次第开放。


传统建筑的门洞,一朵花开了过来
在山里,打造一个花园完全靠就地取材。他们日常在山里晃悠,看到喜欢的植物,直接挖回来种上。遇到好看平整的石头,收集回来铺成石子路。
南边是工作室,他们把一面墙往外推出去一些,又装上整扇的大落地窗,每天的阳光总是最早从这扇窗进来。
七八点时,这里最是温暖明亮,他们在这里喝茶、开始一天的工作。
工作室的墙面斑驳古朴,也是雷禺和群生刻意保留的“野生”质感。墙面掉漆时,他们找了山里的泥和稻草来补,就是为了接近原生的样子。书柜是房东早年打的,放在这样的墙面前毫不违和。
老宅结构方正,所以每天的阳光会精准地在不同方向移动,他们的行动轨迹也是如此——“光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


雷禺和群生很喜欢福州院落开阔的建筑结构,保留了大部分的主体。中午,他们喜欢在天井晒太阳
中午,阳光从工作室退出来,晒在正中的天井里,他们出来晒太阳。雷禺很喜欢老房子的开阔格局,天井里的桌椅板凳植物都保留了下来;
下午,阳光就会移到另一侧的茶室。于是大家又跟着移动到茶室。


茶室及室内的石头墙,闽地常见的蕨类自由地生长进来
茶室的墙面原本是一块木板,拆掉之后才发现后面是齐齐整整的石头墙。雷禺和群生不加修饰地保留了下来,缝隙之间长出了蕨类,也任其生长。
阁楼被雷禺布置成了一个卧室,又打开了两扇小小的天窗,天窗外的蓝天白云,像是画作。


阁楼及天窗外的风景
“偶尔睡在这里,晚上会听得到猫在房顶走路的声音。早上的阳光会从木板的缝隙透进来,一条条晒在床铺上,好像叫你起床”。
他们院子里养了两只猫,一只叫黑虎,很小的时候从庙里收养回来;另一只叫一十五,是文文从北京带回来的。比起城里的猫,黑虎和一十五的活动范围要大得多。


黑虎和一十五
天井北面是文文的工作室。她回到山里后就来到这个院子,和雷禺群生同住。她修缮并改造了北屋,并新增了一个简单的空间,一面落地窗正对着后山的景色。
后山是个小坡,天气好的时候,她带着各色器皿直接爬上坡去喝茶和看书,两只猫咪有时候也会游荡过来,趴在她身边。
我们到的那天,这个院子里的三个年轻人摩拳擦掌要去嘉恺家蹭饭。

嘉恺在院子里搭了一个玻璃厨房,方便朋友们相聚
嘉恺的妈妈是客家人,热情好客,又有令人赞叹的好手艺,在山里的年轻人里很有声望。
嘉恺住得离雷禺他们非常近,开车不过三五分钟。他家后院宛如一个小农场,养了鸡鸭兔子,又种了菜。雷禺一行人到了以后非常自然地去后院地里拔菜,又熟门熟路送进厨房打理起来。
饭厅在院子里,是个玻璃房子,面积很大,摆着长桌长凳。嘉恺说,因为这些人总是会聚在一起吃饭,所以搭了这个开阔和透明的饭厅。即使天气阴冷的时候,这里也总能聚住有限的光和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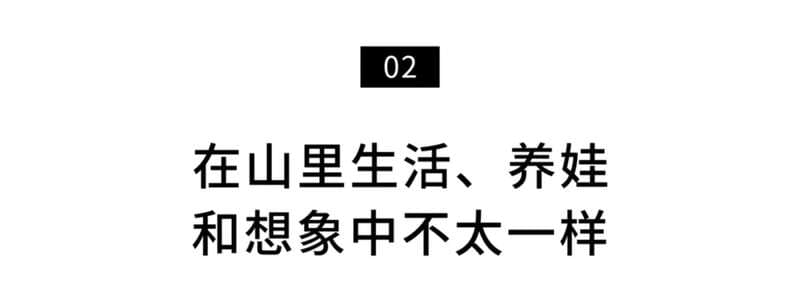

群山掩映中的老宅
何谐和剑斌夫妻俩,带着孩子,住在父亲何连二十年前修建的老宅。
老宅在群山掩映之中,完全和自然融为了一体。初来的人往往会感到惊讶——这座山居没有大门和围墙,对外界毫不设防。何连二十年前种下了两棵拐枣树,现在就长在厨房,穿破房顶,自由地延伸出去。

一棵长在房子中的拐枣树
他们是中国美院的同学,毕业结婚后在杭州工作生活了一年。何谐从小随父亲在山里长大,在不断的商量、磨合后,两人决定一起回到山里生活。
山里还有其他生物。一开始在家里见到蛇,剑斌还会觉得害怕。“现在完全习惯了,可以直接用手抓起来放到野外。”有时还会碰见野猪和山麂,松鼠随时可能闯进他的家里。“就像邻居一样,打个招呼,互不干涉,彼此都有自己在山里的位置”。
住在山里,并不是很多人想象中单纯的“野趣”,也不是隐居避世,而是有很多具体的事情要做。

剑斌在屋顶捡拾拐枣
野草横生的时节要除草,秋冬叶落的时候要洒扫,山里的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节奏,“而且人处理这些的速度很难跟上自然的速度。”土质松动,他们种植树木;山路崎岖,他们自己铺了小路。

何谐剑斌夫妇生活在山景之中
他概括人和山相处的方式,“它有多的(资源),我们可以取一些;它有不足的,我们补充一些。”
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以后,则会感受到山居生活真正美好的部分。譬如落在草叶上的一颗萤火虫发出的微光、石头上经年的青苔、雾气聚起又被风吹散的景象,“不需要刻意去寻找灵感,几乎看到的所有事情天然地就会给人启发。”

对于山居和城市生活之间的区别,文文的感受尤其深。
“在北京几年,总想着可以先工作几年,再去做自己的创作,但在大城市仿佛永远要被推着走,总是不可能停下来。”

文文的空间
到山里后,她发现也不是想象中那么的不方便。这座山里有电、有网、有小饭店、有快递的代收点。“重要的是,在这里,面对的只有自然和自己,就会逐渐意识到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前几年,她和大多数城市社畜一样,每个月将近四分之一的收入用来支付房租。生活在人群里,“不自然地就会买很多香水、衣服,看起来很合群。”
现在住在山里,她的物欲自然而然变低了,衣衫鞋帽够用就可以,化妆品香水这些,更加成了不必要的东西。除了买菜和水电,几乎完全不花钱了。

文文常去雷禺和群生的工作室串门、交流想法
她从北京带回福州家里一大堆行李,真正带上山的只有一个小小的行李箱。靠着这一个小行李箱,已经过完了山里的春天夏天和秋天。
感受到山居的美好后,年轻人开始在山里培育自己的下一代。
何谐夫妇和嘉恺都有了自己的小孩,他们在育儿这件事上观点类似,就是让小孩自由地在山间成长。


剑斌从孩子还不会走路的时候就带去行山,抱着孩子看遍山里的景色。后来孩子会走路了,就任由他自己去探索。山间小路不好走,小孩多有摔打,年轻的父母并不太在意。他们希望孩子是身体健壮、肤色黝黑,在山里跑大的样子。
在山里,“陪小孩玩”的可以有无限种玩法,正如山可以有无限种变化。

秋天,剑斌带孩子去采野果,红色的野覆盆子很酸,但可以做成果酱;黄色的番荔枝味道甜美,据说可以治胃病;在院子落了一地的拐枣甜而微涩,可以用来泡酒。
三四岁的小朋友,对山也有很强的探索欲。有天儿子特别兴奋地对剑斌说“爸爸我带你去探险”,拉着他就往深林里去。那天他们越走越深,捡了满满一篮子的野板栗才回家。

嘉恺本来就学雕塑,对空间很敏感,他觉得小孩需要自由地跑动、感受一些山的高低和空间的错落。“这是天然的美育。”他像是一个大小孩,自己喜欢行山,孩子就像小跟屁虫一样跟着他。“城市里像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盒子:公寓、商场、教室,小孩子长期待在盒子里,怎么快乐呢?”

至于学校的教育,他们都打算让自己的小孩直接在山里的镇上读普通的小学初中。山是天然的屏障,屏蔽了外界的“内卷”焦虑。
“一辈子那么长,更重要的是培养他对世界的好奇,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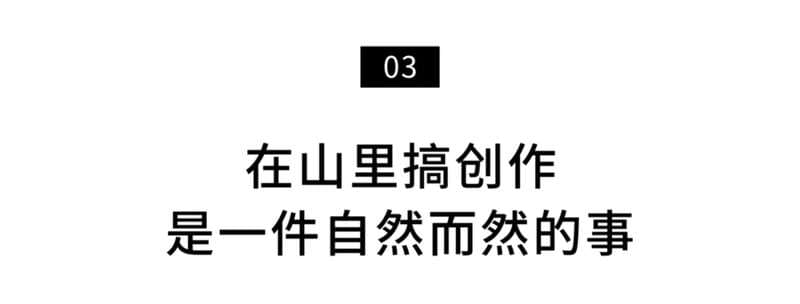
雷禺和群生现在都没有稳定的收入,他们平时接一些创作类的散活儿,时不时也会有经济上吃紧的时候。但因为山里没什么消费,所以焦虑感不会太强。“经常是发现没钱的时候,突然来了个活儿,就又可以支撑一段时间。”这么些年,他们都是这么过来的。


群生作品,他的许多作品灵感都来源于山间的自然万物
他们很早就开始跟着老师唐明修在山里做漆艺,对他们来说,在山里做喜欢的创作,已经是生活本身。
艺术的种子在山里似乎也更适合生长。
山里安静、自然变化多样,人的感受力变得敏锐,“夜深人静的时候,各种创作的想法涌上来,特别过瘾。”


嘉恺把作品陈设在院中,对着远方的山
除了灵感,嘉恺则直接从山里获得创作的材料。他的家整整齐齐垒着大堆的枯竹,是他爸爸去山里砍来给他烧窑用的,做陶用的泥土也来自山里。
他以前在福州城市里做工作室,总是要被各式各样的事情干扰。最后决定上山,是因为当时的工作室面临拆迁——“城市里就是这样,各种变化都太多,也会感觉到自己的边缘化。”
山接纳了他,工作室是他自己建起的,原材料在山里随取随用。“每天都有很多喜欢做的事情可以做,时间是过得很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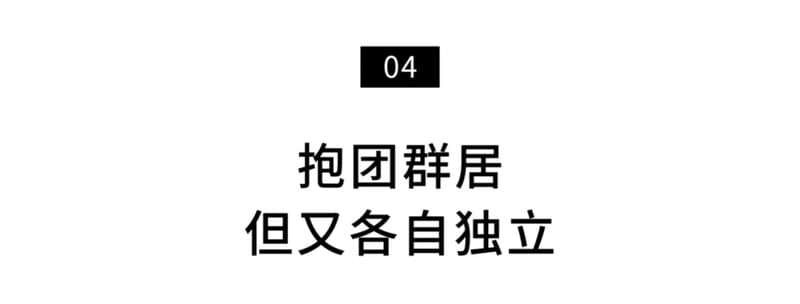

 日常使用的器皿,多是亲手手作
日常使用的器皿,多是亲手手作山里这些年轻人各怀手艺,生活上互通有无。雷禺、群生家里用的各种茶具器皿,形状别致,很多是出自嘉恺的手艺;菜可以从菜地里自己采摘;何谐、剑斌家里炖肉,一次会做很大份量,他每次都分装冻好,分给其他小伙伴。

文文和雷禺在嘉恺家的菜地摘菜
他们年龄相仿,性格投契,住得又近,所以三不五时地就会聚在一起,互相关心、互相照顾。好像兄弟姐妹一样自然。
除了烤火,去“走山”也是日常最受欢迎的项目之一。他们带好马扎、咖啡壶、水果,随时都能出发。


有的路并不好走,不过他们住山久了,个个身手矫健,知道要如何侧身下一个陡坡,又如何小心避开沼泽泥塘。嘉恺对野果兴致高昂,递给我们野猕猴桃:“不很甜但也不酸,这就是山里的味道。”
还有一项活动是打球。一开始,是群生见雷禺身体虚弱,觉得需要强身健体,山里运动条件又有限,于是他买了个篮球。后来队伍逐渐壮大,雷禺和文文都是瘦弱的女孩子,拼抢起来毫不手软。雷禺说,感觉是回到了小孩子的快乐。

这种相处非常随意、自然,文文回忆起自己在北京时,虽然有朋友,但大家在庞大的城市里,其实很难见上一面,“其实未必就不孤独”。
在山上,看起来社交圈子很有限,但她可以很容易地步行着去见朋友。或是路过朋友的家,进去喝杯茶,聊上两句就走。
在这休息的一年里,她很爱去串门,有时候是去雷禺群生的工作室学金缮,有时候是去嘉恺家里“捏泥巴”。其他人也是如此,虽然创作的领域有区分,但是可以互相学习和借鉴。

在面对“是否需要独立空间”时,所有人都毫不犹豫地给出了“是”的答案。工作时,他们很少交流,各自做各自的事情,给自己一块自留地。
“山里这群人,看起来是群居,但其实也是建立了一种默契。在需要独处的时候互不打扰,需要陪伴的时候互相交流。”
群生对于这种状态做出总结:“最重要的是,我们彼此之间都是非常真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