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食通社Foodthink(ID:foodthinkchina),作者:舒泥,编辑:泽恩,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我们平时消费的肉类大部分是工业化集约化饲养的产物。这种模式以“产肉效率”和控制成本为首要目标,把大量动物塞进拥挤的空间集中饲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让动物增重出栏。这种生产方式虽然降低了肉蛋奶的价格,但也造成了其他代价:大量温室气体的排放,动物粪便对环境的污染,激素抗生素的使用对人体健康的威胁等。但是在工业化养殖之外,也存在深刻依附于本地环境与文化、真正可持续的畜牧业生产,它不仅可以为人类提供优质的营养,甚至还能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贡献。
上个月,食通社和X美术馆就以“畜牧业生产和肉食消费”为主题,共同举办了一次线上对谈。我们邀请了在内蒙古草原开展社区工作多年、关心草原环境和牧民生计的自由撰稿人舒泥,分享了她在牧区的观察:为什么游牧是真正可持续的畜牧业?它和工业化养殖有什么区别?牧民们原有的生产方式面临哪些挑战?他们又做出了什么努力来解决问题?
游牧文化对土地和水源的独特看法
不同于工业文化和农耕文化,传统畜牧业以及它所凝练出的游牧文化建立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生产生活都和生态系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首先体现在对待土地的态度上。腾格尔的《蒙古人》里有这样一句歌词:“养育我的这片土地,当我身躯一样爱惜。”而“养育我的土地”在蒙语中的原意其实是“从未被开垦过的土地”,就是说牧民们不希望在土地上修水渠、打田垄,而要让它保持未被开垦的状态。

在内蒙东部靠近大兴安岭的克什克腾旗,当地牧民和林业局就曾因为观念不同,发生了矛盾。林业局认为山坳是植树造林的好地方,就把土地剌开种上了松树苗,希望多植树来改善环境。对此牧民特别接受不了,说这个挖沟机就像从自己的胸膛上开过去一样。他们觉得草甸在山坳里长得好好的,并不需要人工干预。
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对待水的态度也很不一样。前几年我们在中国北方农区做调研时,发现河水基本上是有河皆枯,有水皆污的状态。而草原的情况就不一样,虽然地处干旱区,河水水量不大,但牧区的河流很少断流。
因为在游牧文化中,人们希望水可以自然流淌,觉得河流就像“长生天”(蒙古民族信仰中的最高天神)给大家铺的自来水,一旦断流,下游的人和牲畜就没有水用了。在同样以游牧为主的蒙古国,气候比呼伦贝尔干燥,有一条浅且不宽的克鲁伦河流入呼伦贝尔,它在蒙古国竟然能流1000多公里都不断流,两岸的湿地也发育得很好。

游牧的智慧
很多不了解情况的人会说,游牧是粗放的,靠天吃饭、缺乏管理,而且土地的产权不清。但实际上牧民搬家转场非常符合自然规律,有一套自成体系的应对自然和管理资源的方法。
我在新书《游牧的智慧》里总结了几条游牧的依据。比如:游牧可以适应降水量的时空分布不均。没有哪个地方一直降水多或者一直降水少,各年份之间差异也很大。农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修建水利系统,稳定灌溉水源。但牧区的降水非常有限,没有降水的地方几乎完全干旱,人为修建水利不仅很难滋润干旱区,还会干扰水源,导致湿地枯竭,所以牧民们会优先去雨水好的地方去放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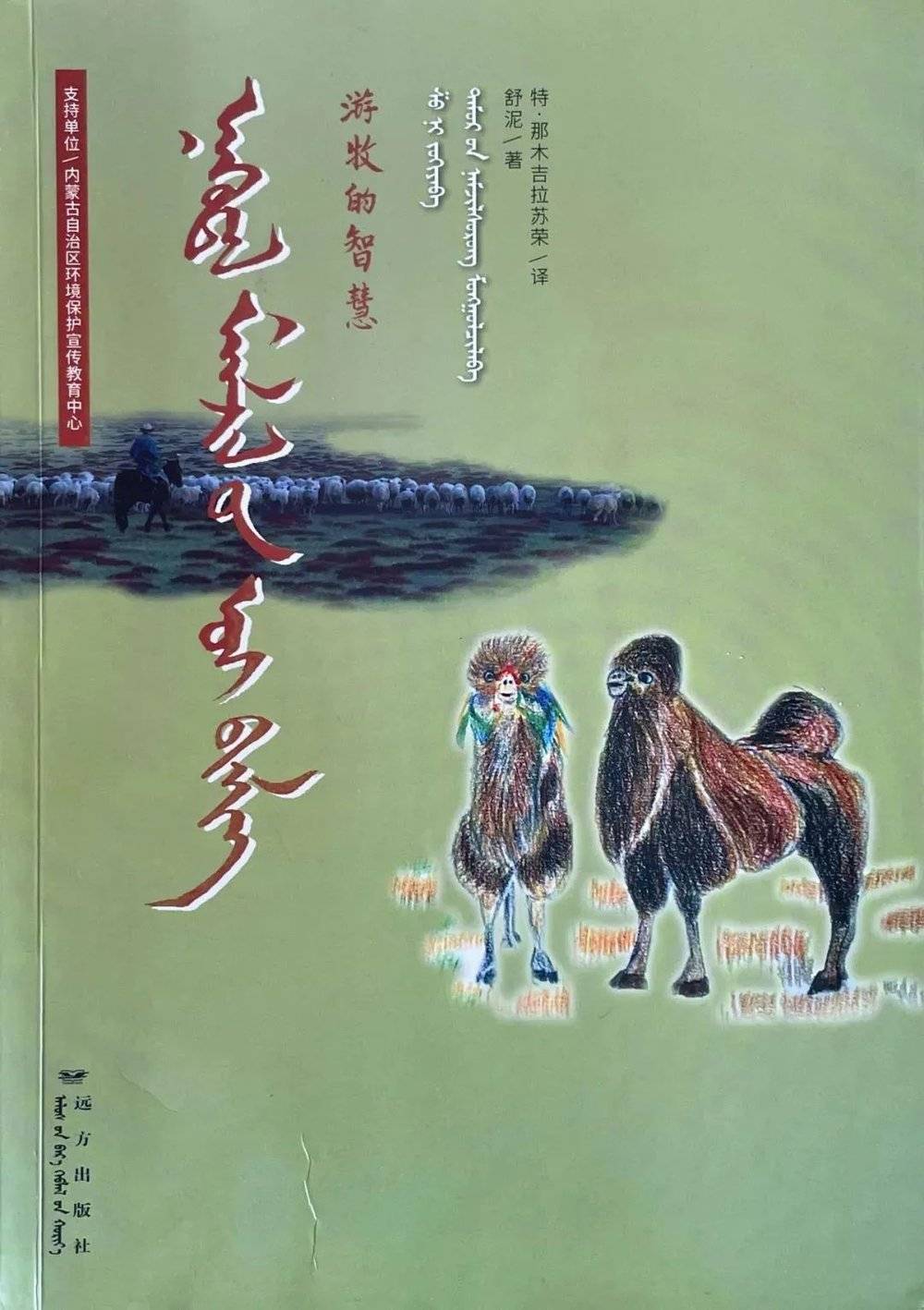
牲畜每个季节需要的养分不一样,需要去不同的地区放牧,因为不同土质和地貌生长的优势植物不一样。除了大多数人熟知的典型草原,和水草丰美的杭盖草原(森林边缘的优质牧场)之外,戈壁滩、沙漠和沙地也是牧民眼中放牧的好去处。后者并不都是环境恶化的结果,也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荒凉贫瘠。


戈壁滩的植被以富含盐碱的小灌木为主,对山羊、骆驼和某些品种的绵羊都是非常好的饲草,比普通的草更有营养,牲畜吃过之后特别上膘,更容易度过寒冬。沙地也和我们通常的理解不一样。虽然和草原在同一个气候带上,但是沙子涵养水源、挡水、存水的能力都比草原强,所以植物的生长量也更丰富,能养活更多的牲畜和牧民。
上世纪90年代,随着内蒙古草畜双承包(草原分片承包,牲畜作价归户)的完成,传统的大规模游牧逐渐转变为围栏内定点放牧,也对草原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举个例子,以往游牧时,牧民会让牲畜固定在一个地方排泄、过夜,粪便踩实后这块地就变成了羊盘。牧民可以从中挖羊粪砖作燃料。羊群搬走以后,剩余的粪便会提供大量的养分帮助恢复草场,从一年生的藜科植物到多年生牧草渐次生长,甚至比没有利用过的草场更加茂盛。

但是定点放牧后,很多羊盘的周围没有时间恢复,变秃的面积会越来越大。因为重复使用同一块草场,本来假以时日就能长出多年生牧草的羊盘,现在只能长出一年生的牧草,秋冬时往往会变成裸地,刮大风的时候就会起沙尘暴。很多沙尘暴就是从定居牧民的家门口刮起来的。
商业资本碾压牧民生计
除了定居,草原上还有另一个深刻变化,就是市场化。随着工业化养殖的发展,牧民在肉制品和奶制品两大产业链中的地位都在急剧下降。
这在养牛的地区尤其明显。现在牧民只负责繁育牛犊,等小牛的骨骼长得差不多了,就拉到育肥厂去统一育肥。在棚圈饲养的条件下,增肥少的传统蒙古牛几乎没有优势,引进的西门塔尔牛的肉量却能在几个月内翻倍增长。

再加上本地畜牧局一直大力推广国外引进品种,很多优质本地种的商业价值还没有被充分发掘,就慢慢地被淘汰了,牧民没法靠卖种畜挣钱了,还要花钱买外面的种畜。
引进品种固然有巨大的商业潜力,但也需要适应当地的环境。一个品种至少需要12年,繁育3代才能稳定下来。但是畜牧局每隔两三年就会推广一个新品种,很容易造成杂交污染,结果是哪个品种的优势都发挥不出来。

另一个例子就是内蒙古知名乳企的发展,沉重地打击了各旗县分散的本地乳制品行业。大乳企通过高价收购低价卖出的方式,垄断了牛奶原料的供应。没有了原料,本地小型乳品厂纷纷倒闭。
之后大乳企又参与订立了行业标准,要求所有乳制品必须在无菌环境中用机器挤牛奶,这减少了大乳企的收奶成本,但这样一来,牧民的牛奶如果要卖到市场上去,就不能再用手工挤奶,而要去有机器的奶站。但居住分散的牧民不可能花一整天时间赶牛去奶站。长此以往,牧民们不再把牛奶卖给乳品企业,原本卖牛奶所得能占到家庭收入的1/3,现在却只能做些奶豆腐供自家吃。

而为了不断提高利润,这两大知名乳企先是把奶源从内蒙古草原搬到了农区,为了进一步降低成本,就再搬到河北、山东这些能稳定提供农业秸秆的省份,后来索性直接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口奶粉或原料奶灌装,完全打断了原有的产业链,减少了牧民的收入来源。
提高现金收入,就能改善牧民生计吗?
不少发展研究和扶贫政策的立足点都是增加牧民的现金收入。举个例子,现在牲畜的出栏率比之前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因为饲草料成本、运输成本增加了,牧民的经济负担反而更重了。有的牧民只卖出7万元牲畜,却要花费3~4万元买饲料。
另外,如果增加现金收入的过程破坏了非现金收入,牧民的生活其实不一定有改善。非现金收入包括良好的生态环境、优质的自产有机食品、根植于游牧文化的传统娱乐和传统智慧等。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这些是“情怀”或者“非刚需”,但牧民是真心实意地喜欢这些,因为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和民族文化,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绝不能轻易地被淘汰。


根据我所在的公益组织天下溪“人与草原”项目多年的调研经验,真正能够帮助牧民的发展项目不需要他们做出很大的改变。比起重新设计一套生产模式,在原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做一些调整,更能改善牧民的生活。
我们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帮助牧民提高市场能力,比如推动牧民和城市消费者的对接。我们在当地的伙伴哈日高壁合作社已经和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合作了5年,在这个过程中,牧民们办起了自己的小型肉食加工厂,学会了羊肉的初加工。这对他们的传统文化还有点挑战,因为城市消费者切羊肉的方法和牧区的方法很不一样。

随着和外界的交流增多,其他商业活动也得到了促进。合作社做了活畜交易市场,打破了当地冷库和肉食加工厂对牲畜收购的垄断。为了让收入来源更多样化,我们和牧民一起开发了深加工产品,比如羊油皂、羊油霜、牛肉干、酸奶糖、传统手工艺品等。这样,牧民对产业链的掌控又往前推进了一环。


天下溪还协助牧民开办了一个游学营,是当地比较成功的第三产业。这个游学营就是本着尽可能不破坏牧民的非现金收入,把一部分非现金收入变现的理念设计的,牧民只要做自己熟悉的传统娱乐和生产项目,就能增加收入。
其实牧区可开发利用的物产资源和人力资源很丰富,但要以牧区牧民为主的思路来开发。比如,我们本着尊重牧区文化的原则来设计项目,即便不会带来显著的增收,牧民也很有积极性。牧民也普遍比较诚信,管理成本不高。牧区独特的文化有助于留住人才,减轻大城市对乡村人才的虹吸效应,在牧区很容易就能找到有头脑能办事的人,我们经常发现去国外留过学的人居然就回家当牧民了。牧民的行动力也特别强,这些都是牧区发展的优势。
如果我们能通过深入的调研,了解牧民的问题和优势,针对实际问题来设计项目,帮助他们把优势发挥出来,那么无论是草原的保护、游牧文化的传承、牧民生计的振兴、还是让消费者吃到真正优质、天然、环保的肉制品,都是很有希望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食通社Foodthink(ID:foodthinkchina),作者:舒泥(自由撰稿人,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法律系,北京天下溪教育咨询机构《人与草原》项目负责人,《中国国家地理》和《美国国家地理》长期撰稿人),编辑:泽恩,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