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Michael Dirda,翻译:林达,编辑:黄月、叶青,头图来自:《沙丘》剧照
1984年春,美国书商协会(ABA)的年会在华盛顿召开。某天傍晚,《图书世界》——当时属于《华盛顿邮报》的独立文学增刊——在位于华盛顿西北区第15大街与L大街交汇处的华邮旧总部(现已拆除)举行了一场鸡尾酒会。正当我(指本文作者Michael Dirda)四处闲逛,竭力摆出一副擅长交际的样子时,我留意到了一位也是独自一人的先生,他看起来颇显疲惫,又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他就是弗兰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我第一时间还没能认出他来,因为他当时刚剃掉了自己标志性的大胡子。
那一刻,我马上就放弃了让自己表现得和蔼亲切的努力。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赫伯特和我就坐在落日的余晖里,谈天说地,但当时还没怎么聊到《沙丘》,因为我俩的谈话总是会绕回到他的好友杰克·万斯(Jack Vance)身上,此人可能是二战后科幻小说领域里最富有想象力的世界构造者(world-builder)。这场交谈令我不禁怀疑:《沙丘》可能部分地出自赫伯特企图挑战万斯的冲动,他细致入微地构想了一个外星文明的方方面面,包括其民众的服饰、文化传统及宗教仪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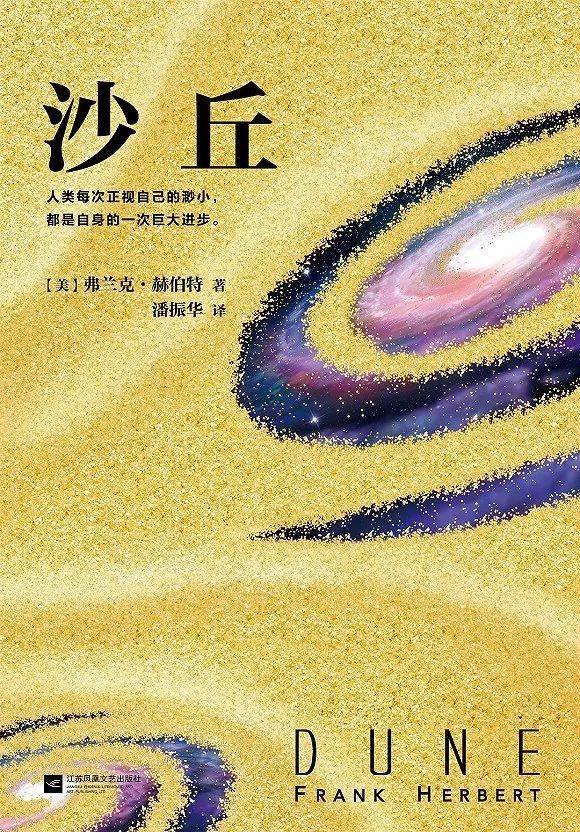
[美]弗兰克·赫伯特 著 潘振华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读客文化 2017-2
对那些完全不懂《沙丘》、对丹尼斯·维伦纽瓦(Denis Villeneuve)拍的新电影以及1965年首发的旧小说均一无所知的人而言,姑且可以这么理解:这个标题指的是沙漠世界阿拉吉斯(Arrakis),该地出产“香料(spice)”,它是一种对空间旅行至为关键的精神类药物,对其供应商来讲则是不可估量的财富之源。小说的情节里——新电影比较忠实地再现了它——包括为阴谋所撕裂的星际帝国、神秘的姐妹会“贝尼·杰瑟里特”(Bene Gesserit)、会以类似于白鲸的姿态从地底深处突然冲出地面的巨大沙虫、精心设计的政治阴谋以及令人震惊的背叛、盼望应许的救世主的原住民弗瑞曼人(Fremen)等等,当然还有饱受怪梦与诡异命运困扰的青年保罗·厄崔迪(Paul Atreides)。归结起来,“正面”角色个个都天赋异禀,有些人拥有巫术一般的精神力量,另一些人则有可媲美武士的战斗技巧,而“负面”角色则大多是猥琐下流的怪物,不是虐待狂就是为贪欲及野心所支配。
1984年时我还是个踌躇满志的青年编辑,没等几个星期,我就打电话给这位新认识的老兄,问他是否愿意为一本书写书评。鉴于当时大卫·林奇(David Lynch)万众期待的电影《沙丘》尚未上映,只在新闻里有过报道,我就让赫伯特写了史蒂芬·金(Stephen King)与彼得·斯特劳布(Peter Straub)合著的《魔符》的书评,这本奇幻小说在当时也颇为出彩并且备受推崇。只让赫伯特来评这本书,算是玩了一个小花招,随后我们在《图书世界》的头版头条发表了他的文章。

1984年12月,我在肯尼迪中心参加了林奇《沙丘》的首映式。活动开始前,参与者的名单就让我觉得既吸引人又不可思议,华盛顿的一线明星与本地科幻小说圈子里这帮不习惯于盛装打扮的人居然混在了一起。然而,在放映结束后,从剧院出来的每个人都面带尴尬。虽有一些礼节性的、稍显克制的赞美之语,但大多数人都认为,这部电影令人困惑、时间过长、脉络不明并且总的来看是一团乱麻。当时《华盛顿邮报》的青年影评人保罗·阿塔纳西奥(Paul Attanasio)——如今已成长为出色的好莱坞电影剧本作家及制片人——的评论即以《沙丘——迷失在尘土中》为题。
好在维伦纽瓦的《沙丘:第一部》(Dune: Part One)收获的反应与此截然不同,我在它于各大影院与HBO Max正式上映前就观看了预告片,发现拍手称赞的观众为数不少。

弗兰克·赫伯特起初只打算把这部巨作写成单卷本,但最终还是分成了三部曲《沙丘》《沙丘救世主》以及《沙丘之子》。维伦纽瓦版电影开头部分的“它开始了(It Begins)”字样令我不由得开始畅想:下一部电影多半会涵盖原作的所有剩余部分,它是就此打住,还是会围绕《沙丘》开发出一个系列,把这个愈发黑暗而复杂的故事继续讲下去?赫伯特的儿子布莱恩和凯文·J·安德森(Kevin J. Anderson,新版《沙丘》的顾问之一)是否还会创作出《沙丘》的诸多续篇或外传?
话说回来,维伦纽瓦的《沙丘》和《星球大战》不同,它并非那种充满热情与希望的太空电影。其基调更接近于瓦格纳式的音乐剧,故事偏向阴沉,不乏与毁灭有关的暗示,配乐上以击鼓声、高亢的哀号与悲鸣为主。但影片带来的视觉冲击力也令人瞠目结舌,特别是酷似机械蜻蜓、速度奇快的小型飞机以及与旧版《毛骨悚然的惊奇故事集》(Thrilling Wonder Stories)的封面如出一辙的、气势恢宏的巨型太空战舰。与赫伯特的书一样,这部电影有意把节奏放得比较庄重,几乎没有幽默元素。生活是真实的,生活是严肃的,没人能有多少乐趣。相应地,剧中人物要么有一种贵族式的高傲,要么在私底下揣测年轻的主角保罗·厄崔迪是否是Kwisatz Haderach(《沙丘》里的神秘姐妹会的语言,意为“缩短道路”,指某种穿越时空的能力——译注),这位应许的战士先知将带领坚强而独立的弗瑞曼人战胜残暴的压迫者。而其中最残暴、最邪恶的敌人哈康连公爵(Baron Harkonnen)则居于黑暗之中,身体四周有烟雾环绕,并统领着一群光头随从,颇具象征意义——这一怪诞形象代表着不受约束、无法无天的资本主义。

众所周知,科幻小说之大谈未来或另一个世界,都不过是表面功夫。实际上,不论是原著还是改编版电影,几乎都总是在含沙射影地批评自身所处的时代。维伦纽瓦的《沙丘》甚至比原著走得更远,触及到了诸如生态学、气候与环境保育、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殖民剥削、毒品文化、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宗教狂热等当代人热议的主题。更加出人意料的是,它还是一曲家庭生活的赞歌,充满柔情地刻画了莱托·厄崔迪(Leto Atreides)公爵对自己已经不再能理解的儿子保罗的爱,以及这位敏感的青年与其出色的母亲、曾受过姐妹会专门训练的妾室杰西卡夫人(Lady Jessica)之间亲密而又偶尔紧张的关系。事实上,杰西卡可以说是这部电影里最鲜活、最迷人的角色。在一个暴乱频仍的世界里,她总是能保持冷静、自律与无畏,并且把这些品质传给了保罗。
电影里最具争议的地方,或许就在于它和当代政治的关联太强了,开篇的弗瑞曼人就身穿飘逸的中东长袍并戴着面纱。保罗在梦中遇见的年轻女子哀叹自己原本美好的故土如何蒙受剥削与战争的蹂躏,她还很像《国家地理杂志》封面上那个有着一双穿透人心的绿眼睛的阿富汗女孩。当弗瑞曼人提到“马赫迪(the Mahdi)”时,任何历史学的学生都会想起那个以此为化名的、拥有超凡魅力的狂热分子,正是此人煽起了19世纪阿拉伯的反英大起义,并引发了后来的喀土穆大屠杀。至于“香料”,大家只要想一想“原油”就行了。这部电影虽然号称以战胜恐惧为卖点,但它所呈现的冲突却很像宗教分子发起的圣战。化用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的话来说,《沙丘》的内核与《伊利亚特》相似,它是一场针对力量(force)本身的全方位沉思。

作为一部小说,《沙丘》所获得的赞誉从来不是无条件的。我认识一些的资深读者、重度科幻小说迷就无法忍受它,认为赫伯特的行文技巧性太差,战争情节太沉闷,整本书晦涩而乏味。但科幻读者本身就比较好斗,争论经常充满火药味,几乎每个领域里广受好评的小说和系列都有论证有力、直言不讳的批评者: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基地》三部曲曾被斥为“一代恶俗”;罗伯特·安森·海因莱因(Robert A. Heinlein)的《星河战队》和《异乡异客》则在鼓吹耀武扬威的沙文主义或某种60年代的自命不凡心态;赛缪尔·德兰尼(Samuel R. Delany)的《代尔格林》(Dhalgren)几乎不堪卒读,而吉恩·沃尔夫(Gene Wolfe)的《新日之书》太过琐碎、神学色彩过浓并且有卖弄机智之嫌。这些批评或许都有其道理。但那些仍然极具争议的、富有想象力的作品——《沙丘》无疑属于这一范畴——仍展现出了经久不衰的活力与相关性。它们依旧是——借用一个时髦的词汇——对话的一部分(part of the conversation)。
本文原载于《华盛顿邮报》,原标题为“‘Dune’ has long divided the science fiction world. The new film won’t change that”,作者Michael Dirda系《风格》杂志书评作者,曾为弗里欧书社出版的《沙丘》撰写序言。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Michael Dird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