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董子琪,编辑:黄月,头图来源:IC photo
当下的文学是否已经放弃讨论公共生活了?文学和公共生活的关系应当是怎样的?
日前,2021年“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在上海举办。在关于“文学与公共生活”的讨论中,我们看到曾经的矿工陈年喜为自己的写作辩护,讲述“江湖写作”的传统由来已久;在二本院校常年处理行政事务的黄灯讲述写作出自内心,她笔下的乡村和课堂确实又与更多人有关;我们也看到基层文学刊物主编吐露编辑不易,有些好稿子约不到,又有些稿子不想要都不行。
文学关注公共生活当然并不意味着对时代热点的肤浅追逐,而应当有更自发的、更深层次的呼应。或如诗人张枣为华莱士·史蒂文斯作序所说的,“世界是一种力量,不仅仅是存在”,世界并不外在于诗歌;生存,这个“堆满意象的垃圾场”,才是诗歌的唯一策源地。
一、陈年喜:我的文学出发点是江湖
陈年喜做过16年的爆破工。2015年之前,从南到北,从东向西,中国所有有矿山的地方他都到过。在工作坊发言时,他说自己有很严重的职业病,难免会咳嗽,请大家谅解。“我的人生真的很跌宕,我本人真的很江湖,我的写作也是很江湖的。”
陈年喜在《炸裂志》里记录了黑暗深处的开矿生活:“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我微小的亲人远在商山脚下/他们有病身体落满灰尘”。他自认并不特殊,因为中国传统写作也是很江湖的,“古代的作家诗人也是该骑马骑马,该打仗打仗,该流浪江湖的流浪江湖,他们的文学的出发点就是江湖。”
他所理解的公共生活不是热点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公共生活,“你经历的那个生活就是你的公共生活,每个人都可以写出自己在场的、知道的、经历的生活,组成的是一个时代的景象图。而这其实是文学非常需要的,不全然是书斋的形态。”
陈年喜还对当代诗歌作出点评,认为如果将当代诗歌放在历史格局当中,会发现它是“相当弱的”。过去人们从风雅颂的风的部分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爱恨情仇,从杜甫的“三吏三别”里能够看到中唐安史之乱的凋敝;回过头来看当下的诗歌,虽然创作手法更加丰富,但从内容和与时代结合的方面来说还是比较弱的。
“一般人对历史的认识是从诗歌和文学作品开始的,很多人难以接触到严肃系统的史料,而从当代作品回看这个时代,很多东西都看不到。看到的是秋天来了、春天来了这样一些和生活不是太相关的描写。诗歌需要时代的氛围和尺度的开放——像是文学刊物的开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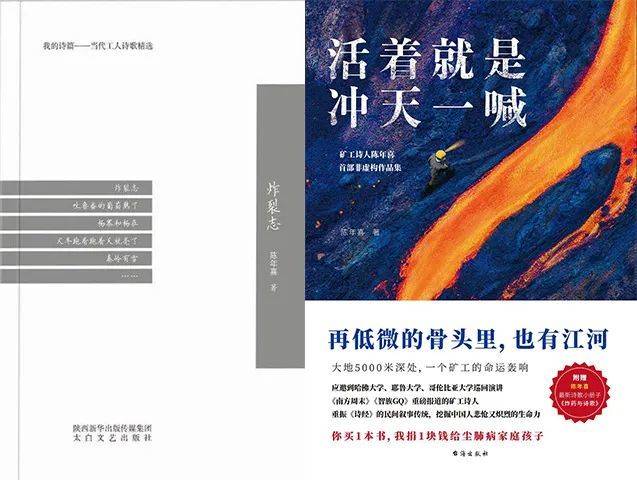
目前陈年喜已经告别矿工身份,从2017年起,他到贵州一家旅游景区做文案,每天8小时坐班,工作就是负责写各种软文以及领导发言。那时候他的工作量不大,两三天才有一篇,大部分坐班时间都很无聊,就开始写自己的人生经历、工友的生活还有家乡的事情。
一方面觉得自己的人生经历应该有更多人知晓,让人知道有一群人在这样生活;另一方面更多考虑的是收入问题,贵州那家单位开给他的工资是包年5万块。
他希望这个时代能给非虚构文学一些场地,(作者)能有更多的空间写作。“非虚构之所以兴起。”陈年喜说,“是因为我们在许多文学作品里很难读到真相和世道人心。”
二、黄灯:个体故事可以为更多沉默的人赋权
黄灯已经离开了写作《我的二本学生》时所在的广东F学院,目前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教书。
有人评价黄灯的写作是“刚好找到了一个阐述底层的点”,她觉得这个点并不是自己刻意找到的,生活本就如此,家里就是有那么多农村亲戚,天天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学生。一次在北京开会,有人跟她说“你真会选IP”,她听了觉得非常生气,“这也太小看自动的写作者了。”
所谓“自动的写作”,就是完全由自身驱动的写作,是缺少明确目的性的写作。以《二本学生》为例,黄灯教了十四五年书,教过四五千个学生,每次上课都是上百人,黑压压一片,这么多年来也经常被学生当成“垃圾桶”——她没有主动去做过田野调查,是田野调查找到了她。
黄灯说自己不喜欢生硬地介入现实,或是以体验生活的名义去到特定的场所,“现在动不动就体验生活,作家要跑到农村扶贫的地方体验生活,就很怪异,这种创作像被绑架了。”
不管是书写亲人还是记录学生,这类写作带来的麻烦都多过名利的好处。事实上,她离开F学院也与写作惹出的麻烦有关。黄灯在那所学校待了14年,也做了13年的行政官员,每天被行政事务环绕,最忙的时候一天要开七八场会,连消防事务都要过问一番。在这样的情形下,她认为自己写作中内在的紧张性与反抗性不能通过任何学术或行政评价体系表达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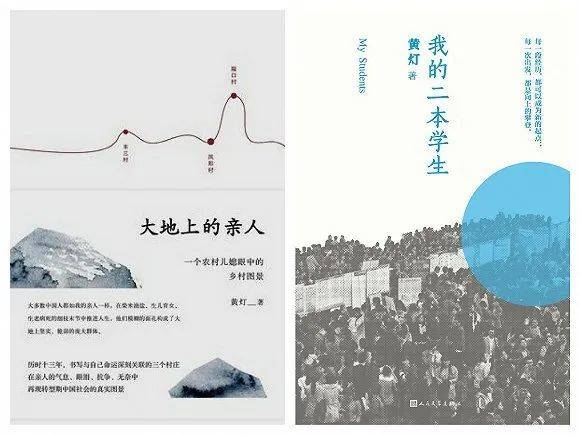
“我真的是一个学者,”黄灯向与会者强调,她受过的理论训练让她可以从现代化、殖民主义、女性主义之类“冠冕堂皇”的话语里轻易地辨别出同类的气息,“在那个理论体系里,如果‘说人话’,大家会认为你没水平,你的论文会被拍死掉。”
在发现学术这条路差不多被堵死之后,她转而开始寻找一种在理论语言和论文之外的写作,要将自己剥得干干净净,要做个老老实实的人,所有的人物都要有真凭实据。
2016年春节期间引发关注的《一个农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是一篇约稿,在此之后,黄灯用40多天在图书馆的一张桌子上完成了《大地上的亲人》,这部书也让她的写作进入公共视线,她丈夫的农村家人的生活成为了所有人都能看到的公共故事。
黄灯在工作坊的发言中提到,“在《一个农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发表之前,我给我老公写邮件,因为这篇文章写的是他家里的事情,好歹要经过当事人同意。他一个星期没有回复我,没有赞同也没有反对。后来我问他,这个事情很多人很忌讳吧,尤其男的,一个女的把家里事情写出来怎么样。他说,这不是写我家里的事情,其实农村很多家庭都是这样。我们农村很多老人过得很艰难。”
个人经验在很多时候可以跟公共经验对接,黄灯认为,至于对接的点在哪里,取决于个人经验如何书写,是写自己的事情,还是以自己作为某一类型群体或者阶层的代表。她说,自己所处的“70后”群体跟中国转型期完全同步,见证了当代中国的每一次重要改革,“我自己身上就有好多改革措施,”所以,个人的事情也同样是公共的事情。
三、是追随还是淡出?文学与公共生活应距离多远
陈年喜形容自己的写作是江湖的,向人们道出这个时代有这样一群人在生活;黄灯说《二本学生》是对《大地上的亲人》里“那些农村的孩子读了书会怎样的”的回应,告诉人们农村孩子并不比城里的笨,虽然他们就算考上大学也不一定是985和211。
复旦大学青年副研究员康凌对陈年喜和黄灯的发言做出回应认为,这二位写作者的文学公共性,出自他们对追随热点的大众性的抵抗,这样的文章就像鲁迅写作《狂人日记》不仅仅是出于外在的触动,而是在长期的自我对话的状态里,通过内在的经验抵抗所谓的“公共关怀”。康凌并不赞成评论家抽着小皮鞭激励作家书写“重大题材”的行为,认为这是一种文学追随公共生活的不健康的状态。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谈到了对“附近的人”的田野调查。在距离清华20分钟车程的高档小区里,他认识了一个年轻的保安,保安喜欢读诗,像是打工诗人许立志的诗,也喜欢写诗,还参与了皮村文学小组。高档小区里豢养着白色孔雀,在小区路上自由行走,他们聊天时白孔雀正在鸣叫。
评论家黄德海则对近年来一些同行鼓励工人写作的行动表示怀疑,“我想问,鼓励他们写作,把他们的情感锻炼敏锐了,把他们的文字锻炼得更好了,他们接下来怎么办?他们感受的痛苦更剧烈了,谁给他提供平台解决问题?”
此外,黄德海认为,文学对公共生活相对地淡出是对文学的保护,这并不是说文学不应该和公共生活有关,而是说写作与生活有关必须出自感受最深的一部分,是扩展公共生活的某一点,而不是和公共生活建立起过于友好或同谋的关系。“一个诗人只有在写作的时候是和写作有关,如果干预公共生活,请不要以诗人的身份。文学家有时候在室内太久了,根本不知道公共生活的复杂性。” 他补充说。
可能是出于对公众评价文学标准的质疑,作家路内在现场朗诵了一段未发表的小说,主要内容是某作家在豆瓣上遭遇一个女性大V差评,由于大V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又引来众多粉丝差评,他的新书评分瞬间跌破6分,作家开始对恶评进行逐条反击,形成网络混战。作家对这位大V的恶评也十分有趣,形容她是“一手端着纽约客的香槟,一手捧着2万V的盒饭”。
与对外部生活充满疑虑的态度不同,一些评论者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评论家方岩在谈论文学与公共性的时候感到羞愧无比,因为这样谈论的时候“是缺什么才谈什么”,而这样的公共性的匮乏不是外部环境造成的,而是自己造成的。他认为,从80年代末到现在,文学批评界对自己一共进行了三次手术——第一次是纯文学概念,第二是人文精神大讨论,第三是学院化,“这三个手术基本上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的三块遮羞布,是三次自我阉割与自我限制,我们把自己逼到一个角落里,身上所有复杂的、丰富的东西全部格式化了。我们如果不反省作为评论者和研究者加在自己身上的种种枷锁和限制,谈文学公共性怎么都是死路一条。”
该场论坛的主持人、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项静表示了对“三次阉割”的异议,她认为,西方的文学也没有做三次阉割,但他们也跟我们差不多,处于一种对没有足够参与公共事件的自我贬抑中。
巴金故居的常务副馆长周立民也赞同冒犯的文学,但让他不满意的是,现在冒犯的小说越来越少了,好像小说家的美学原则过滤掉了公共性,公共社会中最重要的事件在文学作品里的呈现,成为了最隐秘的部分或最简单的背景。“2020年全球疫情是全世界的大事,是人类历史的大事,到现在为止,我们只能赞扬医生护士吗?”
周立民的反思针对的是当下文学生态,认为这是一种被驯养的文学,一方面文学生态受到资本的控制,资本虽然不会冒犯公共性,但会制造虚假的生活以扩大和增值,这样的文学生产首先以盈利为目的,“余华《文城》的试读本,一上来就有那么多评论,这是没有资本的普通作家能够做到的吗?”另一方面,评奖机制也增强了创作的统一性,“你看到的评委永远是那些人,一个作家永远在得各种文学奖,就知道文学不需要个性,也不要侧重点,只需要附和奖项的尺度。”
就连曾经野蛮生长的网络文学也面临着收编与规训,周立民点评道,这会让越来越多趣味趋同的、没有个性的文学出现,“现在网络文学作家都可以评职称了,不是说网络作家不优秀,而是说,职称原来规范的对象是谁呢?过去可以野蛮生长的芜杂之地也逐渐消失了。”
四、是观察还是影响:专业文学如何面对基层文学?
周立民发现,自己所在的巴金故居正在成为热门的打卡点。据统计,巴金故居在2019年共有37万人次前来参观,很多拍照留念的人并没有看过巴金,也不在乎巴金写了什么。除了巴金故居副馆长的身份,周立民也主编内部刊物《杨树浦文艺》——这本刊物被金理称为“基层文学刊物”,目前已经出了70期,由杨浦区作协主办。
周立民向与会者强调,很多读者不会像我们接受过文学教育的人这样理解文学,他们觉得有词语的感觉就是文学,所以更需要理解这些普通的文学爱好者或者说基层文学人士。
《杨树浦文艺》只能办到50%的水平,周立民说,因为这是一份区级作协刊物,他想要跟作家约稿,作家不肯把最好的小说给他,他还要说服人家这是内印刊物,才印2000份,还都全是送的。另一方面,他还要经常与一些不想发的稿子作斗争,有的投稿人甚至堵到了认识的文学教授,“人家跟我说你赶紧给他发了,你的刊物又不是什么像样的刊物。”
杨浦区作协有150个成员,这两年的问题是招不到年轻的会员,而有的会员老先生已经出了几十本书。上海作协也有类似的情况,“大概十几年前他们做过一个统计,里面的中青年占到20%以下。”
基层文学与专业文学的关系应当是怎样的?基层文学难道仅仅是被观察的甚至猎奇的对象吗?
周立民试图沟通两类文学的关联:文学本质上就是自我发泄和自娱自乐,有的人写作有几百万字,对他个人也是有价值的;从社会性方面来说,基层文学作者也是经典文学的忠实读者,对文学的热爱远远超乎想象——用他的话说,“评不上区作协会员也会着急。”
此外,基层文学作者对文学的看法可能会影响公众,因此文学专业人士需要认识到这些并不在自己世界里的人,如何改变他们的文学趣味会成为影响公众文学趣味的关键一环。

严飞也分享了自己生活中所见的文学爱好者。他认为社会学家做田野调查,需要呈现出这些受访者的个性与生命力,余华《文城》里描写人物的段落同样可以用来想象保安和保洁。
两年前,一位装窗户工人到严飞家干活,他的儿子当时读高三,处于迷茫期,工人请严飞加了自己孩子的微信聊两句。高考落榜后,少年来到北京,和父亲一样做上了装窗户的活计。他告诉严飞自己喜欢读书,尤其是加缪的《异乡人》(即《局外人》),因为觉得自己就是北京的“异乡人”。
作家郭爽也提到,自己的表弟在贵州偏远县镇做公务员,她去实地探访才发现,表弟在房间墙角摆了一个长条板凳,上面放了很多书。她此前从没想过,工科出身、在县镇做公务员的表弟会这么喜欢阅读。表弟还安排一些小青年带她骑摩托车出去玩,那些小青年只有初中文化水平或是更低,一般靠打散工过活,他们将郭爽看成了不起的“文化人”,跟她交流心得。他们问,“姐,你有没有看过《大象席地而坐》?”郭爽说没看过,对方说,“我看了三遍,觉得很牛。”
面对这些青年,郭爽想起自己认识的那些互联网“新贵”所说的话:最厉害的互联网产品不是在赚钱,而是在争夺时间,当所有人都被游戏或短视频占据的时候,就没有人会看书和电影。她只想对这些自信的“新贵”说,“去你的,有些时间不能也不会被夺走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董子琪,编辑:黄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