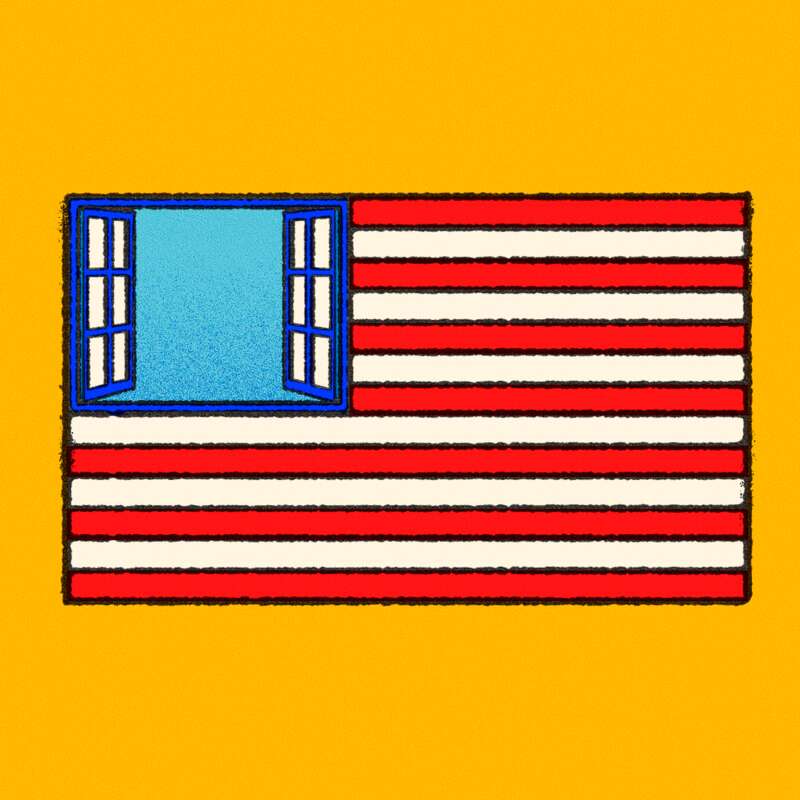
ALBERTO MIRANDA
以下是我的书《最孤独的美国人》(The Loneliest Americans)的节选,该书于10月12日出版。(本周时报杂志上也发表了一篇节选。)这本书是我对1965年移民法的思考,在我看来,它是我们今天生活的多种族社会的起点。
***
1965年10月3日,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站在自由女神像前,说了一句将被证明错误的话:“我们今天签署的法案不是一个革命性的法案。它不会影响数百万人的生活。也不会重塑我们日常生活的结构。”他指的是《哈特—塞勒移民法》(Hart-Celler Immigration Act),这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立法,它取消了对亚洲、非洲、南欧和东欧移民的限制性配额。
该法案最终通过时,反对者描述了一幅世界末日般的情景,美国及其白人人口将被一大群外国人占领。约翰逊则向公众保证,放宽限制只会对美国的人口结构产生轻微影响。他相信,大多数人会留在自己的国家。
在接下来的50年里,《哈特—塞勒法案》将带来数千万来自亚洲、南欧和东欧以及非洲的移民。没有任何一项立法以这样的方式塑造了这个国家的人口和经济史。
在《哈特—塞勒法》之前,移民进入美国依据的是《国家起源法案》(National Origins Act),这是一个看似简单的制度,每年发放15万个签证,根据1920年的人口普查计算,每个国籍分到数量不等的配额。你在美国的同类越多,你的原籍国可以移民的人就越多。因此,爱尔兰、德国和英格兰等国获得的签证数量会远远超过东欧、亚洲或非洲国家。(非裔美国人和非洲移民被排除在配额计算之外。美国白人按国籍分类,而所有美国黑人按种族分类,因此非洲国家的名额最少。)
这种配额制并没有延伸到“东方”。将亚裔排除在美国移民政策之外的官方做法始于1875年的《佩奇法案》(Page Act),该法案禁止中国女性进入美国,以限制中国劳工组建家庭的能力。仅仅七年后,《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通过,终结了中国移民的到来,并阻止所有居住在美国的中国人获得公民身份。
这项法律很大程度上是对加州劳动力市场的回应。大多数移民到美国的中国人都是年轻男子。在淘金热和铁路时代,这些人充当廉价劳动力,通常与主流社会隔离。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制造商和农业大亨开始用华人取代其他劳动力,本土主义的反弹很快就出现了,他们将华人描述为天花和霍乱的携带者,是低一等的人类。1881年,有影响力的漫画家乔治·弗雷德里克·凯勒(George Frederick Keller)画了一幅画,后来成为排华斗争中的典型形象。这幅名为《我们港口的雕像》(A Statue for Our Harbor)的漫画将自由女神像重新描绘成一个衣衫褴褛的华人男子,右脚踩着一个头骨。他的头上有放射状的光点,上面写着“白人劳工的毁灭”、“疾病”、“不道德”和“污秽”。
这种侮辱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例如,在《排华法案》之后,年轻的日本工人仍然被允许进入美国,在铁路、矿业、伐木业和小型农场工作。他们也将很快感受到美国劳动力市场竞争的种族化影响。
1906年旧金山地震后,本土主义暴徒在街头公开攻击日本移民,呼吁抵制他们的企业。这一连串的仇外暴力蔓延到了地方政治。原本可以自由上旧金山公立学校的日本学生遭到驱逐,被迫进入已实行种族隔离的中国学校就读。这一举动在日本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也给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带来了外交上的麻烦。就在此前不久,他还因成功通过谈判结束了日俄战争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最终,罗斯福未能缓和美日关系,部分原因是一个名叫小泽高雄(Takao Ozawa,音)的日本移民,他在旧金山定居,在加州大学学习,并在地震后最终搬到了夏威夷。1915年,小泽高雄成为第一个申请美国国籍的外国出生的亚裔。这场斗争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结论是,尽管小泽完全有条件成为美国人,但公民权只能扩大到白人。
1922年做出的这一决定在国会引发了一场斗争,他们看到了创建一个完全种族化的移民制度的机会——不仅日本人、中国人和朝鲜人,而且犹太人也被排除在外——还有一群议员,他们和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总统一样,认为对移民的新限制会摧毁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的希望。
柯立芝和他的盟友失败了。1924年的《约翰逊-里德移民法》(Johnson-Reed Immigration Act)将“移民”定义为同样有权最终获得公民身份的人。由于来自“东方”的人不是白人,因此无法成为公民,因此该法律实际上终止了所有亚裔移民到美国。
移民法通常与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目标同步发展。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的第二天,美国和中国都对日本宣战,这促使了为期两年的外交努力,将中国列为美国的长期盟友。作为回应,日本开始了一场宣传运动,将这场战争重塑为在“大东亚共荣圈”中对抗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
在亚洲各地播放的数十种小册子、文章和广播节目中,日本宣传机构嘲笑有些亚洲人以为美国人会把他们当作公民,赋予和白人移民同样的权利。他们还提出了一个东亚大陆统一的愿景,能够带来一个新时代,具有无与伦比的和谐和经济实力。大部分批评都集中在一个简单而不容忽视的问题上:华人如何与一个有专门针对其人民的种族主义移民法的国家结盟?
挑拨产生了效果,虽然并不完全是日本人设想的那样。1941年至1943年间,美国的学者、政治家和媒体成员都主张终止《排华法案》。作家赛珍珠(Pearl Buck)的普利策奖获奖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取材于在中国度过的童年,这位长老会传教士的女儿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倡导结束排华的种族主义法律。
1942年在阿斯特酒店的一次午餐聚会上,赛珍珠注意到日本的宣传开始显示出成功的迹象,并得出结论,除非美国让其亚洲盟友相信他们在美国法律下将被平等对待,否则美国无法赢得战争。后来,赛珍珠写道,只要美国继续歧视中国人,“我们在这场战争中就站在错误的一边。我们和希特勒是一伙的。”
1943年5月,赛珍珠和她的丈夫以及一群知识分子和出版商组成了废除排华法案和配额制移民公民委员会(Citizens Committee to Repeal Chinese Exclusion and Place Immigration on a Quota Basis)。他们利用自己在媒体上的影响力来传播他们的信息。同月,众议院移民和归化委员会就废除法案的可能性举行了公开听证会。反对者主要来自劳工组织、退伍军人团体和“爱国社团”,他们挖掘了许多排斥华人的原始逻辑:亚洲人的涌入会带来一波道德沦丧的人,他们很快就会取代本地工人。
但公民委员会有一些强大的盟友:高级军事官员认为,得到中国的拥护不仅对赢得太平洋战区的胜利至关重要,而且对战斗结束后稳定该地区也至关重要。10月,当国会对排华法案进行辩论时,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表示支持废除。他在讲话中说:“国家和个人一样,都会犯错。我们必须要有强大的内在,承认我们过去的错误并纠正它们。通过废除排华法,我们可以纠正一个历史性错误,让歪曲的日本宣传沉寂。”珍珠港袭击事件发生仅两年多后,随着允许部分来自中国的人移民的《马格努森法案》(Magnuson Act)通过,该法律被废除。
赛珍珠和她的盟友提出了通过多元主义增强实力的愿景——自由的移民法可以加深这个国家与亚洲的外交和经济联系,以证明美国确实认为中国人是美国社会的潜在贡献者,而不是不可理喻的外人。1942年,美国战争信息办公室(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委托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超过80%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美国的强大盟友。
然而,这种世故的辞藻和《马格努森法案》颁布后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两年前刚刚批准日裔美国人拘留营的罗斯福促成妥协,只允许华人移民人数每年小幅增加。
后来的移民法案继续限制来自亚洲的移民,但做出了一些让步。1952年,来自内华达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帕特里克·麦卡伦(Patrick McCarran)和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党代表弗朗西斯·沃尔特(Francis Walter)推动通过了一项复杂的移民法,历经无数次谈判,该法在放大围绕亚洲和犹太移民的恐惧说辞的同时,却又莫名其妙地解除了禁止亚裔入籍的限制,这意味着亚裔移民现在可以成为正式公民。所有“东方”国家都有一个签证配额,然而数量很少:每年100到185个。
但这些配额是有条件的:严格限制谁可以来美国。受过教育、有家室的富裕专业人士比贫穷的劳动者更受青睐。虽然该法案已经为移民制定了一些新的途径,但它还包含一个“亚太三角”条款,将亚洲移民的总人数限制在每年2000人。
“亚太地区”的分类纯粹是基于种族:来自阿根廷的第二代中国移民将无法以阿根廷人的身份申请签证。由于他的种族出身,他永远是华人,而意大利移民在英国生的孩子可以在英国配额下来到美国。《麦卡伦-沃尔特法案》(McCarran-Walter Act)也限制了犹太人移民。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都以刚刚开始显现的冷战为理由,以及认为亚洲人和犹太人会在美国境内传播共产主义。
本土主义者和国会中偏自由派的移民倡导者就该法案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参议员麦卡伦辩称:“冷酷无情的事实是,在今天的美国,有一些顽固的、难以理解的团体,他们不但没有融入美国的生活方式,反而成了美国的死敌。”
***
过去,支持移民的政客不愿在原则的捍卫上全力以赴,原因很简单,本土主义一直很受欢迎。但在关于《麦卡伦-沃尔特法案》的辩论中,以纽约众议员伊曼纽尔·塞勒(Emanuel Celler)为首的少数立法者开始提出,对亚裔移民的限制是种族主义和不道德的。在一次演讲中,康涅狄格州参议员威廉·本顿(William Benton)辩称,这种肤浅且最终毫无意义的移民改革削弱了“我们的士兵在朝鲜战争中用血肉换来的巨大成果”。“我们可以完全摧毁这项成果,并且可以无情而愚蠢地摧毁对我们伟大原则的信仰和尊重,颁布这项法律实际上是对世界人民说:‘我们爱你,但我们想隔得远远地爱你。我们想要你,但看在上帝的份上,你还是别来了。’”
这些反驳,加上迫使本国移民法反映民权运动逻辑的压力,将为1965年移民法《哈特-塞勒法案》(Hart-Celler Act)的最终通过奠定基础。1960年,来自欧洲和加拿大的白人移民约占美国移民人口的84%。相比之下,东亚和南亚人的比例约为4%。1980年至1990年间,美国的数百万移民中的大多数来自拉丁美洲或亚洲。
这些工人中的许多人通过《哈特-塞勒法案》中的家庭团聚法带来了他们的亲属。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份报告发现,2011年,来自六个最大“来源国”(中国、印度、菲律宾、韩国、越南和日本)的移民中有62%通过家庭赞助获得了绿卡。你可能是从韩国来美国学习工程学,拿到了H-1B签证,然后进入了中产阶级的同化轨道,但你的兄弟姐妹可能带着完全不同的能力、抱负和生活愿景来到这个国家。
结果发现,本土主义者对进入美国的人群的判断是正确的。在整个19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来自亚洲的移民一波接一波地涌入。包括我的父母、祖父母、母亲的五个兄弟姐妹、我的两个表兄弟和我。尽管在他们的新国家,确实有一些跟他们长相相似的人,但他们和这些“亚裔美国同胞”除了一些老生常谈的文化脉络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无论是食物还是节日仪式,或是对白人的既有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