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人能准确追溯“四大天坑”的帽子是什么时候扣在生化环材(生物、化学、环境、材料)专业的头上的。在知乎和豆瓣等社交平台上,可见天坑专业的“劝退帖”和“自救分享”。一众“报志愿咨询”机构也来拱火,“家里没钱千万别选天坑专业”,“生化环材专业慎入”。
一众科技企业大佬们却发出了截然不同的声音:网易CEO丁磊认为比较有前途的专业是生物医学、材料科学,接下来还有化学和物理——一举选中“四大天坑”专业中的三坑。百度总裁李彦宏称自己对生物信息学充满兴趣,辞去拼多多董事长职位的黄峥曾表示辞职后将专注于食品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
生化环材是否成了不缺钱的人才能学的奢侈专业?还是年轻人想要抛弃的“夕阳行业”?《人物》采访了20多位“天坑”专业的人,他们有的坚持着自己的专业,有的早已放弃转行,还有人在选择的岔路口徘徊。生化环材专业到底“坑不坑”,又“坑”在哪里,出路是什么?多位受访者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为后来者提供一点参考。
“复杂而耗神的体力活儿”
一到春节,李晓敏就会成为实验室最孤独的人。她在北京一所高校读生物博士,胚胎是她所在课题组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养小鼠、让小鼠受孕、在合适的时机取出胚胎是重要的实验环节。实验做得多了,博士们用手指摸摸母鼠的肚子,就能精准知道这一胎怀了几个。
怀孕的小鼠并不会体谅人类春节阖家团圆的需求,一旦有小鼠生病或者错过取胚胎的时机,这一批实验就白费了。“又浪费时间又浪费钱,小鼠很贵的”,身为北京人的李晓敏揽下照料全组小鼠的重责,无论是除夕还是大年初一,她都要雷打不动进实验室,在架子前逐排巡视小鼠的状态,有一年还错过了年夜饭。
作为生化环材专业的博士生,除了不分节假日的超长工作时间,还要做各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实验,因此体力经常是一项特殊要求。
“我觉得我的胳膊好像磨电极磨得都变粗了?”分析化学博士林南那段时间研究电传感器,“如果说我研究的是菜,电极就是装菜的碗,碗里每次装不同的菜,磨电极的工作相当于做完菜之后你要去洗碗。”
“要做一个又快又稳的洗碗工”,随着实验越做越多,手艺日臻纯熟,手臂肌肉也日渐发达。
在林南看来,“洗碗”只是做实验中正常的体力活儿部分,没有心理负担。她本科时期的室友所在的实验室研究的是水污染对水生生物的危害,鱼是重要的实验介质,实验室一位同学专门负责养大量的鱼,然后给鱼“投毒”——在特定污水环境下监测鱼的代谢机制,然后再做解剖。因为面对的是活物,需要一边克服心理恐惧、一边思考实验细节,还要精进剖鱼的手艺。
林南去他们实验室时,远在门口就闻到了一股巨大的腥味儿,“根本不想迈入一步”。后来她听说,这位负责处理鱼的同学,即便毕业转行很久后,每次聚餐都表示坚决不吃鱼,提都不能提。
为了缓解压力,林南每周末会让自己彻底休息一天。休息日的前一晚,她会补偿性熬夜打游戏。有一次半夜2点,她在线上遇到了同在读博的本科同学吴昊,一局打完下来后,二人互相问候彼此为什么这么晚在线。
“我在报复性熬夜。”
“我在过柱子。”
提起有机化学的重要操作“过柱子”,材料学博士巍巍也连连摇头:“太痛苦太折磨人了。”人要一直盯着,不停加洗脱剂,用她的话说“是一套复杂而耗神的体力活儿”。她曾经有一次刚刚做好“柱子”,掐着时间去了趟厕所,两三分钟的时间内,洗脱剂过了,柱子不能用了,还得重做。
每天跟各种“柱子”打交道的吴昊尽量少熬夜,他的日常工作节奏是早8晚11,每周休息一天,而且同组的博士基本都是这个作息。他说:“科研人员要只是996的话,国家科研发展可能会停滞的。”
要说“四大天坑”首先“坑”在哪儿?由于专业的特性,苦、累、熬,就是很多人迈不过去的坎儿。

▲ 图 / 电视剧《神探夏洛克》截图
孤独的面壁者
几乎我们采访过的求学者都表示,最熬人的还不是体力上的苦和累,而是心理上的煎熬。
“做科研的人非常容易陷入自我打压。”环境专业的小乔曾被实验折磨得陷入抑郁。她当时的研究方向是污水处理,需要跟微生物打交道。
微生物通常生长于特定的污泥之中,学校一般不会有污泥储备,需要去污水处理厂取用。一次从郊区污水处理厂返回学校的路上,小乔一直小心翼翼捧着污泥,时不时检查包裹是不是足够严实,还生怕出租车司机因为臭味把她赶下车。这臭烘烘的一袋污泥弥足珍贵,污水处理厂视若珍宝,多一点都不愿意给。
正是这些宝贵污泥中的微生物把小乔折磨出抑郁症。微生物实验中的变量特别多,而且微生物本身比植物要娇贵得多。做实验时,小乔常常顾不上自己吃饭,还要定时定点给微生物投放营养液,控制温度、pH值。变量越多意味着越不可控,微生物一会儿特别旺盛,一会儿又死了,前期记录得好好的数据全都白费了。如此往复多次。
回忆临毕业前的时光,小乔记得当时自己脑子里充满了对自己的“批判”:“国家花钱培养你,你怎么就做出这种破烂?”“当初还想学居里夫人攀科学高峰,就这水平?”答辩前她甚至连退学报告都写好了。
巍巍读博士期间也曾在抑郁状态徘徊了很久。她每天早上6点起床,晚上10点离开实验室,一天能做6组实验,几个月下来记录了大量数据。但到了分析阶段,数据规律完全无法被解释。僵持一段时间后,巍巍陷入一种跟数据死磕的恍惚状态,说话、走路都感到十分费力,还要强迫自己打起精神继续工作。
同实验室的师弟师妹们见了她都不敢说话,想安慰却不知所措。况且,大家在整个博士期间,几乎每个人都在不同阶段遭遇过这种卡住的低沉抑郁期。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2019年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与影响因素》显示,35.5%的被调查研究生可能有一定程度的抑郁表现,60.1%的被调查研究生有焦虑问题。
另一个从事微生物基因编辑研究的博士形容自己在研究中最无助的时刻“就像一个孤独的面壁者”。这种面壁时刻,几乎是每一个科研人员都无法避免的。
吴昊观察自己的课题组,发现大家经常是做了100个反应,只有两三个结果是想要的。虽然早已接受“出不了成果是正常的”,他还是发现自己的心情完全拴在了实验上:新方法试验成功可以一整天快乐,而一个问题卡住试了七八种方法都解决不了时,“整个人处于崩溃边缘,陷入对自己否定的状态”。“游戏、爱好、男女朋友——任何美好的事物都没法拯救博士们实验失败的痛苦。”

▲ 图 / 视觉中国
不想去流水线就要加码学历
被实验室的苦累吓退,或者不想做科研,很多人选择本科毕业直接工作。
去年化工专业本科毕业的凌雪在苏州一家药企工作,岗位虽然叫“合成工程师”,但她时常觉得自己跟生产口罩的流水线上的工人没有太多差别。
“口罩工人是站着不停地组装,重复同一个动作,我是站在实验室的柱子前定时定量往里加料,也是重复同一个动作。会定时做一些中间物测试、写实验报告,听上去好像有技术色彩,但一个初中毕业生,只要有人带着做两个星期,都可能胜任。”
醛类、醚类是有机合成中常见的物料,有刺鼻气味,对人体有害。凌雪的公司安全防护非常严格,进入实验室前,手套、口罩、防护服、通风橱都要严格检查,实验室外的走廊还有安全管理人员随时透过玻璃窗巡视检查,一旦发现异常立刻拉闸疏散人员。一次涉及毒性较大物质的试验后,凌雪一回头,发现门外足足站了3个安全管理员,她形容“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大学期间,凌雪在系里学生会的招聘部,协助企业来学校组织招聘会。秋招的时候,两三个月内最多有60家企业来宣讲、笔试面试,很多人能当天签好合同。那时,凌雪不认为找工作会有问题。直到真正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她才开始思考自己的前途。
这个“工程师”岗位带给凌雪最大的困惑是枯燥和茫然。有时实验反应周期比较长,操作间隙,凌雪会偷偷观察同事:大家基本上都是在打游戏、看小说、刷剧,或者查看自己的股票是红了还是绿了。一名985高校毕业的同事,本科毕业就在现在的岗位上,一干就是5年。据她观察,对方除了操作更熟练,工作内容跟她的没有任何区别。
“我的成长和上升渠道在哪儿?”凌雪问。
曾经有一次,在拿到的合成路线中,凌雪看出了一些门道,兴奋地询问其中的原理,结果负责交接的博士匆忙而冷淡地告诉她,“你不需要知道为什么,照着做就好”,继而转身赶回园区另一端研发部的实验室。
研发部的实验室在凌雪眼中十分神秘,她开始思考要不要趁着下班时间充足,去考研究生。
不过,靠着硕士学历找到研发类工作在当下来看是小概率事件。70后化学博士刘芳毕业时,阴差阳错到上海一家大型化工企业做研发。当时行业人才稀缺,刘芳在内的2名博士,带着七八个本科生从零开始研发一项重要产品。到了2008年左右,她发现,博士渐渐多了起来,本科生进入研发团队成了不可能的事情,“本科只是基础知识的学习,远远谈不上学术训练,承担研发工作的确吃力”。
另一名任教近10年的材料学副教授也观察到专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我们一所省属大学,学生招上来都是普通一本或者二本,很多人硕士毕业时发的文章水平比我们十几年前在985高校的还高”。
这就陷入了这个 “坑”里的学历循环。据这位副教授观察,学生们因为担心本科、硕士学校竞争力不足,或者不想做流水线上的技术操作类工作,拼命去985高校“刷学历”。他所在的课题组,几乎所有的硕士毕业生都选择继续读博。

▲ 某药企生产线。图 / 视觉中国
被“架住”的博士
等到熬成博士,这个头衔仿佛又成了负担。
到了巍巍博士后出站找工作的2020年,她感觉博士的数量已经供大于求。她投了一家大型化工企业的酶制剂方向,面试聊下来也觉得完全可以胜任,但是因为她博士研究的方向是材料,简历上不直接对口,没能被录用。
“生化环材的基数太大了,但凡是个综合性大学,都有这些专业。培养出这么多博士,没有足够的岗位去消化,可不就『坑』了。”同样是“天坑”之一化学专业的余帆分析说。
留校任教好几年的余帆一直在观察业内学生找工作的情况,“肯花钱去投入研发、提高生产的企业太少了,博士们不得不扎堆申请教职,都往一块儿卷了”。
薛飞和妻子沁沁十多年前从北大化学本科毕业后一同到美国读博士。读博的第二年,沁沁选择了退学:自己读博的学校不属于牛校范畴,做出顶级成果的可能性渺茫,更别说毕业后在国内外找到教职了。她转读生物统计硕士,再读完博士。薛飞则继续化学专业,在两所顶级名校读完博士、做了博后,发表了一串顶级期刊的论文。
两人在找工作时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由于化学博士的供给远远大于职位需求,无论是高校还是企业研发,用人单位都有充分的选择空间,也得以压低薪资;而由于数量稀缺,生物统计博士则十分抢手,尤其对于大型药企。
药物研发的过程十分漫长,耗资巨大,而且有着很大的研发失败或者无法获批的风险。精明的药企不直接招聘全职化学或者生物的研究员,而是以博士后课题的形式将博士们招进来,等到研究成果基本确定、双方磨合确认无误后,再发全职聘书。
生物统计博士则在每一条研发线上都是“刚需”,企业会以更高的薪水疯抢人才。作为药企争夺对象的沁沁一面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一面也感到滑稽:薛飞是学霸,相比而言她自认为算“学渣”;等到工作市场上,学渣受到哄抢,而学霸则被挑挑拣拣;即便两人能被同一家企业录取,学渣的收入要比学霸高出至少30%。
夫妻俩曾经分析过:如果薛飞放弃化学,重读两年硕士转行做码农,会是更有“钱路”的选择。成果颇丰的薛飞始终无法放弃过去的积累,“如果我成果不这么好,不这么顺,也许我会很决绝地转向挣钱”。
经历了几年艰难的工作申请后,薛飞成了国内一所985大学的“青椒”,进入“非升即走”的高压阶段。
“当你有了不错的成果,往往反而会被『博士』的身份和这些荣耀『架』在那里”,化学博士的余帆非常理解薛飞的心态。余帆的科研之路算得上顺利:博士没有延毕,博后期间发了顶级期刊,30岁成为北京一所名校的副教授。
“顺利”是在整体层面的,具体到每一个课题、每一个阶段、每一次实验,余帆回忆自己从博士开始,心头的压力几乎没有一天松弛下来,“每天做梦都是实验,因为太紧张了,只能梦里思考,把清醒的时间都用来做实验。”
偶尔跟在北京的同学聚会,听金融、互联网行业的朋友们抱怨起工作强度大,余帆内心会冒出一个念头:“化学或者生物专业的博士如果能有996的工作节奏,可以算得上很幸福了。”
如果恰逢实验瓶颈期,这些外界的信息会搅动起内心的波澜:金融行业工作5年的同学的收入,可能是“杰出青年”都没法企及的,而“杰出青年”是科研界万里挑一的翘楚。
心态起伏多了,余帆已经能熟练地应对自己不时冒出来的“不平衡心理”,他会坦然地调侃自己的工资,还会自嘲道:“除了学术啥也不会”,应对不了校园外复杂的人际关系,放不下“这点情怀”和“沉没成本”,也没法毫无负担地跟一些普通学校的毕业生竞争一份“吃青春饭”的互联网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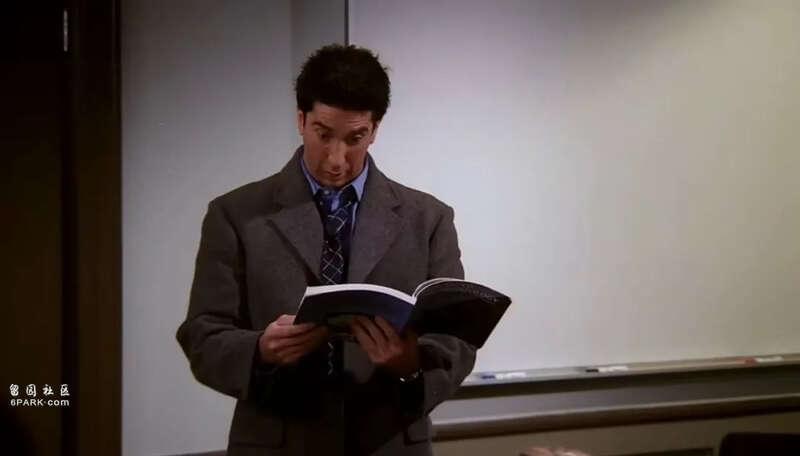
▲ 图 / 电视剧《老友记》截图
出坑
同列为“四大天坑”,还能分出级别。生物专业则被认为是“天坑”专业之首。
因为研究周期更长、工作要求的学术门槛更高,生物行业想找到所谓核心和正统的研究工作,比如教职或企业研发,需要证明自己有不同方向的研究能力,这就需要不停地做博后。
生物学专业的石妍在读博期间,同学历程度的人找工作的“标准行情”是做两个博后并连续发出高水平文章,才有求职的入场券。她算了一笔账:进入生物专业,本科4年,在美国读博平均需要7年,再做两个博后加起来5-6年的时间。从18岁开始,至少要花16年的时间,到了三十四五岁,才有跟高手竞争工作的资格。
算完账的石妍立刻决定止损。博士的第5年,她一边科研,一边找商业实习,苦熬两年后进入了一家顶级咨询公司。据她观察,周围的生物博士们比化学和材料博士们更舍得放弃,不少人甚至在做到名校生物博士后,还会选择去普通一些的学校读一个计算机的硕士,转行去硅谷做码农。“可能是生物卷得更厉害”,不舍弃的话,沉没成本会越来越高。
从事化工销售的王钢原本计划读博之后去高校当老师,直到硕士期间,有一天在实验室不小心看到了组里一名年轻老师的工资条,一颗心瞬间凉了下来。这位老师是前几年系里的优秀博士,被王钢视作榜样。不富裕的家庭条件一直是王钢心头的重担,优秀至此也没法更好分担家庭经济的现实,消除了他继续深造的想法。
硕士毕业后的小乔,戏谑地称自己是“科研失败者”,转行去一家互联网媒体。她有两任领导是生物专业转行,其中一位总监喜欢调侃“因为我们学生物的找不到工作,只能啥都干”。这位总监也坦言,他和很多公司的中层都很喜欢招“天坑”专业的毕业生,因为他们思维比较有逻辑,而且抗压性强。不过若是到了博士的程度,他也有些犹豫,“太浪费了吧?”
仍在读博的林南和吴昊都不确定自己将来是不是要从事科研工作,一方面是长期的高强度工作让他们担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另一方面的顾虑在于自己虽然出自重点院校,但是“海归”们都消化不完,不知道毕业时的竞争会多惨烈。
他们和很多同窗都在盘算另一条备选道路:考公务员。毕竟,对“很多人才引进项目和选调生岗位来说,博士学历都是加分项。”
事实上,很多博士已经走上了这条路。8月底,武汉东湖高新区公开了招聘社区干事免笔试人员名单,所有博士中,除了一名来自行星地质与比较行星学专业外,其余全是“天坑”专业。

▲ 一公务员考点外。图 / 视觉中国
博士们发愁找工作,企业也发愁招人。做了近20年研发的刘芳这两年发现越来越难招到理想的博士了,“候选人数量是不少,但是很难有能力合适的,好不容易遇到满意的发了offer,10个有8个都没来”。她有时会困惑:是不是因为化工企业位置远,相对收入不是那么高,对年轻人没有吸引力了。
相差10岁的刘芳和王钢都经历过化工行业和外企在中国的上升期。十几年前刚工作时,解决了研发关键问题的刘芳给公司带来了很大的收益,其年薪一度成为师门的骄傲。十几年过去了,刘芳发现,现在给刚毕业的博士20多万的年薪,在上海这样的地方,确实很难吸引到人才。
王钢刚毕业时的总收入是高于同届去外企“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同学的,十年后,在职读MBA的他发现,自己虽然身处关键岗位,但是行业的属性使得自己的收入在一众中高层同学中属于偏后的位置。“化工业其实一直在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是稳定的、线性的,不太可能出现爆发式的增长。”
不论是身处业界的王钢,还是学界的余帆和薛飞,常常用“行业稳定”“职业寿命更长”来安慰自己,为自己“留在行业”的决定多添一块砝码。
决定留在“坑”里的余帆会想,相比培养这么多基础科研的博士,既懂专业知识又能对接生产的高级工程师可能是生化环材专业培养未来人才的方向。
提起“会不会鼓励自己或亲朋的孩子学自己的专业”,大部分被访人表现出纠结的态度。
巍巍表示不会反对,也绝不会鼓励,“理想有时候还是挺奢侈的”。经历多次竞争后,她得到了一所不太知名大学的讲师职位。对于一直喜欢科研的她来说,虽然薪资不高、学校的科研条件也不算完善,但好歹她还是喜欢这个专业,得以继续走这条路,也不用转行。“除非特别喜欢、特别有天赋”,否则她不忍心建议别人“入坑”,去承担这背后的辛苦以及收入平平。
但凡面对向自己咨询化学专业的亲友家孩子,王钢也会严肃地问一个问题:“你做好『安贫乐道』的准备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