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松芳是一名普通的公务员,酷爱古典文学,研究饮食文化史,早在20年前就在《南方都市报》上开专栏,至今写了10余本书。
周松芳并不爱吃,在餐桌上,他也只是朋友口中“勇于做东、勤于供酒”的人。
工作之余,他却查阅多达200种文史资料来写作,今年,新书《饮食西游记》出版,讲述中华美食如何西行至欧美的故事,野史正史相结合,“上演了一出独特的东方味道,自东向西流动的剧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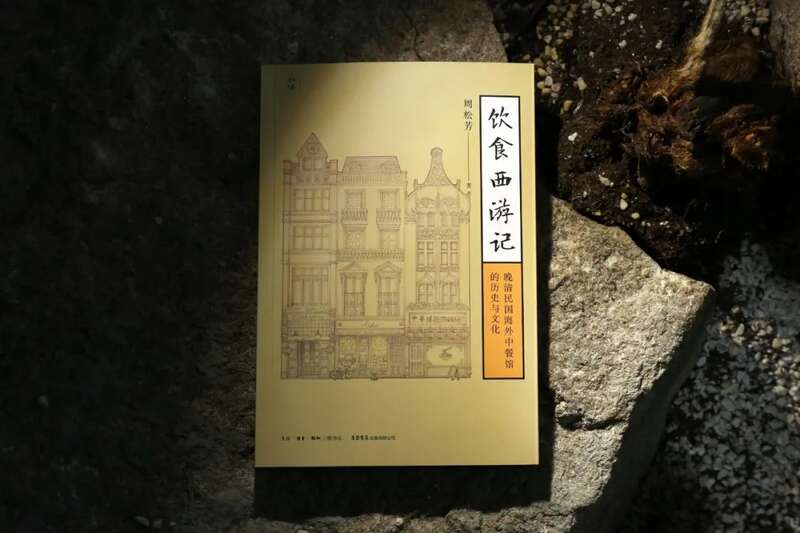

为什么美国人独爱“李鸿章杂碎”?
巴黎的一家中餐馆如何传奇,成了当年最火的社交舞台?
广东人在中餐传播中扮演怎样举足轻重的角色?
拨开美食的外衣下,这本书还侧面写出了中国人向外开拓的奋斗史。
“因为没人写过,我想我有必要填补这部分的空白。”


我是周松芳,是一名国家公务员,从小就喜欢写东西。
我出生在湖南永州市宁远县,上中学的时候语文成绩一直是全校前三的。80年代初是文学的时代,你会写诗,会写小说,你都很容易找到女朋友,就是那么一个年代。
可惜高考没考好,去了一所一般般的学校读酒店管理,我的文学梦还在,于是努力考研想考出去,最后在中山大学读了古典文学专业,直到2004年博士毕业。同时我还有着重要的本职工作,所以就利用闲暇时间写作。
我的太太是广东人,我也是很早就来到广州,深知粤菜在中国美食里不可或缺的地位,同时也对中华饮食向外传播、发展的故事产生了兴趣。机缘巧合之下,我开始研究中餐的“西游记”,用讲故事的方式讲历史,这里面的趣事,真的太多了。

“李鸿章杂碎”的出圈
谈海外中餐,必须得从美国说起、从杂碎说起。
一道象征性名菜——“李鸿章杂碎”就是主角,这道菜是因为李鸿章1896年访美开始备受关注的,说是一道菜,其实是一个总称,鸡杂碎、羊杂碎都统称杂碎,就是鸡鸭牛羊的内脏和下水乱炒在一起。
传说是他常吃的菜,但很可能只是一个谣传,因为锦衣玉食的李鸿章当然不屑于吃杂碎,而且文献也记载,他去出席美国的盛大宴会,都不怎么吃的。
但是当地的华人特别是中餐从业者就抓住这个机遇,编了这么一个故事。李鸿章无疑为草根的杂碎做了极佳的代言,就像那时候的偶像崇拜。
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炒杂碎(chop suey)”成了中餐馆的代名词。

1884年,最早的华裔记者王清福在《布鲁克林鹰报》上介绍中国菜,夸张地说:“‘杂碎’或许称得上是中国的国菜。”四年后,他又在《环球杂志》上写道:“中国人最常吃的一道菜是炒杂碎,是用鸡肝、蘑菇、竹笋、猪肚、豆芽等混在一起,用香料炖成的菜。”
杂碎最开始在唐人街巷内风靡,渐渐地向外走,开始“美国化”。它美国化的最大证据,就是成为了美国军队的日常菜,1942年的《美国军队烹饪食谱》里就有记载杂碎频繁出现在菜单里,而中国菜,也借着“杂碎”开始逐渐发扬光大。




当时中国人在美国就业,太有限了,特别是1882年《排华法案》以后,中国人就只能靠“三把刀”——菜刀、剪刀和剃头刀(代指开餐馆、缝纫店和洗衣店、理发店)。
现在也常听到人说:“美国的中餐根本就不是中餐啊,我们不吃这些菜的。”的确,那时候的华人为了要融入这个环境,不得不迎合当地的口味,但也正是因为这样,开拓了一条非常广阔的路,因为中国人就是能把菜做得好吃。

1940年的《圣·路易斯邮报》声称“中餐是世界上最美味的菜肴之一”;1941-1943年间,旧金山唐人街的中餐厅生意猛增了300%。再举个例子,芝加哥城中250家中餐馆的年收入是1600万美元,相当于21世纪初的3.1亿美元。
这其中的功臣,莫过于广东人了。有名的美食作家“胡一刀”胡文辉也在为我这本书的序言里写道:“在海外,华人史的一半是广东人的,中餐史的一半是粤菜。”

开餐馆就是广东人的强项,作为第一批到海外的,他们自然称霸了中餐业,至今依旧如此。有一次,北大校长蒋梦麟在美国留学期间去杂货铺买东西,因为广东话说不好,只能在纸上写下来拿给广东店员看。旁边站着一位白人老太婆。疑惑地问店里的人:这位唐人既然不能讲唐话(指广东话),为什么他能写唐字呢?
她不明白,方言有多,文字共有,而中国人也不只是广东人。

中餐打天下的两大要素:豆芽和酱油
海外中餐,少不了“神秘的东方黑色酱料”和“摸不透的芽菜”——酱油和豆芽。
在中餐馆里,汤面、炒菜、春卷里全放豆芽,有时一碟炒面端来,甚至豆芽多于面条。曾任《中央日报》驻伦敦的记者徐钟珮说,有一次一个侍者告诉她:“有些洋人,假充中国通,装腔作势地要点竹笋,问他竹笋是什么样子也说不上来,每到这种场合,我们常把豆芽端上去应景,洋人吃着,还直嚷好吃,好吃。”
外国人不怎么吃青菜,中国人弄来黄豆,一泡一发,就解决了远洋吃不到蔬菜的需求。


还非常有意思的是,中国菜中最受欢迎的也不是传统的鲍参翅肚,却是小笋和豆芽,而且价格都是贵到吓人,比如法国的一家中餐厅里——一个全鸭120法郎,一个全鸡150法郎,但小碟小笋却要12法郎,一小碟豆芽也要8法郎。
小笋和豆芽为什么这么贵呢?比较可信的解释是,法国当时既没有竹子(后来渐从外国移植,但难于繁殖),又没有绿豆,所以这两种“宝贝”为洋人所不经见,他们都以为这是中国土产,从中国运去的。
上中餐厅,不吃这两样中国菜,算是乡巴佬。而且吃相更“可观”:他们爬在桌上吃了看,看了又吃,毕竟不知道是用如何巧妙的方法制造出来。
因为广东厨子故弄虚玄,将豆芽的根都砍了,仅现一段芽干,使洋人见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正如洋鬼子跑到中国吃包子,不知糖是如何放进去的,至今还猜不透。

第二个重要的就是酱油。“菜里总归有酱油,这就是中国菜的证明。”
那时候,酱油在外国人眼里尤其神秘,有了它,什么菜都变得好吃了,以至于成了当时的热销产品。
巴黎最负盛名的中餐厅万花楼,就干过倒卖酱油的事:“酱油自广东用木桶封好运去,大约每桶百斤。到了巴黎掺水六七十斤,盐四五斤,参好之后再用小玻璃瓶装好,贴上红纸招条做成中国原庄货售卖。未到过中国的洋人,也不辨高下,通共买去,为的仰慕中国名气而已。”

万花楼的传奇
而说到万花楼,整个欧洲最重要的中餐馆,在晚清民国留学潮鼎盛时期作为文化社交舞台,风头强劲。
巴黎的中餐馆从一开始,无论是经营者还是服务对象,就与英美等地很不同了。英国多以华人水手起家,起初也服务于水手;美国因为淘金热和修铁路,矿工更多;而在法国尤其是巴黎,在留学潮兴起之后,才逐渐在学生和附近的华工聚集地周围兴起了多家中餐馆。

那个时候,学科学技术,美国是首选,学文学艺术,法国是首选,又集中在巴黎。当时的留法学生,往往以中餐厅作为交流聚会的场所,这其中就是万花楼最传奇。
万花楼排场很大,“伙计也最漂亮”。当时在巴黎大学留学的陈寅恪后来在书里写出了万花楼的地位——“你们这些傻子,有钱不晓得用,不如留着请我吃万花楼,别再寿头寿脑的往书店里送。”难不成,吃万花楼比读书还重要?
万花楼多阔绰呢?在那儿做了半年后厨杂役的留学生鲁汉,提供了最佳说明。
“厨房有中西两层,中菜厨房归广东人管,西菜厨房归法国人管,请的也是法国厨师,这在哪里的中餐馆中都是少见的。”
“刀百余把,每日用橡皮轮子磨两次,要磨得雪一般白,无纤毫斑点。”

同时,它是中国文人的齐聚之处。
胡适就在日记里多次写了上中餐馆的记录,而上得最多的,当然是万花楼。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1927年6月26日刚到巴黎,就去万花楼吃饭了,“又见着豆角炒肉丝、蛋花汤,虽然味儿未必好,却很高兴。”吃完中饭,“晚饭也在万花楼吃”。
前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蒋梦麟去吃的时候,只点了几叠便宜的小菜将就吃了一顿,总共不过29法郎,让服务生都觉得他是“不配招待的客”。后来管事的人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蒋梦麟,立马毕恭毕敬。


万花楼还有好玩的,它对欧洲整个生产力的发展都有影响。
核心的酱油和豆芽,这两样都起于万花楼,有资料发现它们的供应链都起始于万花楼。而一些人突然想开餐馆,请不到专业厨师的,都会到万花楼来学厨,德国的中餐馆就跑到巴黎万花楼来请厨师,你就可以看出万花楼在整个欧洲中餐管理的领导地位了。
它内容量大、档次高,还卖体系,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影响力上来了,办得越来越好,直至欧洲中餐厅的“霸主”地位。


留学生在外,也不是都能吃得起中餐的。
“长安居,大不易。”欧洲几大华人所聚的首都,如伦敦、巴黎、柏林,生活起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以菜价论,较之北京平常小馆,约贵数倍。加之饭巾、小账、零费甚多。”
如果又想吃中餐,又去不起馆子的,那就凑份子吃,就像现在的留学生一样,还是很多人常常凑作一块吃火锅,既能解思乡之愁,又能应付自如。
在抗战期间,还有耶鲁大学的留学生用中餐来策划为中国的赈灾活动——卖中国饭:“一小碗汤、一菜、一肉炒菜、一饭,卖一元五毛,本钱只花二毛五分。”
打工挣学费和维持生计,也成了许多留学生的标配。张月庐的《在美的华人餐馆及侍者》就说:“约百分之五十的留学生都是靠在专为美国人开设的中餐馆端盘子维持生计和学业。”

不爱吃的人写美食
我不能喝酒,也不热衷饭局,绝对算不上饕餮之徒。在广州这个美食之都,流连的餐馆不多,一些有特色的小餐馆反而多去。
所以我不像很多人去写当代美食。第一,我没有这样丰富的吃的经历,其次,它没法成为学术被留下来,而我如果要写,就写能留下来的东西。在岭南饮食文化史研究这个小领域,我要努力成为广东第一(有人说那也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一了),为岭南文化做点贡献。


中国人对于中餐的自豪,我相信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也会有很多人感到可惜,为什么中餐在国际上还达不到像是法餐、意大利餐等的地位?首先大家的饮食习惯不同,我们认为好吃的东西,外国人大多不太接受。其次,味觉的唤醒也需要文化的扶持。很多大牌的西式餐饮及其品牌推广,未必全靠品质,背后的文化因素很重要。


所以我们缺的,可能是一种饮食文化的传承。岭南饮食业这么发达,但好的岭南饮食文化著作却不多。大家写的都是当代,注重感官的体验和表达,而饮食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更需要我们去关注,去发掘,去梳理。
像我一样接受了比较专业的文史训练的人,几乎没有什么人来写这个,而有这个业务能力的人,他也未必有兴趣、有精力。所以我虽然不敢说这本书写得多好,但是我自认为还是有一定的填补空白的意义。
虽然这是个边缘领域,但看着这些曾经在海外打拼的华人的故事,还是感慨万千。今天的留学生在海外,如果有这么一本书在手,遥想当年,对照当下,可能也会饶有兴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