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北京生活了十年,
期间他做了7年的艺术家助理,
白天上班,晚上画画,
机械化的生活
一度让他感到焦虑、迷茫……


2014年,30岁出头的谢帆
选择回到家乡四川,
一边画画,一边吃遍家乡的各种美食。
慢慢的,他发现自己的真正兴趣并不在于吃,
而是对盛放菜肴的器皿特别感兴趣。

于是他自学陶艺,
做出的盘子不仅好看,
还特别能衬托出中餐的美,
甚至激发厨师们的灵感,
研发出新的菜式。
喻波、王勇、林敏怡、陈波,
一众美食界的大咖
都争相想要他的盘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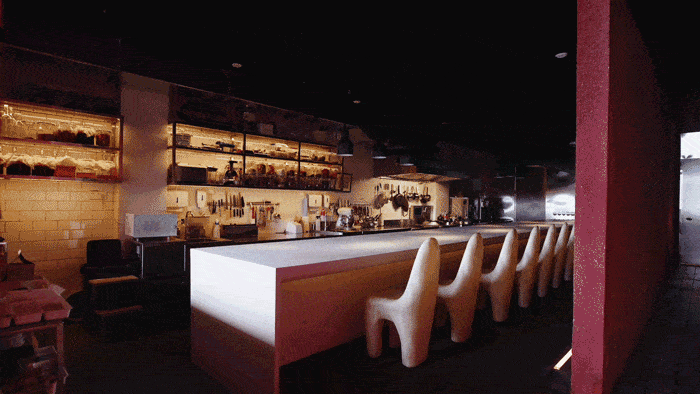


现在,谢帆在成都峨眉影厂附近
买下了一套60平米的老房子,
他会在破破烂烂的房子里
邀请美食界的朋友们一起煮大餐,
像画画一样,创作一件件美食艺术品。
谢帆说:“器皿是一个媒介,
需要激活另外一个人的创造力;
我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把食材体现得更动人。”
撰文 陈稻稻 责编 邓凯蕾


我是谢帆,四川江油人,2005年从四川美院毕业之后,就去了北京发展。
在艺术家的工作室当了助理,一干就是7年。每天白天开着车去上班,晚上就回到自己的世界,画自己想画的东西。虽然有规律的工作,却没有一个艺术家的身份。
那时正值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爆发时期,身边好多同学都已经签约了画廊,有的甚至已经小有名气,但我还是默默无闻,大家也不知道我在画什么。
有一次我回到川美,连我的专业课老师都问我:“谢帆,你是不是一辈子都这么当助理了?”

2011年,我决定慢慢独立出来做艺术家。习惯了原来那种每天规律上下班的状态,我感觉自己仿佛失业了,很焦虑。
在北京前前后后待了十多年,自己也已经30岁出头,我犹豫了许久,还是想回到家乡四川,算是回到了原点。


食物背后的器皿,是中国菜背后的魂
在朋友们眼里,我很会“找吃的”。我之前有一个工作室是在市中心的老小区,楼下全是各种串串,每次外地的朋友来我家玩,都会觉得我住在美食一条街上。
本地的朋友也觉得我挑的餐馆不错,于是我慢慢成了他们口中的“美食家”。

其实对于美食的兴趣,很可能是从小潜移默化的结果。我妈妈她们家就是做餐饮的,有一个很大厨房,给食客做药膳。记忆里,小时候一到过年就会一大家子人坐在一起吃饭,就像电影《饮食男女》里面的画面一样。
我甚至一度想把药膳重新做起来,那是我心目中最高级的中餐,有很多功夫菜,能体现中餐的高级、精致。


渐渐的,我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并不在于做菜,反而对于盛放菜肴的器皿特别感兴趣,我觉得好的器皿可以激发一个人的创造力,帮助厨师研发新的菜肴。
我开始自学陶瓷知识,马上就去研究材料学。经历了很多次的实验,终于建立了自己的标准体系,让材料变得可控。


制作陶瓷的过程,很接近我以往的艺术经验,它像是铜版画和传统摄影的暗房阶段,都有人为不可直接干预的过程,需要的是人对材料的经验。
比如绿色的盘子,要用什么样的天然材料,结合配方、配比,才能烧出想要绿,很有挑战性,也很有趣。


食物与器皿的搭配,其实是有一个色彩的逻辑在里面的,菜与菜之间也有一个叠加的关系。
首先要判断菜肴的状态——是干的、湿的、带汤的还是半带汤的;有些需要保温、敞开,有些需要兜进去。了解了这些内容之后,再去选择匹配的器皿、颜色。最后还要决定摆盘是否需要留白,以及留白的尺度。

比如糖醋排骨,我会把它骨头底下的一分部露出来,然后缠上绳子,绳子的出让这道菜更像一个装置,用手拿着的时候也会有不一样的手感。
排骨的糖汁是比较鲜亮的颜色,比较透,像果冻一样,就会选一个奶白色的器皿去体现它的红亮。


2016年,我受南京四方美术馆的邀请,在附近的寺庙做了一场斋饭。我先是在寺庙周围考察了一周,掌握了方丈主持的“用餐作息”,随后邀请了建筑系的学生跟我一起用火锅纸做了餐盘。
有将近200人参加了那次聚餐。通过在寺庙置办斋饭的行为方式,去探讨人群与信仰、形式与秩序之间的关系。食物被放置这么特别的“盘子”里,不仅食物的意义被改变,连“吃饭”这个动作,以及人与寺庙空间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为复杂多义。这顿饭竟让不少当时参加的朋友回味了三年。

“我是川菜大师这么多年等待的人”
2016年,我回到成都之后,在一个签售会上认识了扶霞。扶霞·邓罗普是英国知名的美食作家,90后年代初为了研究中餐来到中国,曾经在四川大学上学。
认识扶霞之后,她第一时间把我介绍给了喻波。喻波是一位非常有国际影响力的川菜大师,国外很多明星主厨都非常关注他。

当时他邀请了我去他家吃饭,原本我对他的印象是一个很传统的中餐厨师,去到他家之后才发现,他是那种很文人气的厨师,家里收拾得特别规规矩矩,也很朴实。
之后我们就开始聊美食,我发现他一直在寻找适合中餐的器皿,甚至去日本收过一批陶艺家做的东西,但他始终认为,中国菜应该有中国魂,只有中国人自己做的器皿才和中国菜最配,这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但在中国,我们能找到的器皿,无非就是景德镇的青花、白瓷。它们本身也很美,但却无法衬托食物的美。比如把一块红烧肉放在青花瓷的盘子里,酱色很青花瓷的颜色就不太搭。
饭局散了之后,我根据对喻波的了解,重新梳理了一套器皿单子,拍了照片给他看。


没想到第二天,他就来到我的工作室,看到实物之后非常激动、满足。她太太对我说:“喻波这么多年,一直在等这么一个人出现。”


有了喻波之后,陆陆续续深入合作的已经有11位主厨了。像杭州明星主厨王勇,另外还有不少年轻的主厨,像出生餐饮世家的陈波,曾就职于哥本哈根著名餐厅Noma的Toto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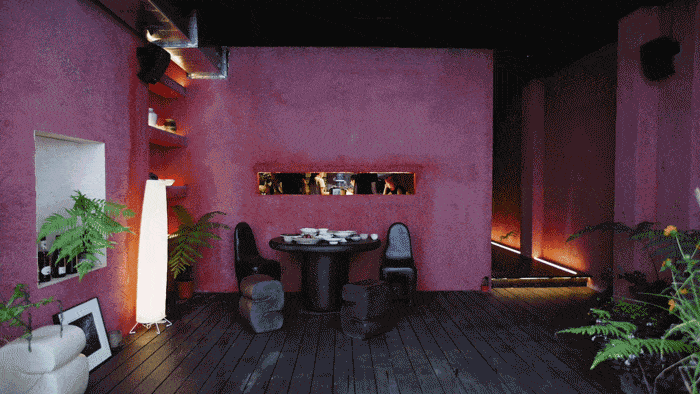
跟这些主厨在一起,不光要一起吃,还要一起玩,这样才能充分了解这个人,做出适合他菜肴的器皿。器皿是一个媒介,是要激发另一个人的创造力。
慢慢的,我发现大厨们在与我合作前后,菜肴的风格也有了变化。在国内,大部分的厨师认为,用他们自己的食材和烹饪方式做一道菜,味道就代表了他的风格。

但其实中国人说的“色香味”,色是排在香与味前面的,同样的食材、烹饪工艺,需要一个特别的元素,让别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你做的菜。

买下成都的老房子,
请大厨来破厨房里做大餐
从北京回来以后,我大部分时间是在工作室画画。工作室位于成都南边的一个新区。200多平米的大空间,我把一部分划分为画室,另一部分正在改造中,准备把江油老家的陶艺工作室搬到成都,这样可以一边画画,一边做一些陶瓷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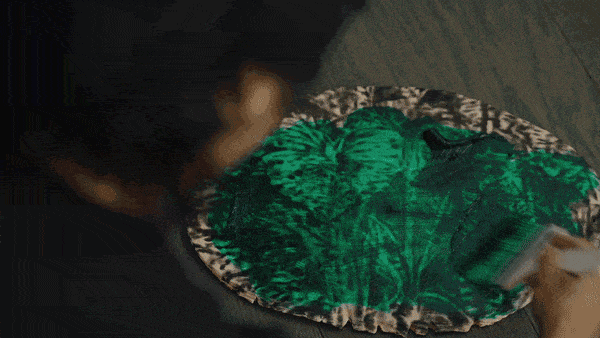
墙上挂了几幅画,是我待在四川这几年画的,来做客的朋友,可以通过这些画,感受到我的生活状态。
在成都,随处可见一种叶子很大、低矮的植物,叫滴水观音。它们不是野蛮生长,却又无处不在,很容易被人忘记和忽略,我喜欢画一些大家日常并不太关注的事物。

现在,我一周大概有三、四天的时间会待在这里工作,其余休息的时间会在峨眉影厂生活区的老房子。


老房子是上一年疫情期间买的,我想在这里真正融入成都。一层,带有一个很舒服的小院子,屋里面堆了很多器皿。我会邀请一些厨师的朋友过来,在破破烂烂的厨房里面做大餐。
最近还做了一个新的美食空间,与几个固定的主厨朋友合作,研究美食、菜品,还会带他们逛逛菜市场,吃一些非常地道的成都小吃、餐馆。

我有两个小孩,姐姐9岁,弟弟6岁,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我是纯陪他们玩。对于小孩的教育,我其实没有太多标准。
但我会观察他们的性格适合哪些方向,像姐姐就比较适合有创造性的行业,因为她不会因为外人对她的评价感到不开心。弟弟比较适合社会性的工作,医生或者律师。

在北京你只能看到艺术家,回到四川以后,能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人,打开世界的另外一面。
我觉得艺术不只是绘画,做美食其实就是做艺术。器皿是一个媒介,需要激活另外一个人的创造力,我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把食材体现得更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