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网(ID:eeojjgcw),作者:王陈,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1960年5月17日,当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渡过安达拉卜河进入越来越开阔的巴米扬峡谷时,他被眼前所看到的景象震撼,“不远处,佛教石窟沿着岩壁北面开始出现,石窟越来越密集。一座小一点儿的佛像在前,高35米。大一点儿的在后,高53米,这两座佛像面部涂着灰泥,安坐在岩石中挖出的两个巨大拱形的石龛之中。”
那个高53米的大佛就是著名的巴米扬大佛,这尊开凿于公元5世纪的世界文化遗产在2001年3月12日被塔利班用大炮、炸药以及火箭筒炸得面目全非,一起被炸毁的还有那尊35米高的大佛以及峡谷中的其他佛像。这成为21世纪人类佛教文化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
汤因比是幸运的,他亲眼目睹了大佛的威严庄重,感受到了大佛带来的平和气氛。“大约11个世纪之前,佛教就在巴米扬消失了,但是佛教信仰带来的平和依然统治着这里……在月夜俯瞰整座峡谷,能感受到这种平和。平和的白杨林闪着银光,平和的佛像和洞窟投下片片阴影。当你凝视这里,佛教的平和也会慢慢降临在你躁动的西方灵魂上。”
一、欧亚通衢
1960年,整个阿富汗都处于一片欣欣向荣之中。这一时期阿富汗处于巴拉克宰王朝末期,末代国王查希尔·沙阿和他的两个堂弟达乌德(任首相)、纳伊姆掌握着国家的权力。整个1950年代,自由议会虽然被解散,但整个国家在强人政治的推动下处于一种积极的变革之中,国家开始拥抱现代化,推行教育改革,妇女被允许与男性一样去工厂工作,女性也不再被强制穿罩袍出门。
塔米姆·安萨利那本被人们认为是理解阿富汗过去和现在最好的著作《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详细地记录下了这段历史。1957年,喀布尔电台开始播放女歌手的音乐,电台里也有了女播音员,“政府没有反对,这可被视为批准,也没有引发骚乱。”1958年,在政府获得父母同意书后,40名穿着罩袍的女工入职一家国营制陶厂,开始与男性一起工作,这“没有引发流血事件。”
随后,一场“不穿罩袍”运动从王室向民间普及,女孩子第一次不穿罩袍出现在高中,她们“穿灰色的制服,搭配黑色长袜,白色头巾。”这一些变化令国内几位最有权势的神职人员震惊,上书试图阻止这场运动,但并未成功。“每个人都为暴乱做好了准备,但一切都风平浪静。”
“王室的步伐虽然不太大,但他们开启了一扇门,变革随之缓缓而来。接下来的5年里,阿富汗女性仿佛走完了5个世纪的历程。她们终于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并在教师、护士甚至医生的岗位上发挥作用,政府部门、工厂和私营企业机构中,也出现了女性职员的身影。”几年后,喀布尔电台的女声播音成为常态。
作为美籍阿富汗人,塔米姆·安萨利非常怀念那段时光:他姐姐就是阿富汗第一个脱下罩袍穿上裙子进入高中读书的女孩儿。
1960年,汤因比的巴米扬之行是他深入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印度进行4个月零10天的旅行的一部分。这一年,这位英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已71岁。这片夹在阿姆河与亚穆纳河之间的亚洲高原,深深吸引了汤因比,因为这里“一直是上演人类历史重大事件的舞台。”
这次亚洲高原之旅显然激发了汤因比的激情,旅行结束回到英国后,他写了一本游记《亚洲高原之旅:文明的兴亡》。在书中,汤因比以宏大的视野和生动的文字对这几个命运多舛的国家给予了关注,1960年4月到5月间,当他坐着路虎汽车穿行在阿富汗群山之间时,对这个国家充满了乐观情绪。
汤因比把连接西南亚、印度次大陆、中亚和东亚的阿富汗称为典型的“通衢”(与他创造的另一个地理概念“绝地”相对,他认为,在陆路时代,日本、爪哇以及摩洛哥、不列颠群岛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陆路时代都是“绝地”)。
在陆路时代,阿富汗和叙利亚这两个曾经的文明枢纽之所以能够兴旺发达,主要是因为地理位置和陆路交通优势,在利用驴、马和骆驼等家畜转运物资的漫长时代,阿富汗是欧亚大陆移民、文明和宗教扩张的高速路,自然而然,这片土地也是诸个大帝国眼中的肥肉。但随着15世纪葡萄牙人发明了可以连续数月在海上航行的新型帆船,西欧人拥有了掌控海洋的能力,西欧暂时成为世界的中心,所有航线汇聚在西欧,再从这里发散,“基本交通工具的革命性变革,暂时将阿富汗和叙利亚踢出了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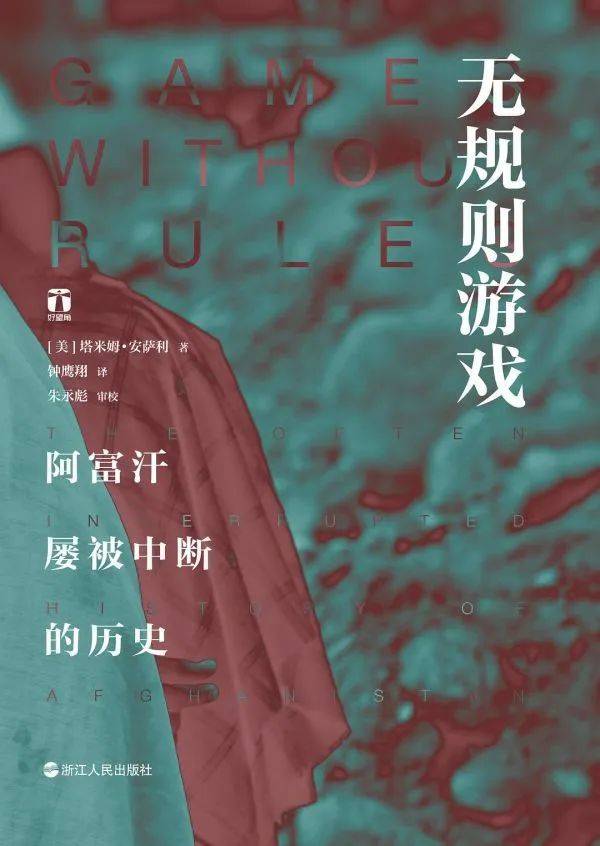
作者: [美] 塔米姆·安萨利
出版社: 浙江人民出版社
译者: 钟鹰翔
出版年: 2018-11
二、冷战机遇
1960年前后,美苏争霸冷战正酣,对阿富汗的争夺,也是两个大国冷战主题下的一个地缘政治缩影。当时的阿富汗在大国的争斗夹缝中,却显得游刃有余,获得了很多利益。汤因比注意到,借助美苏争霸,阿富汗获得了大量外国援助,一时间发展迅速,这位历史学家甚至预测:这块古老的土地将再次焕发生机。当时,苏联和美国的工程师们都在为阿富汗修建道路、港口和水利等基础设施,汤因比据此认为,这将保证阿富汗再次成为国际枢纽,恢复它在使用驴和骆驼时代的地位。
在壮丽的赫尔曼德河畔,汤因比感慨美国人庞大的水利改造计划,他们帮助赫尔曼德河峡谷管理局在这里修路、筑坝、开挖河渠,想让大片荒地变成绿洲,这个庞大计划是逐步开发赫尔曼德河南岸河湾地带,一直延伸到阿富汗边界。
在那里,阿富汗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团队都有明显的美式思维,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曾在美国生活、工作和学习,一些还娶了美国太太。他们所有人都表现出对美国生活的某种怀念,并将美式生活随身带了来,在荒漠上创造这个新世界,创作一座亚洲的美国城市。汤因比如果能活到今天,他会更加感慨,在新世纪初的20年里,美国人在重塑阿富汗的过程中,耗费了更为惊人的精力和金钱。
美籍阿富汗人塔米姆·安萨利也是个历史学家,他出生和成长在喀布尔,于1964年移居美国。在《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这本书中,他对上世纪美苏在阿富汗的争霸史记录得更为详细。两个大国在希望控制阿富汗的战略初衷上,与19世纪大英帝国三次入侵阿富汗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不同的是,冷战之后,阿富汗人更多利用了美苏之间争霸的微妙心态,而大国之间的竞争确实也推动了阿富汗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还推动了随后的社会进步。
“达乌德和纳伊姆放眼世界时,他们在冷战中看到了机遇”。于是,美国投入巨资帮助阿富汗组建赫尔曼德河谷工程局,并派出工程师、地质学家、土壤学家等来到阿富汗西南部,指导阿富汗人修建大坝,建设水力发电厂,规划运河网络,灌溉沙漠,并平地建起了一个拉什卡尔小城,也就是汤因比在赫尔曼德河上看到的那个“美国城市”,这个小城被阿富汗最保守的势力——杜兰尼和吉尔扎伊普什图部落(普什图是阿富汗的主要民族,巴拉克宰王朝的创建者和历代国王都是普什图族人)所包围。在这个“小美国”里,游泳池、俱乐部、现代化的医院、公立学校等一应俱全。
当时,西方大国还深入了阿富汗的教育系统。喀布尔各大高中的课程体系,几乎都是由德国、法国和美国规划的,喀布尔大学也在积极与哥伦比亚大学、怀俄明大学、科罗拉多大学等美国大学建立伙伴关系,“这些学校还派出学者、教授来阿富汗担任教职,赴美留学的学生队伍也呈壮大之势。”
虽然占据地缘优势以及先行一步,但在影响和控制阿富汗上,苏联明显处于劣势。为挽回局面,1955年,赫鲁晓夫访问阿富汗,并与阿富汗签订了一份协议,苏联将向阿富汗提供1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援助。
这加剧了两个大国在阿富汗的竞争,双方你来我往,纷纷投入巨资和专业力量给阿富汗,帮助阿富汗修建机场、港口和公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美、苏在阿富汗实施了一揽子援助计划,在地球上最艰险崎岖的地形上,修建了超过1200英里的优质柏油路,建立起了连接阿富汗主要城市的公路网络。”
塔米姆·安萨利不如挪揄地写到:“达乌德和纳伊姆该多么喜欢这场冷战啊!”
三、纷乱何由
如果阿富汗照此发展下去的话,很可能会成为区域经济强国,但接下来,一次次的国内政局动荡,以及苏联人入侵阿富汗,再次彻底打断了阿富汗的发展脚步,阿富汗再次陷入纷乱之中。
苏联入侵的一个主要后果,就是阿富汗原有的社会结构被重组。熟悉阿富汗社会结构的塔米姆·安萨利总结道,阿富汗基层社会一直处于“乡村共和”状态,在苏联入侵之前,这种“乡村共和”还是完整的,“土地所有者、部落首领以及村中的马利克等世俗长老,是乡村社会的真正主人,他们拥有土地、财富和武器,当然还拥有争权夺利的意志。他们和神职人员合作,但后者起从属作用,只负责批准他们的决定。”
苏联入侵扭转了上述局面,即越来越多的“圣战者”在寻找合作伙伴时,将注意力集中在了神职人员身上,“这一阶级以牺牲世俗长老为代价,获得了空前的权力。土地被烧焦、经济被摧毁,苏联军队地毯式的空袭,不仅让几百万人陷于离乱,乡绅仰仗的体系也在轰炸中一溃到底。”
1988年,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但阿富汗并未因此走出混乱。苏联撤离后,阿富汗境内留下了近30万名武装人员,其中政府军有10万人,另外约18万人隶属于各个“圣战”武装,他们久经战事,各种武器傍身,各派力量都囤积了弹药,足以支撑多年的内战。所有这一切,为日后塔利班的横空出世埋下了伏笔。
1994年,穆罕默德·奥马尔于巴阿边境成立塔利班之前,阿富汗各派武装已经联合攻占过一次喀布尔,这次攻占发生在1992年4月,由前苏联扶植起来的纳吉布拉政权被推翻,游击武装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国。首都失陷时,阿富汗总统穆罕默德·纳吉布拉·阿赫马德扎伊逃到联合国驻阿富汗办公大楼里——猫了四年之久。
1996年9月,塔利班第一次攻占喀布尔,是月27日,塔利班将这位“喀布尔之主”残酷处死。这一年早些时候,被塔利班摧毁的还有巴米扬大佛。曾为阿富汗的历史着迷的汤因比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对阿富汗将再次复兴的预测没有发生,这个中亚国家一次次陷入混乱,并沦为一个“失败之国”。
塔利班在1996年至2001年短暂建立的政权,虽然被美国以打击藏匿的本·拉登为由推翻,但从此之后,塔利班作为阿富汗最重要的民族主义武装,再也没有退出过历史舞台,在过去20年里,美国和美国扶持的阿富汗政府虽然一直想彻底剿灭塔利班,但事实证明这是一厢情愿。当塔利班今年第二次易如反掌地占领喀布尔,并在8月19日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时,就正式宣告美国阿富汗战略的彻底失败。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万达·菲尔巴-布朗(Vanda Felbab-Brown)最近撰文认为,这表明美国已经意识到,“在阿富汗的长期军事参与已经成为一种战略负累和无用的投资,美国已经不具备改变阿富汗基本政治和军事动态的能力。”
她转而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美军撤出阿富汗后,阿富汗的政治和安全形势就会出现令人满意地发展。不幸的是,一场愈演愈烈、高度分裂和血腥的内战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至少,塔利班获得正式权力将给国家的政治分配带来痛苦的变化。”
或许这种远距离观察和判断还为时过早,但是不论从阿富汗的历史看,还是现实看,她的分析都有一定的道理。
美国人在过去20年所面对的塔利班,其实在本质上和当年英国人三次发动英阿战争以及苏联发动阿富汗战争时所激起的阿富汗部族社会里潜藏着的莽荒之力别无二致,虽然外部力量一次次推翻了喀布尔王权,但征服者最终发现他们无法统治这里,不得不被迫撤离。
四、他者之败
对于阿富汗政府(无论什么样的政府)来说,也一直同样面临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就是塔米姆·安萨利所说的:在阿富汗,一直以来,臣民眼中只有家,没有国。他们只服膺于宗教和传统,听命于部落和氏族。“对于这样的国家,王权又该如何行使日常权力呢?这个问题困扰阿富汗的统治者达半个世纪之久,并将阿富汗分裂成了两个文化世界。”
进入二十世纪乃至新千年后,在文化本质上,阿富汗的根本问题可能还在于此。喀布尔合法的中央政权在本质上与以前的国王没有太多区别,仍然要面对群山深处数不胜数的部落和氏族。
而这样持久的文化传统,却能让塔利班如鱼得水,他们借助宗教和传统,能鼓动和激发起阿富汗民间各个部族、派别乃至异教徒的热情,一起对抗那些外来者,两百年前是这样,一百年前是这样,现在仍然如此,他们对抗的是文化意义上的“他者”。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塔利班重掌政权后,虽然短期内因为政治的需要,会在社会改革以及与各方合作方面做出努力和让步,但这都可能是暂时的、表面的、策略性的,长久和深入的改革难以发生。因为原教旨主义的、基于教法原则的社会主张是塔利班的底色,放弃这些底色,塔利班将不再是塔利班,这一如当年阿富汗历史上的那些改革者,一旦深入改革,就会搅动起深藏在阿富汗社会内部的传统力量,并一次次引发巨大的社会动荡,这样的历史悲剧不断在阿富汗重演,很多时候与外部力量无关。
这或许不该成为阿富汗人民的宿命,但历史总会再次成为残酷的现实,根源何在?这能归结到“普什图民族主义”上吗?起码,当年汤因比在写作《亚洲高原之旅:文明的兴亡》一书时,是有过这种担忧的。他认为,阿富汗、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三个国家就像世界上大多数非西方国家一样,感染了西方民族主义的政治疾病,且“无力承受这种疾病造成的沉重社会负担。”这或许仍是一个“他者”的观察,这种观察多少有一些“疏离感”。
2002年,塔利班被美国推翻后,塔米姆·安萨利37年来第一次回到喀布尔,他一路北行,游历了大片乡村,一直到达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曾经抵抗苏联人的根据地潘杰希尔山谷。“当时,首都的三分之一或更多的区域被夷为平地,北郊的平原上还有战火硝烟,”塔米姆·安萨利说,“我发现,阿富汗还是那个我离开时的阿富汗。”在他眼里,在很多方面,阿富汗仍然像18世纪的阿富汗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刚刚联合起来的样子。
10年后,他重返喀布尔,并去了一趟巴米扬,他虽然注意到阿富汗与10年前相比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喀布尔的人口已经从35万增长到了数百万,但这个城市依然缺少交通信号灯,交通拥堵依然无解,但人们并不着急,街头的人告诉他,“一切听从真主的安排吧!”而在偏远的农村地区也是如此,阿富汗人仍在遵循着某种传统的规则生活,“当阿富汗在18世纪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联合起来时,它可能就有了一种一贯的文化”。不论以后阿富汗的历史如何演进,它的框架是一贯的。
2012年,巴米扬大佛虽已被摧毁,但塔米姆·安萨利看到,附近的巴扎(集市)和他幼时没有什么差异,店里的老板和顾客一边喝茶,一边谈生意,街上的小贩在高声叫卖。唯一的差异,是他看到有人在使用笔记本电脑连接互联网,下载20世纪50年代喀布尔电台里播放的音乐,这些音乐可以追溯到12世纪甚至更久远的时代。在巴米扬,他看到的景象让他感受到,“21世纪与12世纪在这里紧密相连。”
阿富汗的这种文化特质或许让我们更容易理解:为何很多时候外部力量支持下的喀布尔政府会形同虚设,政府军会放弃抵抗“圣战者”,这也是塔米姆·安萨利始终对外来文化和试图征服阿富汗的帝国们持批评态度的主要原因,他进而认为,“一旦外部压力减弱,阿富汗人就能着手解决国内的文化矛盾,这条路注定布满荆棘,但是,希望并非那么渺茫。”
站在巴米扬大佛曾经凝望的巴米扬集市上,他说自己突然生出一种感觉:周围的一切并不代表过去和现在,也许它们象征着未来,它们正从阿富汗历史的沼泽中升起。我无法想象它最终的形态,只是突然觉得,阿富汗就像一个实验室。数个世纪以来,无数势力席卷过这片土地,这个国家充满了矛盾——我们的星球又何尝不是如此。如果阿富汗能成功地将国内的众多民族融合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文化整体,那么,也许这个星球也会有希望。
如今,塔利班再次抓住了这个机会。但是,它能“成功地将国内的众多民族融合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文化整体”吗?或许,塔米姆·安萨利也难以预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网(ID:eeojjgcw),作者:王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