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迷于一件叫“开放麦”的事。
下班后,他们在小酒馆、咖啡厅里的野生舞台上
跟陌生人讲5分钟的段子,
调侃自己的生活。


北京某开放麦现场
开放麦,作为一种零门槛的脱口秀形式,
不光是专业演员的新段子演练场,
也成为普通人消解生活、发泄情绪的出口。
“讲开放麦之后快乐多了,自信多了。”
自6月起,一条与上海、北京、杭州等多地
讲开放麦上瘾的年轻人聊了聊他们的故事。
开放麦这东西究竟有多爽?为什么爽?
每次5分钟的快乐,改变了什么?
撰文 朱玉茹 责编 陈子文


18:30,下班时间一到,邱瑞便从工位上起身,越过点好外卖准备热血加班和满脸倦容准备回家躺平的同事,匆忙地乘上拥挤的晚高峰地铁,最终,钻进了二环老胡同内的一家小酒馆,这里已经陆续聚集了一群年轻人。
从晚上7点半到9点,他们坐在狭小酒馆的某个角落,等待着能上台讲5分钟段子。
“最近过节嘛,我们领导就在工作群发红包。群里20个人他就发了6个红包,自己还抢1个,你说什么人能干出这种事?”
“我发现,你在家躺着发呆是不会快乐的,但你在工位上发呆,怎么就那么快乐!”
“自从我妈加入了这个子女相亲群,她整个人就变得格外兴奋。就感觉我还没找到老婆呢,但她已经找到自己的亲家了。”


北京某开放麦现场,人多到过道内都站满了人
大厂程序员、会计、公务员、医生、警察、全职妈妈、学生、专业脱口秀演员……聚光灯下,形形色色的人尽情地吐槽着生活里的糟心事,眼睛里有种平时看不见的光芒。
有些人爆梗不断,越讲越激动,直接跳下舞台。有些人紧张地忘了词,尬在台上。底下的人就低头喝酒、吃菜、玩手机,也不介意。
这场活动有个“学名”——开放麦。它是一个野生的舞台,算是脱口秀最原始的一种形式。任何人,只要你有料,就可以拥有5分钟的时间,上台以段子的形式讲出来。


在北京,工作日每晚至少有5、6场开放麦,大多隐藏在小酒馆、咖啡厅里。它们相互间隔不远,有的甚至在一条胡同里,为的就是方便开放麦演员一天可以多讲几场。
一线城市几乎都是这样,开放麦遍地开花,上海的氛围尤为热烈,省会城市也至少能保证每周有2场。
观看这些开放麦基本是免费的,或者只需要10几块钱。“一分钱一分货”,主持人一般都会在开头“友情声明”。好不好笑不敢保证,但是绝对真实、直接。
一场开放麦,10-20个演员,差不多人数的观众,大家大多在20-35岁。2个小时里,他们亲密说笑,像相识多年的好友。2小时过后,他们回归各自的工作、生活,谁也不认识谁。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沉醉于这样的快乐。日日夜夜,反反复复,欲壑难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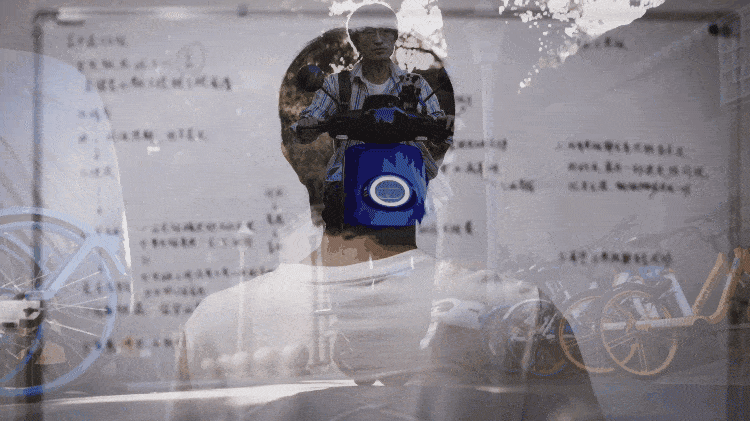
邱瑞的三点一线的生活:公司、开放麦、家
职场积压的负面情绪,讲个段子来消解
第一次是怎么登上台讲开放麦的,每个人的故事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他们积压了很多负面情绪,却没有合适的地方倾诉和发泄。
吐槽负面情绪,是开放麦的本质。而其中,最大的负面情绪之一来自职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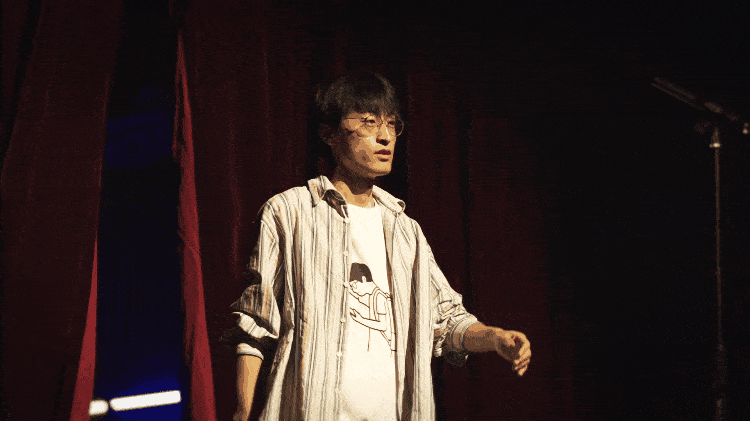
邱瑞在舞台上讲段子
25岁的沈阳人邱瑞是一名程序员,从3年前开始北漂,他就在讲开放麦。吐槽工作,或者说,“骂老板”是他段子的核心之一。
“我面试的时候,那个老板不懂业务不说,还想压低我的工资。知道专业上干不过我,就跟我玩玄学,问我,’你敲代码的时候有没有写诗的感觉?’”
说来也巧,开放麦参与者里的程序员含量极高。他们是一帮“躺平学”程序员,不主动加班、不主动跳槽、不主动要求升职加薪。邱瑞就是其中之一。


工作日的夜晚,灯火通明的办公楼和加班的邱瑞
刚来北京的时候,邱瑞其实特别愿意加班,愿意给自己时间安排得满满的,觉得能学到东西,能出人头地。“后来慢慢发现,干的时长再久,你也就是一个部件,你走了公司马上就会找另一个人来填补你的位置。”
而开放麦不同,谁也讲不了你的段子。“一对比,慢慢我就会把重心放到一个我不可替代的上面了。”
“我老板就是那种奋斗款,一天到晚让你奋斗。你问他今天能不能不加班早点走,他回:’你每天这么早走,实现自己的梦想了吗?’”

囧在讲开放麦
说这话的是32岁的杭州某银行中层——囧(人名),饱受业绩压力的折磨。而他描述的这位极品领导,大约一年前调来他的单位。没过多久,囧就开始讲开放麦了,吐槽这位领导各种令他无语的事。
“每次喊我们去开会传达文件,那文件5分钟就念完了,非要多念几次,撑到半个小时,他才觉得算是开了一次会。”
笑完闹完,第二天再去上班,囧神奇地发现,这领导看着好像也没那么讨厌了,其实还挺有趣的。“当这些东西变成你灵感的来源,还逗笑了别人,其实它就变成很正向的东西了,是一个很大的调节。”

 小乔在讲开放麦
小乔在讲开放麦观众对这样的内容总是反应热烈。“就像是有人替我做了我不敢做的事,”27岁的北京国企员工小乔说。
去年8月,她第一次看开放麦就被爽到了。当了1个多月的观众,她鼓起勇气,决定上台试试。
那时她刚进入现在的公司,领导就坐她正后方,她紧张得觉得自己全身的毛孔都处在高度警惕的状态。
讲开放麦之后她觉得自己放松多了,工作上也慢慢适应。“之前都是,天呐负面情绪扑面而来,我该怎么办?现在是,快来一个负面情绪,我要把它写成段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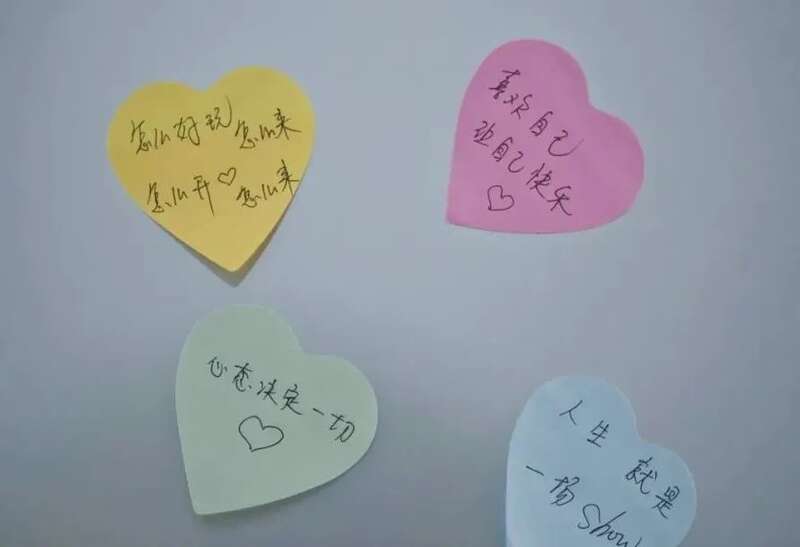

小乔在北京的住所
感情里的那些事
小乔开始讲开放麦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她和交往多年的男友因为异地分手了,“很难受,需要一个东西来填补。”
感情问题是另一个开放麦上经常提到的主题。小乔见过一位精心打扮、妆容精致的女性来讲开放麦,吐槽刚用短信和她分手的渣男。
“她真的一点都不好笑,当时大家其实都挺尴尬的,但是给她了很多掌声,好像是在鼓励她。”

囧在讲开放麦
囧也讲感情问题,被爸妈催婚。“他们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于我不结婚上面。”
没讲开放麦之前,囧几乎每天都要在办公室待到9点,等爸妈都睡着了才敢回家。“我就像是个垃圾桶,接受所有的不良情绪却没有地方倒。现在我找到这道往外说的口子,才能更包容,更好地和他们相处。”

孤独的老葱,总是一个人
老葱也讲感情,不过他的问题和这些人都不一样。
“我往这儿一站你们应该就知道我的情路有多么地坎坷。这个世界上很少有男人可以像我一样,如此完美地避开一个女孩所有的择偶标准。”
老葱今年31岁,身边的朋友基本都结婚生子,生活进入另一个轨道,只有他一直单身。
去年疫情,他一个人蜗居在10平米的出租屋里,每天睁眼上班闭眼睡觉,单身的孤独感被放大到了极致。“外卖不是可以打电话找客服投诉吗?我就没完没了地说,不让对方挂电话。”

老葱被虐狗的单身日常
疫情一结束,他就开始找开放麦讲,讲他被嫌弃的单身日常。在电影院跟检票小哥一场恶战,对方上下打量,“就一张啊?”
公交、地铁上,一个女生上来了,第一选择肯定不是坐他旁边,或者说一有空座了,马上移走。
第一次上开放麦,透过面光,老葱看到前排的人眼睛放光地看着他,那是他从未体验过的感觉。越讲老葱越是上瘾,现在他周一到周四每天要讲2-3场。
“台下我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但在台上,我就是关注的焦点。我上台刷刷存在感,生活中就不太会觉得那么需要存在感了。上开放麦,可能就跟过性生活似的,一样的快感,一样的欲壑难填,永远想表现得更好。”

老葱在讲开放麦
有些话,更容易对陌生人说
对老葱来说,在开放麦认识了一批不错的新朋友,是吸引他不断回到这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讲完了开放麦,一帮演员们还能一起凑个酒局。周末的时候,大伙还有工作坊,互相帮忙改改段子。“挺神奇的,其实我们对彼此的了解还是仅限于段子里说过的内容,但是相互之间有特别强的信任感和连接感。”


观众给忘词的小乔鼓励,小乔示意“再多来点”
这种微妙的亲密感,也许也能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人会选择向陌生人倾诉自己的私事。
“但每个人生活都不容易,老向身边的朋友、家人传达负面情绪,他们可能也承受不住,”小乔说。
和开放麦上的陌生人说则不同。“有人会认真听,一般也不会哄我下去。我也不担心他们跟我的生活牵扯在一起,他们的反应也不太会伤害、影响到我。”

小西在讲开放麦
34岁的小西是开放麦演员中的异类。她是公司的副总,婚姻幸福,基本就没什么负面情绪。“你就觉得自己很强,陷入一个无限自负的状态。”她来讲开放麦,就是想有的时候被陌生观众浇一盆冷水。
一定程度上,开放麦已成为一种简单且直接的新型社交。这群人是不是快乐,笑声就是唯一的评判。你可以选择在结束后回归自己的生活,也可以选择把它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开放麦演员和观众们的聚会
邱瑞和囧都遇到过不少演出结束后来加自己微信的观众,他们就把这些人拉到一个群里,多的时候有几百个人。
“各种工作、年龄的人都有,一些00后还给我科普为什么他们愿意排队三小时买一杯奶茶,”囧说。
“我之前在远郊合租,说第一次知道1个屋子能住7个人,东西坏了只要能用就不会有人去修,特别大的共鸣。”邱瑞说着,又补了一句,“其实所有人都很孤单。”

邱瑞上台
跟不认命的自己,达成某种和解
“我以前很虚荣,事儿都要吹大了说,刚来北京实习时,跟家里说的是我要到北京赚大钱去了。这事没干成之前就很难受,你跟家里人没法聊。”
邱瑞觉得,脱口秀给他的最大帮助是把人变得真诚了。“它让我慢慢跟自己和解了。”


深夜结束开放麦后,邱瑞独自回家
“所有人一开始都不想跟自己和解,一股劲儿就想把自己变得更好,把缺点全都改掉。”上台讲了大半年后,他开始往自己心里边问,“我为什么来北京待着,我跟女朋友的那些事是为什么?我为什么是我?”然后,去接受自己的一些缺陷,“做及格线上一点或者下一点的那个人。”
如今讲了3年、已经小有名气的他,依然时常感到焦虑,不知道怎么平衡好工作和脱口秀,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放弃哪一边。
“但现在会突然间有一个声音说,那个焦虑就是正常的。解决不了就先放着,定了目标然后往那方向走就行了。”
老葱总说开放麦就像是一场梦,醉生梦死几分钟,结束了,药劲过了,发现现实还是那个现实,但是你面对它的心态变了很多。“快乐了,自信了,也没那么矫情了。”

一芯在北影的毕业照
26岁的衢州姑娘一芯也有同样的感受。一芯之前是做演员的,北影表演系出身。“想象中的未来都是特别光鲜亮丽的,等真的去跑剧组想要获得一个角色,才发现都是泡沫,有很大的落差感。”
那时候,她觉得自己抑郁了,把自己关在家里一个多星期不想出去,也不想让别人走进来,觉得一切无意义。
“但作为一个成年人,你还是要找办法自己消化。”去年10月,她找到了开放麦。

一芯在讲开放麦
一芯段子的主要内容就是调侃自己,调侃自己演技差、声音被说像绿茶,调侃自己的恋爱、生活。
演员梦碎后,一芯一度觉得羞于见人,尤其是回老家的时候。“现在不会再这样了,调侃完之后,就觉得这都不是事儿。也许我的人生就是很平凡,但是我觉得有奔头,我努力的话,一天会比一天好。”

讲开放麦后,一芯越来越积极、开朗
不同年龄、阶层的人都来讲,这事会更好
一芯感觉到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做这件事,“每次去讲都能见到不少新面孔。有人’死’过一次之后就不敢来了,也有的不服输一定要炸场,尝到鲜之后就不想走了。”
“第一次讲开放麦我发了个朋友圈,从来没有那么多人给我点赞过,都特别羡慕。”吴志国——上海德济医院神经心理科主任,对我们说。
他上台讲开放麦,是因为某脱口秀厂牌的活动——“每个人都可以做5分钟的脱口秀演员”。

吴志国在讲开放麦
吴志国发现,吐槽自己生活的同时,也能消除大众对自己行业的一些误解。他希望听完他的5分钟,更多人能知道精神病医生也可以很幽默,不用惧怕心理疾病。
吴志国有个学生,叫黑灯,从2018年开始讲开放麦,讲他从12岁就患上的一种眼科罕见病——青少年黄斑变性。

墨镜是黑灯上台的标配,不是耍帅,而是他不能面对强光
“盲人讲脱口秀有先天的优势,不会怕冷场的问题。我讲一个笑话要是没人笑,我就想,哦这帮观众,又没来啊。”
他12岁就查出这个病,也曾经历过一段漫长的挣扎的接受疾病的过程。逐渐接纳后,找工作时他会主动告诉对方自己视力不好,发现其实也有不少单位可以接受。
他遇见了一群病友还有他们的家属,特别是小孩的家长,焦虑、无助。他讲开放麦,对这群人来说是极大的慰藉和鼓励。“他们看我的现场、视频,听我调侃,然后一片笑声,会觉得好像这病也没那么糟糕。”
“开放麦上有特别多黑灯这样的年轻人,他们讲一些其实有些沉重的话题,家庭暴力、言语攻击,但是都是很轻松、搞笑地说出来,特别震撼我,你能看到那种自我疗愈的力量。”作为心理科医生的吴志国说,“从我的专业角度讲,幽默就是一种升华的、成熟的面对困难的防御机制。”


2小时的狂欢过后,安静的场地等待着下批人来寻找快乐的人
如今全国各地的脱口秀厂牌都开设了开放麦,“不过现在讲开放麦的人可能还是过于年轻了,讲的也都是年轻人的事。”
不论是台上的演员、还是台下的观众,如果能有更多不同年龄、工作、阶层的人加入进来一起讲,视角将更丰富,层次将更丰满。
相信这场人间喜剧,也会治愈更多人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