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3tails(ID:threetails),作者:罗瑞垚,头图来自:罗瑞垚
回北京快一个月了。这些日子里,见了很多朋友,分享了一些过去两年多在班加罗尔生活的经历。突然发现,这种无主题的漫谈形式,反倒逼着我在无意之间做了一些结构化的思考,我过去生活的点滴和片段,好像珍珠一样被慢慢串了起来。
也正因为这些互动和思考,让我又重新生出了一些勇气。这与我刚回国时的感受还是很不一样的。
回国前后那一段时间,剧烈地波动和不确定性让我非常沮丧和恐惧。我还记得有一天,我失落地对布老师说,“我感觉我就像是谈了三年的恋爱之后被分手,才发现原来对方不再爱我了。”
“因为你从一开始就是单恋啊。”他半开玩笑地说。我也哈哈一笑,但还是难过。
我把这件事又告诉了另外一个印度朋友,她也笑了。然后停了一会她说,“你知道,一个国家是由她的人民组成的,我敢说你交了这么多朋友,他们都是真心爱你的。”当时听到这句话时,我只把它当做了一句安慰。但恢复过来之后我意识到,我在印度见过的人和故事,还是很值得书写的。我不应该活在恐惧中自我审查。
但这种感觉好像不能直接地与“爱”对等。对我而言,更像是一种“夹缝中人”的共情。

1
在中文的传播语境中,印度有两幅面孔:一个是高速发展中的现代印度,一个是落后愚昧的传统印度。从四月的这一波疫情开始,后者被逐渐强化,新冠疫情将所有的社会秩序击得粉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其首都陷入如此巨大的医疗危机,闻所未闻。
回国之后,有不少媒体约我写稿。因为一些非常具有冲击的影像传播,很多人都很关心一个问题:在第二波疫情到达前,为什么印度民众仍然在大规模聚集?这背后有什么“文化因素”?
但我一直坚持认为,疫情的控制不完全是一个社会议题,它更是一个公共政策议题,需要重点去看的是政府的治理,而不是民众。具体到印度来说,印度疫情的步步失守,其实背后是政府的步步失策。这背后可能和它政治、经济社会运转的逻辑强相关,与民众的意识和文化的相关性倒是最弱的,简单地说,没有人不怕死。
就我在印度疫情中生活一年的经验来看,人的行为是动态权衡的结果。比如说,我在印度的时候,去年十月到今年二月的生活已经逐渐接近了正常。我坐过飞机、火车去过其他城市,住过酒店,去过商场,偶尔去外面餐厅吃饭,定期和朋友聚会,经常骑着电动车在街上闲逛。

我确实做好了防护,回家后也会马上消毒。但我不会因为每天新增一百多例的病例,就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出门。甚至我也生出了一点侥幸:我这么年轻,肯定不会死。
我感觉身边很多人也和我一样:每个人都笼罩在巨大的、无处可逃的失望和沮丧之中,不知道这一切何时能结束,什么时候生活才能有进展;并且有一种随机的恐惧,不知道下一波高峰期何时到来。但既然病毒不会消失,我们被迫要与之共存,那可能就像被迫生活在污染的环境中、有患癌症的风险一样,为什么不尽量让自己开心一点呢?
只是在印度这样的国家,这种动态权衡的空间比较大,比如有些人就会去参加宗教和政治集会。但问题也依旧是:谁组织的集会?目的是什么?
我的感觉是,一些人之所以这么关心印度公共事件背后的“文化因素”,仍然有一种“东方神秘主义”的猎奇视角。只是这次我们也戴上了“西方”的眼镜,对邻人的痛苦冷眼旁观。这种麻木,经常戴着一张“异文化”的面具。
死亡难道不都是痛苦的吗?痛苦难道不应该被感知吗?我经常会收到很多人转发给我一些视频和图片,问我是不是真的。我回忆起去年疫情初期,我在网上看到很多武汉的视频和图片,我都不敢再看第二遍,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了好几天。
我不想去描述、回想、解答它。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种集体的伤痛记忆。

2
这次疫情的失守,对于印度这样一个处在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社会,既是意外,也合乎逻辑。前两天,还在班加罗尔的朋友发来了几张照片,照片中的城市又逐渐恢复了生机。我想到,生活在印度就像是和魔鬼做交易,要冒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才可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疫情时代,更是如此。
我所说的风景,其实就是这种处在传统和现代夹缝中的张力。这并不是我的原创,《孟买:欲望丛林》的作者也说过类似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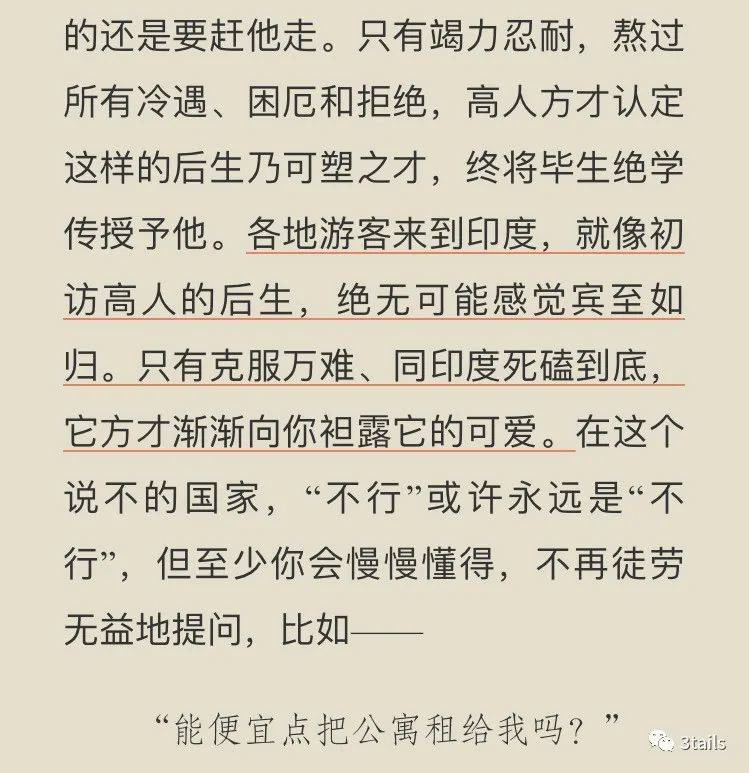
这种张力无处不在:比如封城。中产小区的居民可以乖乖关在家里,等着蔬菜水果送上门;农民工却要携家带口、徒步返乡,因为他们居住的是非现代化的、不通水电的贫民窟,做的是停工就失业、无法“居家办公”的传统工作。
再比如婚恋。离开家乡到大城市读书和工作的年轻人,接受了自由恋爱的新风潮,甚至也感受到了自由的滋味,但等到婚姻这一步,又要与传统婚恋观发生强烈冲突和对抗。
还有我之前写过的小区互助与冷漠。不同阶级之间强烈的身份差别,和中产阶级对底层普遍施以的善意是同时存在的,他们存在于同一个空间,却又是两个世界。

在观察这一切时,我也一个夹缝中人。我既不是完全的外来者,也不是他们的一份子。这让我有机会掀起“异文化”的面纱,去尝试理解那些看上去不那么带劲的复杂现实。
去年搬家时,我写过我在两个不同社区的居住报告,一个是在相对富裕的封闭社区,一个是在最普通的印度中产社区。生活在其中,我更是一个夹缝中人。那些生活在富裕小区的富人邻居,我稍微够一够也可以和他们搭上话,虽然我只是一个临时的租客,但我来自中国、说英语,总能找到共同话题寒暄几句。
而在后来居住的街区,我更像是他们眼中的“外来物品”,但我也乐在其中。当邻居们看到我去市场买菜、在阳台晾衣服、出去遛猫的时候,他们也慢慢对我产生了兴趣,问我吃不吃印度菜,会不会穿纱丽。看我穿着破洞牛仔裤,邻居家的小女孩鼓了好久的勇气对我说,“阿姨,我喜欢的你的裤子。”
后来我越来越喜欢这种“夹缝中人”的状态。其实一直以来,我也都处在夹缝中,一直在寻找一个舒服的姿态。
我生长在一个偏远的西北小镇,那里的人们依然有着最传统的看法和观念,我几乎是一个负面典型。但我有机会接受了国内高水平的教育,有机会接触到更广泛的资源,奔波在北京。但我却没有完全跨越到任何一边,我始终在中间。

3
回想起这种“夹缝生活”带给我的改变,是非常显而易见的。第一波冲击在我隔离的时候出现。
在酒店隔离时,三餐都是用塑料饭盒装着的,外面还套着一个巨大的塑料袋。两天下来,我为我隔离期间将产生的塑料垃圾而感到不安,但我又没有选择,酒店不可能为了我一个人就改变规则。
在印度,我早就习惯了尽量少用塑料的生活。餐馆打包非液体的食物,基本上都是报纸或者锡纸,或者就是防水的纸盒,只有实在没办法的才用塑料餐盒。垃圾干湿分离,干垃圾直接连桶倒进垃圾车,湿垃圾用报纸包着倒进垃圾车。

也尽量不消费瓶装水和饮料。我的印度朋友出门基本上都会带一个水杯,很多公共场合都有免费的饮用水。有个朋友来中国玩时,拿着杯子到处去找人要水,结果没人给他,商家都是让他买瓶装水,他就买了两根黄瓜吃了。
第二波冲击在隔离结束之后。我敏感地发现,公共场所到处都是扫脸的装置,甚至连申请健康码也要扫脸。不扫脸简直寸步难行。
而重点在于,印度仍然有足够方便的替代方案。虽然说印度的移动互联网正在快速发展,但放弃外卖和网购,仍然可以在十分钟之内找到市场,买到物美价廉的生活必需品。没有了淘宝的各种生活神器,反倒让我意识到极简生活的好处,很多可有可无的支出也省掉了,发扬印度的Jugaad大法。

最让我惊喜的是,生活在一个更边缘的地区,让我对中心化祛魅。读研究生时,我曾写过一句现在看来很搞笑的话,“世界的中心在北京”,就觉得一定要去北京做新闻。虽然这个决定看来是没错的,但理由确实幼稚。为什么一定要去中心呢?
生活在印度南部,它丰富多元的文化形态是妙趣横生的。相比于经常被认为代表了印度的印地语文化,我倒更希望能写写南部的其他社区。
如果要将这些我观察和感受到的片段串起来,还是需要一个有解释力的框架。我之前一直刻意远离宏大叙事,现在慢慢发现,有些事情我确实看不懂、想不明白。只能慢慢走、慢慢看,以一个“夹缝中人”的自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3tails(ID:threetails),作者:罗瑞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