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人们的欲望,对世界的理解愈发单一均质的时代,这些历史的碎片和人物故事是值得珍惜和书写的。它们不断提醒着人们,“昨日世界”曾经存在,人类不仅会重复类似的傲慢和无能,甚至还没有能力再重复一些传奇人物的经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网(ID:eeojjgcw),作者:陈亚南,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人们对待近现代世界各地发生的历史,往往是在两种极为浪漫主义的态度中选择其一。一是把一切人类的苦难不幸,都看作是强权争斗的作品。于是各种民族主义、革命、厮杀,都变成了大国棋局中无谓的牺牲品和“棋子”,似乎只有执棋者才是历史中真正有意义的行动体;二则颠倒过来,把强权的冲突和博弈都看成是必然会被历史规律和人类进步所淘汰的东西,可以对其存在无动于衷,从而某种超越历史的道德或人性成为了最值得追求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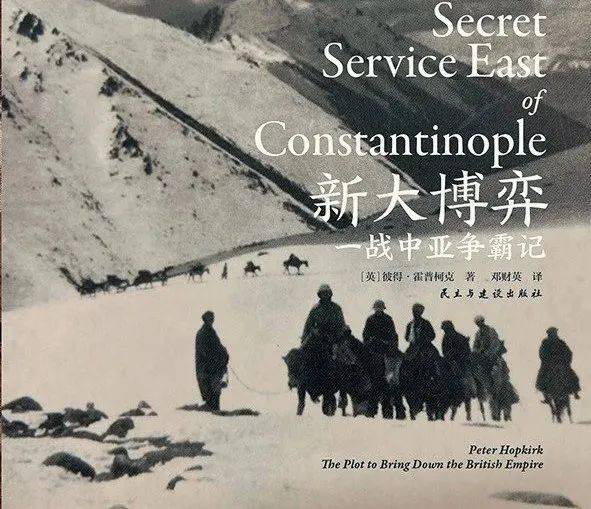
英国记者彼得·霍普柯克则试图用英雄人物传记来为历史作注,以克服他在1990年代就体会到的后冷战时代遗忘和修改历史的趋势。把历史聚焦在人物身上,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上述两种史观的冲撞能够被叙事所吸收,最后化为人物自身的矛盾和纠结得以呈现。霍普柯克精于此道。作为畅销历史读物《大博弈:英俄帝国中亚争霸战》的作者,在这本《新大博弈:一战中亚争霸记》中他延续了同样的书写方式。
对于大部分读者来说,要进入霍普柯克笔下的历史颇有难度。所谓大博弈,指的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英国和俄国两个帝国从高加索山脉、里海、中亚和阿富汗,一直到印度西北和新疆、西藏的横跨数千公里的区域中开展的军事和政治竞争。一方从印度次大陆向着阿富汗边境进发,另一方横越西伯利亚草原从费尔干纳谷地南下。
这其中混杂了军事对峙、情报谍战、宗教煽动、政治阴谋,还有移民和族群冲突。而在《新大博弈》中,霍普柯克所着眼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英国在高加索、南亚和中亚的竞争,这其中又卷挟了其他强权——如即将走到终点的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和波斯的卡扎尔王朝。
作为数十年计负责为主流大报撰写中东和中亚新闻的资深国际新闻记者,霍普柯克的行文紧贴一个个历史人物的行动、身世背景与投入强权竞争的心态。就故事性而言,《新大博弈》非常出色。通过笔下的一个个人物,霍普柯克既延续着新闻写作的丰富故事性,也试图展现出这些人物自带的悲剧色彩。
比如,历史上有几位帮助德皇穿越波斯,试图说服波斯沙阿和阿富汗埃米尔反英起事的德国冒险家,霍普柯克花费了许多文墨来丰富他们的故事。这其中有威廉·瓦斯穆斯。1915年时,德国和奥斯曼联合进军阿富汗的远征还未出发便已然夭折,瓦斯穆斯在波斯单枪匹马地挑起了一项特别任务。他像一个游击队员一样到处游走,用磁铁打出火花伪装成发电报,忽悠部落民说德皇如何对圣战虔诚狂热,串联他们向英国在波斯的利益发起挑战。他一个人像鬼魅一样来来回回。
在英国人眼中,“这个冷酷无情又富有魅力的敌人竟构成了如此之大的威胁”。只不过他结局悲惨,去世时十分潦倒,身无分文。霍普柯克看起来很欣赏这位孤独的传奇冒险家,对他后半生的凄凉不无感叹。
另一个人是冯·尼德迈尔,他带领一支上百人的远征队伍,试图穿越伊朗高原东部干旱的无人区,穿过英国人的封锁线,进入阿富汗说服埃米尔参与反英战争。路程艰难,队伍和毒蛇、蝎子、干渴、疾病一路搏斗,最终成功抵达喀布尔。只不过阿富汗的埃米尔对他们合击英国的大业实在是没有兴趣。尼德迈尔后来又试图走另一条路,横跨俄国人控制的草原前往中亚,同样徒劳无功,还险些断送了性命。
霍普柯克的笔下几乎没有什么幸运的角色。或者在那个时代中,大部分人都最终变成了失败者。英印政府的诺埃尔上尉出自贵族家庭,祖上会波斯语、阿拉伯语和俄语。一战尾声时,十月革命爆发,布尔什维克控制了阿塞拜疆的巴库。诺埃尔上尉被派去巴库活动,试图找到英军介入的机会。他积极活动,试图策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政变,结果事败被抓,投入监牢。他的对手,巴库公社的布尔什维克政委、亚美尼亚人邵武勉更为不幸:奥斯曼军进逼、阿塞拜疆人和孟什维克们背弃、英国人私下密谋,他和他的同僚们最终被残酷杀害。
19世纪末,普鲁士击败法国成立德意志帝国后,是否追逐海外殖民地成为了俾斯麦的心头难题。随着威廉二世的上台,俾斯麦小心翼翼不激怒英国的政策被改写。德国开始在帝王野心、商业利益与殖民情怀的合力激荡下向海外扩张,寻求“阳光下的土地”。“如果这个新国家要与英国、法国、俄国以及其他国家竞争,那么它就必须想办法获得原材料和海外市场。”然而作为列强扩张的迟到者,德国人发现要争夺殖民霸权,就不得不削弱英国人的力量。这促使威廉二世将外交团队投入近东与中东,撬动英国人从波斯到印度的霸权。
威廉二世的棋局很理想:奥斯曼帝国的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格外希望恢复帝国的荣光虔诚,也是狂热的宗教信徒。英国的殖民地上则生活着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群体。德皇的如意算盘是:柏林与君士坦丁堡的宫廷联合起来,煽动一场宗教圣战,以一举颠覆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而作为大英帝国的实质心脏,一旦英印统治颠覆瓦解,英帝国的世界统治便也摇摇欲坠了。这一切促成了德皇在1898年对君士坦丁堡的访问。随后,德国派遣军官团指导奥斯曼的军队现代化,并不断怂恿帝国内部的扩张力量——恩维尔帕夏等亲德军人——夺取权力。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发动政变罢黜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1913年,恩维尔帕夏又带领军人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随着1914年萨拉热窝事件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奥斯曼和德国在中东成为了并肩作战的盟友,试图向高加索、埃及和伊朗高原三个方向发起攻击。
然而威廉二世的盘算没有成功。他曾经认为列强不会联合起来对付德国,尤其是英国会选择中立而孤立于欧陆之外。结果却是英法俄一齐对德国宣战。在中东和中亚,那些被认为会一呼百应地起事进攻英国人的本地领袖也并不遂柏林的愿。德国远征队抵达阿富汗,埃米尔向德里的英国人发去电报,宣布自己站在英国人一边,当然,也借着这场效忠多索要了不少利益。
尽管这些故事引人入胜,但霍普柯克书写宏大历史的野心,和他的智识精力之间,形成了不小的落差。《新大博弈》的主要参考资料,来源于作者在英国收集到的档案和回忆录。英帝国以丰富和严谨的档案整理而闻名,但也因此,霍普柯克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权力部门和高级官员的世界里去。在这个世界里充斥着一种对世界的技术性探讨。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处发生了什么,应该怎么做,有何建议。可是,《新大博弈》的故事并不只发生在英帝国的行政机器与政治精英中,它也同时发生在君士坦丁堡、柏林和德黑兰的宫廷、喀布尔和德里的兵营与巴扎里。对这些材料,霍普柯克的处理能力就显得鞭长莫及了。说到底,《新大博弈》尽管是一部当代作品,但仍是呈现为英帝国对涉及自身的历史事件的反映与回顾。
这也使得这和霍普柯克书写《大博弈》一样,在根底上陷入了英国人对世界的认识框架。许多学者都论述过,“大博弈”与其说是实际上发生的一场英俄正面冲突,不如说更多来源于英国人对自身在印度统治不够牢固的担忧,与对俄罗斯帝国的莫名恐惧。同样地,《新大博弈》也毫不意外地带有19世纪末英国知识阶层看待世界的恐惧和焦虑。在20世纪初的著名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看来,谁掌握了中亚草原,谁就掌握了源源不断向世界四周扩张、滋扰和攻略的能力。在1904年宣读的论文《历史的地理枢纽》中,麦金德声称“正是在外来野蛮人的压力下,欧洲才实现它的文明。因此,我请求你们暂时地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看作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因为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当时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成果。”
麦金德的这种担忧长期以来促使英国人积极同占据中亚的俄罗斯对抗,并将之定性为最能威胁英属印度的假想敌。到了一战前,这种想象因德国的崛起而异位,但其本质没有变化。然而这种地缘政治的想象不曾预料到的是,印度这样的帝国心脏最终是不会甘于成为帝国的棋子与发动机,它最终会离开,让帝国土崩瓦解。更耐人寻味的是,这样的结局并非因为外力染指印度——无论是一战中德国试图渗透,还是二战中日本试图进逼,英属印度都仍然维系了对伦敦的效忠。
真正改变了的是,随着在帝国中的地位愈发重要,印度人理解了这个帝国其实是一个颠倒过来的秩序——伦敦的生存实际上端赖德里和加尔各答的存在,依靠着旁遮普和孟加拉的人力。从这个角度来说,威廉二世的地缘政策相当精准,只不过,他和英国人犯了同样的错误——并没有把殖民地当作具有自身力量和思考的政治体,而幻想着殖民地人民头脑简单,对宗教信仰或其传统无比狂热,易于煽动。
在《新大博弈》中,有一个大大被作者低估和忽略的“配角”人物。在描写到印度人被德国人怂恿和支持的反英起事时,霍普柯克提到了一位狂热的印度民族主义革命者萨瓦卡尔。此君被描写为一个狂热的阴谋家,在伦敦的印度留学生中鼓动反英情绪,策动暗杀和袭击。
在霍普柯克笔下,萨瓦卡尔的故事终结于被判监禁,在孟加拉湾中央的安达曼群岛服刑。但霍普柯克没有再追加笔墨,或可能根本没有注意到的是,萨瓦卡尔及其兄弟的目标比单纯的反英要危险和疯狂的多:他们远远吸收了比书中描写更多的德国民族主义思想乃至部分法西斯主义理论,主张将印度建设为一个单一种族、单一文化、单一国体的超级民族国家。
而为了这个目标,他们不仅仅是策动武装冲突,还倾心于建立遍布全国的社会和教育网络。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印度今日的执政党人民党,正是其徒孙一辈。早年的英国档案显然不会预料到萨瓦卡尔的后续故事。失去印度之后的英国人对印度本土的政治也失去了足够的兴趣。
借助档案,帝国的后裔们大概只会把萨瓦尔卡当作一个头脑发热的殖民地青年男性。霍普柯克撰写此书时,萨瓦卡尔后辈挑动的印度族群冲突正如火如荼。对这条故事线索的忽视,足证霍普柯克借助帝国知识书写前殖民地历史时的短板。
也许是因为常年担任记者,又因为记者生涯中多次遭遇危险,或被怀疑为间谍,或被处心刁难,霍普柯克可能是将自己单枪匹马行走四方的感受融入了笔下的人物,以至于有些过度渲染情报人员和少数政治人物在地缘政治中扮演的角色。这倒是符合自作家吉卜林以来英语文学中对地缘政治博弈的奇幻书写传统:神秘的情报战,更加神秘的对手,斗智斗勇,暗杀与探险家,这是有关英俄大博弈的不变主题。
吉卜林在其名篇《吉姆》中就这么塑造了一个被投入大博弈的英印少年,但故事的主线是一场寻找圣地的近乎漂流之旅。这样的文学传统不止在帝国中流传,也渗入第三世界的反帝文艺中。以至于1980年代天山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向导》也讲着类似的故事——英俄两国的探险家为了扩张帝国的势力,在喀什噶尔和塔克拉玛干追逐一座消失的古城。
围绕着这些“英雄人物”的历史书写,当然也必须说是有其可贵之处,尤其是,1990年代冷战结束后,许多历史都开始被重构,简单的历史终结论将列强扩张时代的残酷变成了世界进步的粉红色注脚。在这点上,霍普柯克倒是十分清醒和较为公允的。
比如,尽管霍普柯克并不同情冷战对手,但他也对一战后阿塞拜疆的布尔什维克烈士们怀有敬意,尤其是他注意到,1990年代苏联解体后,这些历史人物的历史痕迹行将被抹去:“对这些昔日英雄的抹杀和去神话化,现在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在他们的家乡巴库,他们依然躺在广场下面,但除此之外,所有其他关于他们的痕迹几乎都被摧毁了……念他们的永恒火焰也已经熄灭。”
在一个人们的欲望,对世界的理解愈发单一均质的时代,这些历史的碎片和人物故事是值得珍惜和书写的。它们不断提醒着人们,“昨日世界”曾经存在,人类不仅会重复类似的傲慢和无能,甚至还没有能力再重复一些传奇人物的经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网(ID:eeojjgcw),作者:陈亚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