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条(ID:yitiaotv),撰文:洪冰蟾,责编:石鸣,原文标题:《她把别人的家庭聊天视频,一刀未剪送到国际,入围各种奖项》,头图来源:《家庭会议》
2020年12月,《家庭会议》在广州纪录片节展映,此前它已经在几个国际电影节上转了一圈,入围和获颁了各种奖项,包括法国真实电影节、伦敦Open City纪录片电影节新锐电影人奖……


片子拍了河南洛阳的一户普通人家,家里有一个成员进入ICU,生死未定,大家开会讨论后续怎么办。
全片都是真实记录,没有排演,一镜到底,一刀未剪。
中国独立纪录片之父吴文光评价此片,“一个镜头到底,一个家庭的内部之门打开”。豆瓣网友感叹,“人的本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导演顾雪是80后,《家庭会议》是她的第一部长片,她告诉我们,自己的家庭也面临过类似抉择。
我们聊了聊她的经历和她的创作:
“我在这里说的话,有一些从未对家里人敞开聊过,家庭是我最感兴趣的主题之一,把家里的问题搞明白,大概也就知道现在的社会是什么样的了。”
《家庭会议》:我折返于家庭琐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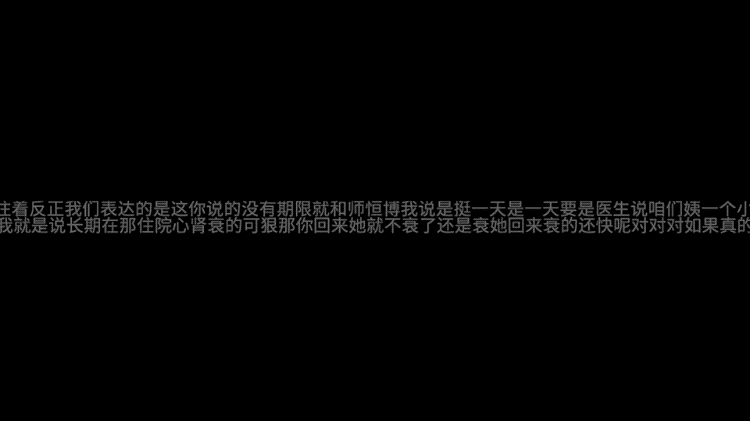
《家庭会议》时长65分钟,从头到尾就一个镜头,时而左右移动,时而停顿在某个人身上,完整记录了一场家庭讨论。
讨论的内容是要不要救躺在ICU的自家亲戚。这个病人被称作“五姨”,视角来源于主持家庭会议的两个人,“五姨”的外甥和外甥女,他们是一对亲兄妹,是导演顾雪之前已经跟拍了一年的纪录片对象。
那是2018年冬天,顾雪跟着这对兄妹,去到了“五姨”家里。一进家门,她就看到一个和她差不多大的男孩神情凝重,拿着一盒首饰,给他表姐看。表姐说:“这个都不值钱。”

这个男孩就是五姨的儿子师恒博,他的妈妈在ICU里生死未卜,命运要靠即将开始的这场家庭会议来决定。
陆续有人裹着寒气进屋,走到师恒博身边,跟他说些安慰的话。临近正月,洛阳天黑得早,吸顶的白炽灯,把沙发打得亮白,隐隐约约的烧水声从里屋传来。两代人聚在一起,窸窸窣窣说着家里的事。
顾雪就在现场,她预感到接下来会发生故事,她决定开机。

会议一开始,师恒博就告诉大家,母亲病情恶化,保住性命的可能性渺茫。
“最好的情况就是植物人,就算眼睛能睁开,那也是睁着眼的植物人。”
二姨希望可以让自己的妹妹回家,死也要死在家里。三姨希望转到普通病房照顾,找人做日常护理。四姨说就在ICU呆着,保存最后的希望。
呆在ICU,一天就得花上3000块,昏迷状态遥遥无期,万一人财两空怎么办?大家不断揣测医生话里的意思,试探会议中其他人的想法,谁也不敢给出最后的决定。
巨大的情绪压力下,师恒博抖落出更私密的对话:有人曾劝他“放弃算了”。

他是独子,还在读大学,生父早就不在了,继父指望不上。要负担后续的支出,恐怕得卖掉母亲留给他的房子。对于可以预见的死亡,他从更理性和现实的角度,考虑是否要放弃治疗。
在现场,顾雪能感觉到这个20岁左右的男孩,孤立无援。他双手抱在胸前,越来越深地陷进沙发里。有几个瞬间,他突然望向顾雪,向这个家的外人,投来窘迫的眼神。
“面对决定一个人生死这件事,大家都是往后退的。”
这场会议也折射出家庭内部的话语权。可以看出,主事的表哥表姐,是这个家里最有经济地位的人,一上来就制定议事规则,把控会议节奏。
老人们,则在决策中失语。她们缺乏医学知识,不具备体力和财力,发言会被粗暴地打断。
“(我们)没有文化,你们讨论就行了。”

影片在拍摄完成后,一刀未剪,直接成片,接下来入围了法国真实电影节、布宜诺斯艾利斯纪录片节,获得伦敦Open City纪录片电影节新锐电影人奖,还被法国图书馆和华语独立影像资料馆永久珍藏。
国内的几次放映,观众都被卷入到影片里真实的抉择两难。很多人联想到自己的家庭也面临过相似的处境:“中国人像买彩票一样,期待医学奇迹在亲人身上发生,结果往往人财两空。”
有人感叹导演的洞察力:“窒息的临场感,家庭关系的权力结构、话语体系,很有价值的影像文本。”
还有人想到,如果有一天自己老了该怎么办:“等到我们这一辈,不会是几只猫几只狗讨论说,我觉得可以放弃治疗,多买几个罐头。”

以下是导演顾雪的自述:
有一天,版版哥跟我说,他五姨现在情况很危急,在ICU,生死不明朗,全家族的人约好了五点半在老房子见面。
版版哥是我正在拍摄的一部纪录片的主人公,他们家是洛阳的膏药世家,有两百年的历史,三代同堂住在一起,我们拍他们已经拍了一年。
版版哥和我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剧组已经收工,摄影师拿着摄影包,制片决定去吃拐角那家的烫面角和牛肉汤。
我说,我想去现场看看。

开机拍摄他们开会的过程是临时决定的,但最后把它做成一部影片,是因为这样的场景,我非常熟悉。
从小的记忆里,这样的家庭会议我经常见到。会议一定是发生在客厅的沙发上,寒暄之后,各自表态,进而争论,试图说服,重复观点,再次阐述自己的意图,这样来个两三回合。
偶尔会争个面红耳赤,情绪激动,但是很快就会有相应的角色来安抚,最后往往是男性的长者、和经济上更有话语权的人来做个结束。每个人带着自己的心思和不满,发几句牢骚,各自散去。

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要用一个长镜头来展现。人们往往希望得到一个更加准确的主题或答案。但生活其实就是充满了含混、琐碎、无意义的反复和无奈的滋味。
这些反复争论,每次似乎有结果又没有结果,正是我对于中国家庭关系的一个观察:人和人之间难以沟通。
完整保留发生的所有细节,让观众、摄影机、事件当事人的三个时空完全统一,我觉得这太好玩了。
虽然一开始就想好了要“一镜到底”,但现场总有突发状况,整个拍摄过程,我一直处在兴奋紧张交织的情绪里,真的是拍到最后一刻,才觉得这个作品可以成立。
想拍十年自己的家庭:我对亲密关系是有质疑的
我出生在河北承德,父亲是满族人,母亲是汉族人,还有一个大我8岁的姐姐。
我的姥姥叫安桂英,她有10个孩子,我妈妈排行老三。姥姥的头发总是梳得溜光,打麻将输了还会发脾气。

姥姥78岁的时候得了脑淤血,之后十年里一直瘫痪在床。我特别清晰地记得,姥姥住在主卧,我住在她旁边的次卧,夜里,姥姥经常哎呦哎呦地叫个不停,我时常被惊醒,然后难过地睡去,一点办法都没有。
有一次,姥姥和我妈妈说:“琴,快点让我死了吧,实在太痛苦了。”妈妈说:“老天没说带你走,我可不能把你送走。”
后来一个朋友和我说起他外婆的事情。他外婆病重,他回去看她,当时医生说人已经失去了意识,就只是活着。最后他做了一个决定,让他的外婆安乐死。
因为这件事情,我和他大吵了一架。当时觉得凭什么他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太残忍了。他很爱他的外婆,特别痛苦。他说,因为活着只会更加失望。
拍《家庭会议》的时候,这两件事从记忆里窜了出来,又交织在一起。影片的英文名就是“选择”,我想我到现在也给不出一个答案,但我想看到这部电影的人,会去思考:如果换作你,你该如何选择?
大家庭人多,是非也多。家族里有人被欺负了,姐妹们就一起出门,和对方干仗。有时候也会因为芝麻蒜皮的小事,在亲情和利益关系中扯皮,在家庭琐事中分分合合。
印象里,过年的时候,这10个家庭都来看瘫痪的姥姥。大人们在外面吃饭,相互敬酒,嘻嘻哈哈地笑。姥姥躺在里面,哎呦哎呦地叫。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会对亲密的家庭关系持有怀疑。甚至觉得更像饭桌上的秀场。我们明面上其乐融融,私底下各怀心思。

2020年春节,疫情严重,我回到老家。除夕晚上被通知正月里不可以走动,要在家自我隔离。那段时间,每天都看手机里关于疫情的新闻,非常压抑,当时想表达点什么。
我想到薄伽丘的《十日谈》里,瘟疫流行,十个人逃到一个地方避难,每天讲一个故事。
于是,我请妈妈这一边的十个兄弟姐妹,每一个家庭坐在自己家的沙发上,看手机,读一条疫情期间的新闻,每个新闻就是一个故事。
我拍摄下全过程,然后并置在一起,给我爸妈看,再拍下他们观看的过程,制作完成新片《庚子新年》。

《庚子新年》算是开启了我的家庭影像计划,我打算每一年选择一个线索,记录我的家人,十年之后,能在时间的纵深里看他们的变化。
拿起摄影机,我也终于有了一个理由,可以走进我亲人的生活里。平时我们的生活也不过是新年聚会里的相互问好,其实并不知道彼此是否真的过得好。当我在镜头后对他们提问,我们产生了一种新的交流方式,我才发现,我原来不够了解他们。
家庭里出现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可以放大到任何一个地方,我想往内走,观察每个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当我真的把家庭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搞明白,大概也就知道现在的社会是什么样的。
做自己的东西,不和那些“社会男人”竞争
2019年10月,我的一个手机丢了,里面有很多我拍摄的影像素材。于是我就开了一个公众号,叫“顾雪的影像日记”,每天在手机上制作、上传,到现在已经有近140篇了。和过去写日记的感受相似,记录下当天的心情。
我会对日常有一种迷恋,瓦尔达有一部纪录片叫《拾穗者》,讲的就是那些经常去捡别人不要的东西的人,我在影像日记里做的是“日常拾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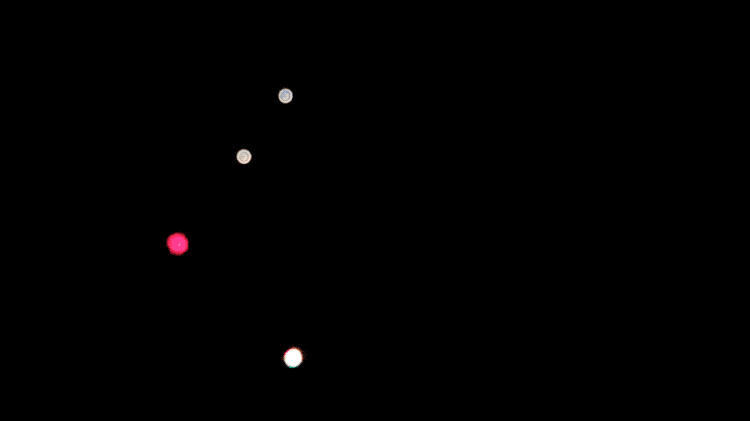
有一段时间我会放着摄影机一直拍,想去捕捉日常里会发生的戏剧性瞬间。
有一次,一个男生约我吃饭,我带着摄影机就去了。我其实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我很期待那个未知性。
尽管看到了摄影机,他还是在镜头面前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开车送我回去的路上,他说了一句:“我一看你带着摄影机出现,就知道这个表白应该不会成功。”

10年前,我拍了第一部纪录系列片,叫《失语者—朝鲜战争战俘纪事》。拍摄对象叫作张泽石,他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参加了朝鲜战争,被俘后坚持回国,回来后经历了各种运动。
2015年,我认识了顾桃导演。因为都姓顾,又都是满族,我们一见如故。我常亲切地称呼他“老顾”。
老顾的作品,我很早就看过的,包括他的“鄂温克三部曲” 《敖鲁古雅・敖鲁古雅》《雨果的假期》《犴达罕》。当时他正要动身去新疆拍片,问我是否愿意做执行导演。我第二天就辞了职,第三天跟着老顾去了新疆。

2016年,我和老顾合作了一部描写少数民族少数性取向的纪录片《牡丹花开》,讲述他们在新疆的生活。
片中有一个主角叫米雪,她是回族人,做了变性手术,变成一个非常迷人的女人。和米雪相处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她的敏感、细腻、妩媚,更重要的是她在面对自己选择和社会标准冲突时候,那坚毅和温柔的力量。
拍完这部片子,我开始感觉到,我自己身体上有一种女性的启蒙,特别是女性触感的启蒙。这个可能跟我小的时候对生理上的一些感受不同,我开始能够欣赏女性的美,来反观到自己的一些女性特征。
有一个男导演看完我的影像日记,他说他觉得这个东西是没什么意思的,每天拍日常琐碎的东西,就像是一个vlog。这个事情给我触动挺大的,后来我就想,关于价值的标准是由谁来定义的。
吴文光老师看了《家庭会议》很喜欢,他说他喜欢这种观念加现实的创作,他鼓励我说,“不要去跟男人较劲,女性是天生的感性强者”。
听完这话,我开始思考这是属于一个女性的视角吗?还是说的确有一些女性创作和男性创作中独特的东西,有待被挖掘。

《家庭会议》放映之后,经常有人会这样问: “一个镜头太长了吧”,“很多琐碎的为什么不去掉?”“这不是摄影师完成的镜头吗?导演做了什么?”
我的回应是:当我决定开机的那一刻,这个电影就开始了。当我决定把它呈现给观众的时候,它就完成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条(ID:yitiaotv),撰文:洪冰蟾,责编:石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