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更有一群年轻人正在崭露头角。
她们以敏锐的洞察和新颖的手法,
进行创作与表达。
24岁的大连姑娘岳明月,
创作纤维艺术作品已有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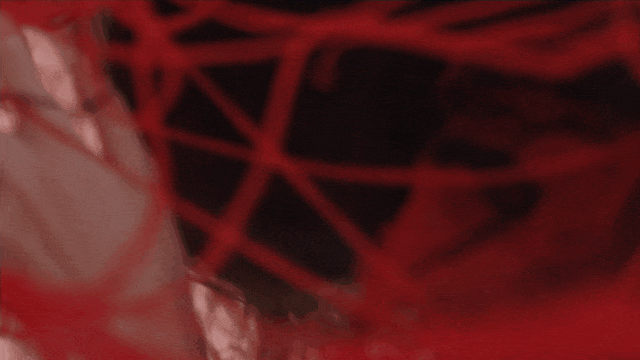
作品《祈主保佑生养》,展览巨大的“子宫”
她从小性格温和,
但创作的形式特别大胆。
20岁,她在爷爷去世后,模拟殡葬现场,
在黑纱白布间行为表演,最后一把火烧了,
想要连接两个世界;
22岁,陪母亲做完子宫切除手术后,
她开始用红纱缝制巨型子宫,
探讨生育与女性身体。
还邀请观众一起走进去,
重新感受母体内温柔的包裹。
岳明月发现,
90后对于“生育恐惧”“突然离世”的认知,
往往是一瞬间的,
“关于生命的始与终,
我觉得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聊会更好。”
年后,一条来到岳明月的创作现场一探。 自述 岳明月
撰文 陈薇沁 责编 陈子文

岳明月在巴黎艺术城展览现场看了岳明月的“子宫”红纱装置、以死亡为题的黑纱系列后,我们惊讶于她的年龄:1996年出生。
疫情后的2021年春节,她选择不回家过年,从北京跑到上海青浦驻地一个月,“工作室因为疫情被封了,父母也挺支持我换个环境来创作的。”她几乎没有任何年轻人的“不良嗜好”,不打游戏,不去夜店,也不爱购物。接触几次,会发现她的敏感、怪异与可爱。


清华美院展览现场岳明月在清华美院学习纤维艺术6年多,连续参展3届“从洛桑到北京”国际纤维艺术双年展,2019年底在巴黎艺术城举办双个展。在这个领域里她还非常年轻,常用大胆的形式来创作女性题材的作品,大面积用同一个颜色,喜爱用纱超过布,“因为纱又柔软又坚韧,就像女性一样。”以下是岳明月的自述。

大学的时候,我陪妈妈去做了子宫切除。
她检查出了子宫腺肌症,这是一种非常频发的女性复合病。她因为长期服药,凝血系统失灵了,表现就是会大出血,非常痛经,流血不止。试了许多保守治疗的办法,直到完全没有办法,只能切除。
妈妈手术的那天是我月经的第一天,痛经非常强烈,我在妈妈的手术病床上躺了很长一阵。

幼时岳明月与母亲
手术后,我问妈妈感觉如何:“做了手术后身体感觉好多了。但作为一个女性,子宫被切除,心里真的很难受。”
我虽然没有生育过,但那一刻,作为妈妈的女儿,我对她的痛苦感同身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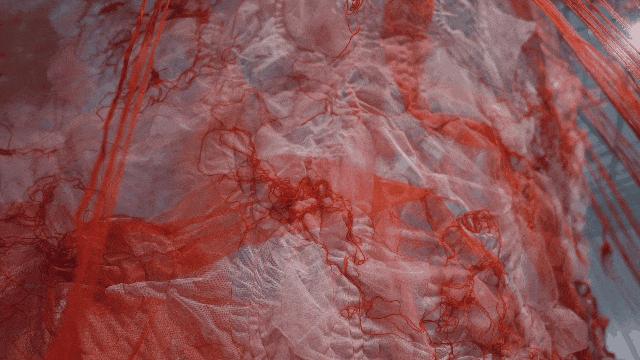

那时候是准备毕业设计的初期,我希望用我比较擅长的纱材料做一件象征子宫的作品,让大家重新感受生育的价值。《祈主保佑生养》,在大型刺绣机上制作,把纱和线不停往正在绣的机器里去撒,做出那种血液的效果,就像是皱褶的皮肤和内壁。
红色的纱和布层层叠叠地软软铺开,整个作品长、宽都是4米多,高1.5到2米之间,取决于布料的延展,它带来的感受就很像子宫本身。

纤维作品《祈主保佑生养》它第一次在清华美院的艺术博物馆展览的时候,被保护得很好,周边放了禁止入内的一米带。我就和保安说,不要保护这件作品,让所有人都进去。
观众刚开始是比较犹豫的,害怕扯断了哪根线,毕竟“艺术品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于是我就在里面用身体做了一个表演:用子宫的皮肤去包裹自己,在子宫的脉络里疼痛和挣扎,最后躺回子宫里去感受它的温暖。


观众进入作品,感受被作品包裹跟着我走进去的观众都说:“真的有回到子宫、回到一个很安全温暖的空间里的感觉。”纤维它天然就有一种温热的状态,像一个罩子一样裹住我们。
《祈主保佑生养》这个名字,是我和一个编剧朋友一起讨论出来的。当时会大量去聊《使女的故事》这部剧,它讲得比较极端,认为女性就是作为一个生育工具,她的责任就是不断繁衍后代,延续人类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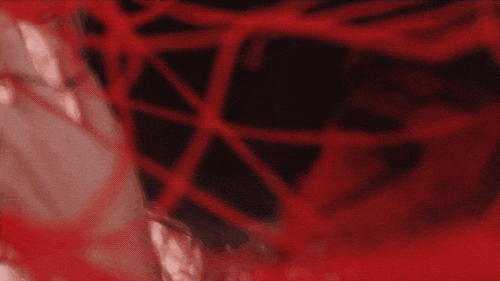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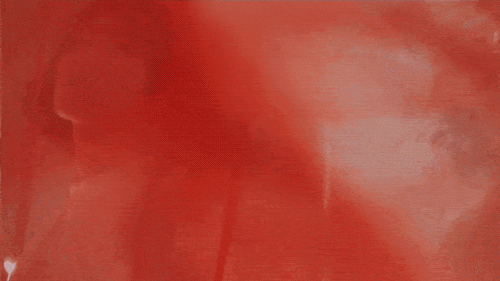
我取这个名字,是在对女性和生育认知非常冲突的时期。当时会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一些女性器官的独特,它在生活中是困扰着你的。为什么一定是女性去经历这些利用呢?
直到我去看了话剧《阴道独白》的中国版,原剧是美国的导演,其中说了许多在战争时期女性被性侵的故事。中国版描写的全部都是中国女孩的故事,演员里包括一位跨性别的女性,都很敢讲关于“阴道”的故事。再做红纱系列,我就会想做得更温柔一些。



红纱《婴儿》系列在巴黎艺术城驻地的时候,做了非常大的一个长卷的红纱《婴儿》,在一个扭曲的空间里有远古的鱼、书、丛林和神话,大大小小的婴儿在这样的世界里不停地穿梭、翻滚,可以理解为非常浪漫的“胎动”。
用红纱做这一系列作品,它让我联想到了所有女性去孕育生命的过程中,她们的热情和她们的温柔。

每当观众通过的红色走廊,都会有种“进出女性子宫”的感觉2020年,我参与了一个女性群展,策展人特地计划在一个红色的通道里,挂上我一幅幅的《婴儿》红纱作品,所有的观众进入和离开展厅都需要通过这个过道,仿佛在进出女性的子宫,很自然的过程。

从初中开始,很长一段时间“死亡”这件事情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最恐惧的是妈妈让我在家多和爸爸相处,她从很早就为我设了心理预期,抵挡未来她可能的突然离世。
2017年,跟我很亲的爷爷突然离世了。爷爷的5个孩子在老家举办了一个很隆重的葬礼,祭拜、巡山、火化,所有人都在悲痛,所有人都在哭泣,又像是一个表演,又非常真实。

 那个时候,我对“死亡”的顾虑也突然就崩不住了,之后做了一年多和死亡相关的作品,取名《黑纱》。
那个时候,我对“死亡”的顾虑也突然就崩不住了,之后做了一年多和死亡相关的作品,取名《黑纱》。

《他看不见我为他燃烧的花》草图与作品呈现 《他看不见我为他燃烧的花》是我送给爷爷的。
我把从葬礼上带回来的黑色“戴孝布”和丧葬“烧纸”的概念结合在一起,用火烧黑纱的边缘,缝制出许多黑色的向日葵。火在中国人的心中是通灵的,连接着两个世界,希望能把我内心最柔软的东西寄送给爷爷。



那个时候我就碰到了刘丽娟,她是我在清华纤维艺术专业的同学,我其实有点惊讶她对死亡的话题也非常关注,两个人聊了很多亲人离世的故事,然后逐渐开始探讨死亡是什么?葬礼是什么?
最初的探究是比较疯狂的,两个人找了一个空地,仿照传统的丧葬仪式,挂上白布与黑纱,拿着空白的镜框在里面旋转、默哀、走来走去,最后一把火烧掉了这场“没有人过世”的葬礼。




和刘丽娟合作的动态影像《始终》,展现一个人如何从出生、好奇、挣扎、回归的过程很快我们又想着如何去抵抗死亡。影像作品《始终》探讨了一个人如何从白色像胎盘一样的地方苏醒,然后慢慢意识到死亡,从不接受、到焦虑、再到反抗,最后平和接受的一个过程。

作品《安魂曲》2018年,我们做了一件长5米多、宽1.5米的黑纱作品,取名《安魂曲》。名字来源于莫扎特,那是他生命结尾写的最后一首曲子,还没来得及写完,里面强烈激情的曲调,让我联想到一个即将离世的人,那种汹涌的不舍。

清华美院的老师来看展,说我们这么年轻的艺术家就探讨生死,真是“又拧巴又有趣”。
我倒不认为这是一个贬义的评价,我从10岁开始就对死亡有很深的恐惧,如果可以提前接受死亡教育,我认为是件挺好的事。


在安徽的百年祠堂里办展意外的是我们后来还被邀请,把这场展览在安徽一个村世代相传的祠堂里再办一次。
相比我们年轻人的胡思乱想,村里的老人早就为自己备好了棺材,观念非常豁达,“生死天命,珍惜当下”。
在那里临时做了黑纱系列的最后一件作品《光》,黄色的柔和的纱挂在门口,就是一个光的空间,中间有燃烧着火的空间,里面祠堂的棺材上,有悬挂的黑纱,就像是每一位老人对死亡的寄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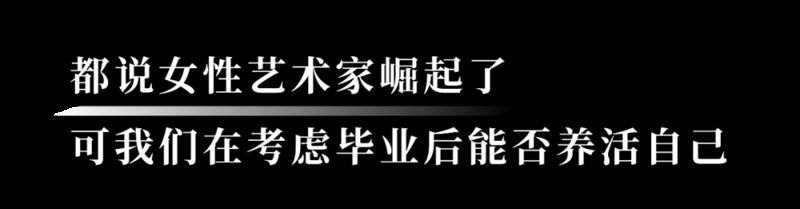
小时候,我的父母是开书店的,我是属于一边画画一边读书,这样慢慢长大。
舅舅曾在清华就读,2014年,他建议我在几个录取院校里选了清华美院,“在清华能学到的比纯艺术更多,在文学上或者哲学上,甚至理工科的课程都可以接触到。”

纤维艺术是一个分在设计学里比较小众的学科。大学里会教授高比林、奥比松的编织技术,很适合慢慢创作。
我也受到很多老师的影响。专业里的前辈像是林乐成老师,开创了清华大学纤维艺术专业,很早就把洛桑双年展的精神带到了国内。肖薇老师是做戏剧和电影学研究的,她带着我接触了即兴表演,打开自己的身体,很感性地进入艺术。洪兴宇老师,做了很多河南汴绣的研究,把中国的手工艺带入当代艺术中。

2021年春节,在上海驻地创作一个月今年春节前受到疫情的影响,北京的工作室都贴上了封条,我也被迫放弃了里面巨大的刺绣机,决定带着妈妈的缝纫机来上海驻地,待上一整个春节,重新整理一遍作品。来之前,我提前回了一趟老家,住了10天,陪在妈妈身边包饺子,晚上就一家人去提前放过年的烟花。
在上海青浦驻地的这一个月,我一边继续在做《婴儿》系列,一边也和三四个女性艺术家朋友们一起体验慢生活,到了中午,一人拉一个板凳,在太阳底下聊我们未来想做什么。

岳明月和她的艺术家小伙伴们,最爱在午后一起晒太阳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存在着焦虑。
一方面是对创作的担忧,一方面也是在犹豫,是否去当一个职业艺术家,是否要去找一些兼职,是否要放弃一部分创作。

探讨生死的影像作品《始终》
这些年大众对女性艺术家有更多的关注,发声渠道变多了,社交媒体上也有更多的消息,甚至女性艺术家拍卖近两年来也有了不错的成绩。大家聚在一起都会开玩笑说,是不是我们终于可以养活自己了。

岳明月在无题空间驻地创作纤维艺术本身很大一部分创作都和女性运动相关,因为缝纫这项技艺是和最原始的、最女性的、最家庭的事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是发自内心地沉醉在刺绣机能做出的各种各样的肌理里。红纱系列还在继续,还有更多的身体上的、材料上的、工艺上的、题材上的想做的东西,今年计划做与女性劳工相关的作品。
我是通过这些创作,来不断了解自己和自己相关的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