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疯掉的黑皮在南京路广场的正中央,在众目睽睽之下撒泼打滚,而他背后的大屏幕上放的正是《大闹天空》的片段。
太上老君把孙悟空拿下的时候说“该死的猴头,这下你该知道了吧,这就是反抗我的下场。”
最后黑皮也被打趴下了。
周围看热闹的人围了一圈,耳朵里传来了一段旁边商场播放的音乐,宋祖英的《好日子》。
像是声画错位的两个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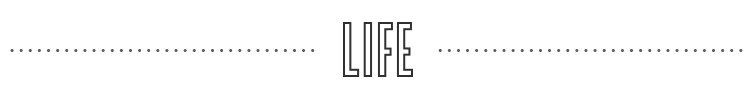

《南京路》是导演赵大勇的一部纪录片作品,记录的就是发生在上海南京路步行街上的人和事。 只不过他拍摄的并不是那些打扮精致的游客和灯红酒绿的景象,而是在这条街上靠捡垃圾、偷东西、卖唱要饭为生的人。 在这部片子里,你会看到镜头紧跟着那些人的身影,站在他们的视角凝视他们。 无论是他们半弯着腰把脑袋钻进垃圾桶里捡瓶子的时候,还是他们垫着破布睡在街角的时候,摄像机始终都以平视的角度进行拍摄。

透过这种视角,我们看见了一些鸡零狗碎的生活碎片,和一种存在于“人群之下”的社会群像——
比如一家祖孙三代在困苦里挣扎。
爷爷用轮椅推着残疾的爸爸,爸爸坐在轮椅上吹曲子,年幼的小男孩跟在旁边,手里抱着一个用来收钱的塑料碗。
路过的人群好奇地打量他们,大人们低头看着佝偻着身子的老人,被抱着的孩子也低头望着轮椅旁的男孩。

在这里,生活的底线全都被打破。
当清洁工人拿着大水管清理街面时,有人从角落里冒出来,蹲在路边开始洗衣服,不需要肥皂或洗衣粉,他们能搓多久完全取决于冲水的时长。

睡觉的地方,每个星期都要换好几次。
下雨的时候躲进商场角落里,天热的时候睡在露天天桥上,运气好一点能捡个纸壳垫着,运气不好的时候直接睡在地上。
就算睡不着他们也习惯性闭着眼,因为不想看着那些高跟鞋和皮鞋从眼前踩过去。

在南京路这条街上,他们已经习惯了在人们俯视的视线下讨生活。

片子里有一幕是仰角拍摄。
楼上西餐厅的人在优雅地吹萨克斯,路上行人站着在说话,人群之中,他们缩着肩膀低着头,身体被塞满塑料水瓶的垃圾袋压得很底。

在这些繁华与热闹的夹缝里,
他们走在人群之中,却也活在人群之下。

尽管他们已经习惯这样的生活,
但那些自上而下的注视却像是有实体的刀子一样,逐渐割掉了他们身上的某些东西。
首先是衣服鞋子这种无关紧要的。 如果你足够细致就会发现,那些刚刚从农村来到南京路的人,往往衣着整齐和普通路人没什么两样。
即使要靠乞讨度日,也会穿上一件白衬衫。

有时候被人骂“你他妈乡巴佬要饭的”。
他们会很气愤,会操着一口方言味浓重的普通话顶回去:“你们城里人以前下放到农村还不是要住我们乡下人都不住的牛棚。”
他们用这种方式换取一丝心理平衡。
但如果是像黑皮这种,在这里呆了好几年的人就完全不是这样。
除去最冷的一两个月,他几乎不穿上衣,每天光着膀子挤在人潮拥挤的步行街捡瓶子,有时候为了一个易拉罐,他能把脑袋完全塞进垃圾桶里。

路人嫌他脏,一边骂他一边躲远,黑皮也无所谓。
有一次一个孩子拿个矿泉水瓶子丢他,瓶子里剩下的水散到脸上,他什么也没说,把瓶子捡进麻袋之后,甚至开心地笑了起来。
管废品的老李的话说他:“黑皮脑子太傻了,话也不会说也不知道丢脸。”
但对于黑皮来说,丢脸有什么?丢脸一次能换来几分钱,就值了。

大胖子在南京路呆的时间比黑皮还久,他也不爱穿衣服,不过相比黑皮的沉默寡言,大胖子更活泼,是南京路上的“名人”。
每次喝多了,他就把塑料瓶放在耳朵边假装“大哥大”,煞有其事地说自己是黑社会大哥:“等我发了财,我们就去泰国、去美国好不好?”
 就算没人听,都能自言自语好久。
就算没人听,都能自言自语好久。要是有人看,他就更来劲,一段又一段顺口溜不重样,嘲讽权贵,嘲讽整日的所见所闻。
有时候还爱编排故事。
说在步行街看到女的跟老外亲嘴,睡一晚上五百块,而自己想要赚这个钱捡瓶子得捡到死;
说西游记里孙悟空上天去当弼马温,结果中了天庭的计大闹天空,最后失去踪迹不知死活。
每个故事的结局,大胖子都要哈哈大笑,给别人判定个生死:“中国男人都死光啦!,孙悟空也死啦!都死了死了!”
这个人仿佛已经钻进了他自己所建立的那个精神世界,风马牛不相及的故事,他试图以一种幽默的方式来消解掉自己的痛苦。

对于我们来说衣服代表着体面和尊严,但在生存的压力面前,体面和尊严是最没用的东西。
甚至会成为负担,要面子的人饿死,不要脸才能活下去。
所以后来,乞丐丢掉累赘的衣服,开始装疯卖傻赔笑讨好,黑皮也变成了疯癫的胖子。
他们在南京路生活,不断丢掉一些东西。

除了衣服,他们慢慢失去的,还有名字和声音。
在南京路,没人在乎你叫什么,大家都用对方家乡的地名或身体特征来称呼彼此。
黑皮,胖子,还有安徽和湖北。
安徽是个二十岁的年轻男孩,每天从黑皮这些人手中把废品零零散散地买来,再卖给大量回收的人。
收一个塑料瓶子再卖出去的利润最多就两分钱。虽然是“中间商”,但大多数时候忙一整天连饭都吃不饱。

湖北则更“聪明”一些,他不捡垃圾也不倒卖废品,而是靠“偷东西”生活,街上的路灯、电线、铜牌在他眼里被换算成等价的青菜或者荤腥。
幸运的时候,几句臭骂能换来一碗“青菜”,如果想开荤就得最好被抓进局子的准备。
据他回忆,曾经最风光的日子是在偷了一个奔驰车的车标之后,虽然最后被抓住坐了一年多的牢。
但湖北说:“挨打也值了,那是唯一一次我觉得自己活得像个人。”
紧接着,他又马上解释,其实每次偷东西都不是故意的,实在是饿得不行了,平时大部分时候是绝对不会偷的。
偶尔会出一些意外,不偷就得饿死。至于是什么意外,湖北不愿意说,旁边的人指了指他脸上的疤。
据说,那是被人用匕首划的。
他们这样的人,为了活下去就得学会昧着良心生活。

经常和湖北在一起的还有一个看起来十多岁的男生,他们叫他“小孩”。
明明正是上学的年纪,小孩却进去被关了五个月,前几天才从牢里放出来。
问到家里的情况,他想了好一会才慢慢说起来。
刚好,背后十字路口的汽车鸣笛和餐厅的管弦乐声同时响起,
镜头里只能看见小孩的嘴巴在动,至于他具体说了什么,已经被淹没在一片嘈杂声里听不见了。
可能关于父母,可能关于曾经的生活,也有可能是关于未来的设想......
年龄小的好处就是还能对未来充满希望,
尽管大人们都知道这未来注定黯淡无光。

这这样的场景还有很多——
“刚来的时候,觉得来到大城市感觉不一样了,看什么都充满希望,想着一定要混出个名堂,结果不到一星期,就发现......”
“那次我捡了整天瓶子只卖了 5 毛钱,在路上看见东方明珠的广告,我就把买馒头的 5 毛钱换了一张票坐轮渡去了浦东,
结果看到东方明珠觉得也不过如此,那时候真的好难受,一顿晚饭就这样打了水漂,我本来以为......”

他们的声音逐渐消失在南京路来来往往的喧闹声里。
看起来好像理应如此。
这就好比你走在路上,一个流浪汉自言自语说自己发生了什么事,
就算他喊得再大声,也不会有几个路人真的注意到他说了些什么。
最多瞥一眼就过去了。
他们发现什么,他们难过什么,没有人听得见,更没人会在乎。

《南京路》,越看到后面,压抑的感觉越重。
这种压抑不是来自他们每个人所经历的苦难,而是那些和他们本身无关的真实日常。 黑皮和安徽每天都要背着的,比人还要高出大半米的废品垃圾包。

总是盖过他们说话声的,各种汽车鸣笛和路人指指点点的说话议论声。

时常占据一大半背景版面的,各种小洋楼和楼上衣着精致的人们。

在这些镜头里,捡垃圾的人总是被放在了画面的最底下。
他们就这样被垃圾压着,被杂音压着,被人群压着,永远无法直起腰版。
他们虽然生活在这里,但他们从来不属于南京路。或者说南京路从来不属于他们。 另一方面,在他们身处的底层社会内部,似乎也逃不过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互相之间,也在时刻为了占据和拥有的资源而斗争。

捡瓶子和收废品的人因为几分钱打起了架,警察不愿意管,用一句“你有钱吗?没钱打什么架?”把他们堵在门外。
离开了警察局,他们接着打。
拉三轮车收废品的人经常抢用手推车收废品的人的生意,抢不到的人就带着几个自己这边的人去搞坏对方的拉车。
你来我往,从来不曾停过。

脑子灵光的聪明的人骗老实人赚来的钱,唯一一个被黑皮当成“朋友”的阿桥,某天晚上带着他们俩一起挣来的全部家当 900 块钱跑了。
阿桥的债主找上门来,最后狠狠打了黑皮一顿。

每天都有人从南京路消失,离开猝死,或者变疯。
最近一个变得不太正常的人,是黑皮。
阿桥离开之后,他开始整日酗酒,有一次喝醉了想要给别人劝架,刚好遇到警察过来,发酒疯的他把警察的帽子给摘了,结果一同被抓进了拘留所。 大概是被关进去后又挨了牢头的打,出来后黑皮走路一瘸一拐的。
也是从那儿开始,原本不爱说话的他变得跟胖子一样,整天絮絮叨叨,但没一个人听得懂他在说什么。
有时候走着路突然就哈哈大笑起来,后来又因为偷铜牌和打架被反反复复关进了拘留所几次,黑皮的精神状态也越发不正常。

人人都说“黑皮疯了”。
黑皮最后一次出现在片子里,也是在结尾的时候。
他正提着袋子走在步行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开始放声唱歌,
然后又抱着柱子转圈,在绿化栅栏里钻来钻去,坐在垃圾桶上又跳下来......

就像一个撒泼的野猴子。
与此同时,在他上方的广告屏幕里,正播着《大闹天空》里太上老君孙悟空拿下的那一段,他对孙悟空说:
“该死的猴头,这下你该知道了吧,这就是反抗我的下场。”
该死的黑皮也被打趴下了。
在南京路他不是第一个,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参考资料:
纪录片《南京路》3 号厅检票员工《自焚,猝死,底层猪,外卖员,流浪汉,社会达尔文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