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名经济学家并不是个轻松差事。企业高管抨击他们没有足够精确地计算成本和收益,而利他主义者则指责他们汲汲于成本和收益。对政客们来说,经济学家可谓大煞风景,因为他们不会允许前者承诺繁荣却不付出相应的牺牲代价。甚至包括乔治·萧伯纳 (George Bernard Shaw) 和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 在内的一批才华横溢的文人作家都曾在创作之余对经济学家发表过一番不恭之词。事实上,自从卡莱尔将经济学称为“阴郁的科学”(dismal science)以来,经济学家就一直是千夫所指。
然而,经济学家却感到自己蒙受了不白之冤,因为他们通常并 非恶行的始作俑者,而只是坏消息的信使而已。他们所传递的信息 也很简单直白:人类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我们不再身处伊甸园, 这个世界也并非到处流淌着奶和蜜。我们必须做出各种抉择,是要 更清洁的空气还是更快的汽车,更大的房子还是更大的公园, 抑或 是更多的工作还是更多的娱乐。经济学家并不会告诉我们哪些选择 是不好的。他们只是说,我们不可能鱼与熊掌兼得。世事总有选择 取舍,而经济学正是关于选择的学问。它并不会告诉我们具体该选择什么,而只是帮助我们理解自身选择所带来的后果。
当然,伟大的经济学家并不甘于仅仅做个信使。尽管他们曾备受嘲讽,甚至被冠以各种揶揄味道十足的诨名——笨蛋斯密、秃头书呆子穆勒、锦衣玉食的公子哥凯恩斯等——但他们的动机却无可指责。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经济学家虽然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遭受如潮恶评,但正如凯恩斯曾指出的,这门学科中大多数杰出实践者的初衷均是出自善意,是为了寻找改善世界的方法。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尤其认为,经济学应该是一门将精于盘算的科学与对人的奉献加以调和的职业。
中世纪有三大职业——旨在保障身体健康的医学、旨在实现政治健康的法学以及旨在塑造精神健康的神学——而马歇尔则希望经济学能成为第四种崇高的职业,其目标不仅仅是为富人服务,而是为所有人提供更好的物质健康。马歇尔以过人的勇气,试图在两种强有力但又有各自缺憾的经济学发展趋势之间进行调和:一种趋势让经济学成为脱离实际用途的数理经济学, 另一种则是抛弃理论反思的纯粹情感激进主义路线。他在剑桥大学努力建立的相关课程将最具科学头脑和最富激情的一群人聚集在了一起,其中最为出色的代表便是凯恩斯。
将经济学与现实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最紧密纽带始终是政治。事实上, 直到 21 世纪, 经济学也还被称为“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几乎所有杰出的经济学家都曾在政府的某个层级任职。其中大卫·李嘉图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两人还曾在英国议会的选举中赢得席位。在这些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身上,我们自始至终所看到的,不仅有科学兴趣所闪出的火花,而且也不乏激昂澎湃的热情。 在无数平平无奇的演算符号和统计数字之后,我们仍能从中窥见他们惊世骇俗的观点。
纵观经济思想史,我们看到政府和经济学家之间时而对抗时而合作的趋势。当亚当·斯密痛斥欧洲王室与商人之间的不伦结合时,现代经济学开始崭露头角。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和托斯丹·凡勃仑(Thorstein Veblen)这几人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 就是他们都意识到商人喜欢利用政治来为自己寻求庇护。
斯密在一篇著名的声明中告诫人们,商人们彼此会面,绝大多数都是为了密谋算计消费者。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在今天,那些在地方商会会议上滔滔不绝鼓吹自由市场的雄辩者一旦有机会,就会想尽办法确保自身的垄断地位,与政府签署独占合同,或支持通过保证其自身收益的法规。值得庆幸的是,政客们并不会对商人有求必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社会党领导人承诺通过工会联合和国有化,即可实现英国的繁荣,令其成为人间乐土。但事与愿违的是,英国经济却从此每况愈下。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的一位传记作家曾讲述丘吉尔在下议院外的男厕偶遇工党领袖的一则轶闻。那名工党领袖先进了厕所,占了一个小便池。过了一会儿,丘吉尔也进来解手,看见他的对手也在,他却没有立即解手,而是干站在一排小便池的另一端。“今天感觉咱们彼此不太友好啊,是吧,温斯顿?” 这名工党领袖见状问道。“没错。”丘吉尔吼道,“因为你每次看到什么‘大家伙’,就想着把它国有化!”
大多数美国总统对经济学原理几乎一无所知。约翰·F. 肯尼迪(John F. Kennedy)曾经承认,他之所以能记住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管控的是货币政策而不是财政政策,仅仅因为时任委员会主席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 的名字和“货币”(money)一样以字母“M”开头。显然,在肯尼迪的任期内,像沃尔克(Volcker)、格林斯潘(Greenspan) 或鲍威尔(Powell) 等人恐怕要与这一职务无缘了。
对经济学家来说,选战大概是最难挨的时刻。每当一位政治家向其选民允诺更多的人造黄油和军火弹药时, 经济学家都必须站出来警告这些承诺可能招致的灾难性后果。经济学家在提高民众经济素养方面取得的任何进展,都可能被候选人不切实际的胡言乱语在转瞬间彻底抹去。选举年的演讲就相当于黄金时段电视节目的政治版本。当一个总统候选人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他不能让自己看起来比《老友记》(Friends)中的乔伊·崔比安尼(Joey Tribbiani) 更老于世故。当然,对于一些政客来说,这算不上一个很大的挑战。
由此不难看出为什么政客会误解他们的经济顾问。经济学家彼此之间沟通所用的语言和他们对公众宣讲的语言截然不同。这些同行间说的是“模型化”的语言。在试图解释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时,他们必须化繁为简,首先简化归并出在任何给定的时间里最重要的因素,因为每一个经济现象都可能受到成千上万个事件的影响。
例如,美国消费者的支出水平可能取决于以下因素:天气、音乐品位、体重、收入、通货膨胀率、政治运动以及美国奥运代表队的成绩。为了对这些因素加以孤立并对其进行重要性排序,经济学家必须设计出相应模型,将无穷可能原因中的部分排除在计算之外。最出色的经济学家,正是那些最持久、最稳健模型的设计者。
当然,所有的科学家都必须构建模型。多年来,物理学一直以牛顿万有引力模型为基础。天文学家则仍在沿用哥白尼提出的天体运行范式。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经典之作《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便追溯了这些模型的发展历程。
那么,为什么经济学的建模比这些“硬科学”(hard science)更困难呢?此处可以举个例子,想象一个外科医生在给一个患者做肾脏手术。在检查完 X 射线摄影胶片后,外科医生知道了患者的右肾位于其结肠下方两三厘米处。
然而,不妨设想一下,当外科医生切开一个切口时,肾脏却改变了位置,这会是什么情景? 而这正是经济学家面临的状况,当他们孤立原因并估计其影响时,影响的程度就会发生变化。随着人际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化,我们进行科学探究的主题也在不断流变之中。因此,经济学可能不是一门“硬科学”,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门“容易的科学”。 因为它是如此变动不居,以至于对其所做的研究如同刻舟求剑。难怪凯恩斯勋爵坚持认为,成就经济学大师所需具备的一系列特质,比成为骑士甚至圣徒所需更为罕见,他写道:
他必须既是数学家又是历史学家,同时还是政治家和哲学家。……他必须理解符号的意义,同时又能诉诸语言。他必须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从一般性的角度去思考特殊性,并同时触及抽象和具体层面。他必须在研究现在的同时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他既要考量人的本性,又不能遗漏人所制定的制度习俗。他必须富有追寻目标的激情而又排除先入之见。他要像艺术家一样超然物外,但有时又要像政客一样与世浮沉。
经济学的源起
当我们准备钻研经济思想史时,应该从何处起步呢?我们可以从《圣经》(Bible)开始,其包含了许多关于土地、劳动力、资本和债务减免的表述。但《圣经》所呈现的更多是清规戒律而非细致分析。虽然亚当·斯密的名字和他的道德立场都来自《圣经》,但显然该书并未给他的经济理论提供多少灵感。
我们也可以将对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探讨作为起点,他曾以雄辩有力的言论赞扬私有财产,并谴责单纯为财而敛财的行为。但亚里士多德对经济学的了解仅限于认识到时间是一种稀缺资源而已。因此,他将自己的时间更多投入到了哲学研究和亚历山大大帝的教育之中,而不是经济理论。这种选择也算卓有成效。亚里士多德无疑仍是哲学巨擘之一,但即使冒着得罪那些视亚里士多德为偶像的西方文明史公开课拥趸的风险,我们也得承认,他在经济学科领域只能说建树甚微。
在中世纪,神学家们也会讨论经济问题。天主教的经院学者会围绕市场中的正义和道德问题而争论不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构建了“公正价格”(just price)的学说,并完善了教会对高利贷的看法。《旧约全书》(Old Testament)明确禁止向同一群体内部成员发放有利息的贷款,而中世纪的神学家则试图将利息的不同组成部分,如风险、机会成本、通货膨胀和不便补偿等一一分开,以打破这一严格禁令并使其有机可乘。
神学家们面临着痛苦的选择。 一方面,如果他们继续墨守挑战正当商业活动的正统圣经阐释,经院 学派就会成为无本之木,因为许多人甘冒神罚的风险也想着撞大运赚上一笔。但另一方面,如果神学家只是轻易宽恕乃至纵容一切形式的重商主义,他们作为教会领袖的信誉便岌岌可危。
他们的大部分经济理论,设计初衷都是在世俗性和神圣性之间求得两全。这种立场对经济学研究而言既显憋屈难受,也绝对谈不上有利。他们之所以谈论经济,只是出于身为上帝牧者对“迷失羊群”的职责罢了。 但是他们的职责其实是引导羊群前往天堂,而不是为他们谋求更高的生活水平。而当新教徒们的出现让原先还算划一的羊群分裂成不同小群体后,这任务就变得更加难办了。
上文提到了重商主义者,对于他们,我们可不能就这么一笔带过。一般而言,这些人是 16 世纪至 18 世纪侍奉欧洲君主的一个作家和宫廷顾问群体。他们并没有一本共同的“正典”,并且有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随着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的王室竞相巩固自身国界,同时又跨越重洋争夺海外殖民地,律师和商人们开始为各国国王和王后就如何管理经济出谋划策。
对此进行回顾总结,我们便可以列出他们的建言中经常出现的几个原则:首先,一个国家应该通过向王室的忠诚臣民授予垄断权、专利权、补贴和特权来维护国家内部秩序。其次,一个国家谋求殖民地的目的应该是获取贵金属和原材料,这些是衡量国家财富的出色指标,也可以为征服战争支付开销。最后,一个国家应该限制其对外贸易,使其制成品出口大于进口。通过持续的贸易顺差,就可以从债务国身上获取黄金(财富)。
因此,在重商主义的指引之下,我们看到国家纷纷致力于开疆拓土。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国家对其内部经济的控制日趋收紧,借助行业公会、垄断和关税,政治宠臣们牢牢把持着国家的经济权 柄。在一些国家,这种控制所涉及的范围更甚于其他国家。
在路易十四(Louis XIV)统治时期,其财政部部长让 - 巴蒂斯特·科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 对许多商品的生产进行了巨细靡遗的规 定,并赋予行业公会极大的权力。在一次令人惊叹的旨在展示皇权的活动中,他曾宣布来自第戎的织物都必须包含 1408 条织线!重商主义者为亚当·斯密树立了一个完美的批评靶子,因此我们似乎可以以他为起点,开启我们的现代经济思想探究之旅。
斯密从几个层面上严厉批驳了重商主义理论。
首先,重商主义者以金属货币和贵金属的多寡来衡量财富,而斯密则认为,真正的财富应该以家庭的生活水平的高低来衡量。成袋的金币未必就能换来成袋的食物。
其次,他指出财富必须从一个国家消费者的角度来衡量。将财富全部交由一国总理或阿谀奉承的商人一手掌控,这种策略对于这个国家的公民可能并非幸事。
最后,斯密认识到,个人的积极性、发明和创新能激发经济的更大繁荣。重商主义政策将垄断权和保护权肆意授受,结果只会使国家陷于瘫痪。这些言语可谓现代经济学的初试啼声。
我们该对经济学家不予理会吗?
自亚当·斯密时代以来,真正脱颖而出的经济学大师可谓凤毛麟角。主流经济理论也并不能放之四海皆准。令情况雪上加霜的是,今天的经济学家陷入了一种前后不靠的境地:回顾过去时,他们难以对 20 世纪 70 年代初至 90 年代初生产率增长为何出现下降作出解释,而放眼将来时,他们又无法设计出在 21 世纪中期偿还政府债务的最佳方式。
不过,经济学家们对有一点倒是十二分的赞成,那就是国家和个人若无视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就是在冒愚蠢的风险。 一个国家若是为唤回重商主义时代的昔日荣光而提高贸易壁垒,最后只会令其本国消费者受池鱼之殃。农产品价格高企的国家同样会伤害自己的消费者,并只能眼睁睁看着过剩的谷物在仓库里腐烂。对于这两点,几乎没有经济学家会有异议。然而,能将这两点听进去的政客却是寥寥无几。
即使政府并不总是采纳经济学家的建议,我们也可以指望经济学家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目前达到了什么水平,将来可能会达到什么高度。自工业革命令英国大放异彩以来,美国人就一直期待着自己的国家能强大富饶。我们总是将现在看作一个卑微的起点,去希冀未来的持续进步。然而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人类的进步从来就不会持续不断。每个年头都可能成为全新黑暗时代的序幕,而如 今的工业化国家集团每次都逃过此劫,这就等于是在不断为人类创造一项持续发展的新纪录。看看法国史学家乔治·杜比(Georges Duby)笔下 11 世纪的欧洲吧。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这可怕的几十年时光,是发生在古希腊、古罗马、古巴比伦和古埃及等文明荫庇之下相对富裕繁荣的年代之后,而不是之前:
……公元 1000 年的西方世界,一个饿殍遍地的蛮荒世界,人丁稀薄,但对当时的社会而言仍然过剩。几乎两手空空的人们挣扎求生,却只能沦为喜怒无常的大自然的奴隶,沦为因缺乏耕作而贫瘠不堪的土地的奴隶。当农民播种一粒小麦时,即使年景不算差,也从不会期望收获三粒以上;所谓的“好年景”不过意味着复活节之前可以吃到面包。在这之后,他将不得不靠草皮树根之类从森林和河岸边搜集的充饥之物勉强果腹,还得空着肚子进行繁重的夏季劳作,然后疲惫不堪地苦苦等待收获……
有时,当大雨导致土地漫灌,妨碍了秋耕的进行,或是当暴风摧毁了庄稼,日常性的食物短 缺就会发展成饥荒,掀起一波致命的饥饿浪潮。那个时代的编年史家都描述过这样的饥荒,无一不是触目惊心。“人们互相追逐只为以对方为食,许多人割断了同伴的喉咙,就像饿狼一样饮其血,啖其肉。”
发达国家有朝一日会不会再次经历这样的恐怖梦魇?它们是否会重蹈那些第三世界邻国的覆辙?即使是凯恩斯这样的经济学大师,在他最为离奇荒诞的预知梦境中,恐怕对此也无从知晓。但我们实知道,伟大经济学家的目标就是避免我们堕入这黑暗的深渊。
令人感佩的是,伟大经济学家所创立的那些理论中,有许多至今仍能为我们所用。他们所留下的睿智理论,几乎每一条都有着即使在今天也切实可行的细节,或是时至今日也能找到可做比对的示例。
本书试图通过对主流经济学的探究来寻求这些大师们的智慧,并致力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谁首先获得了这些洞察,并建立了这些持久耐用的模型?我们可以以他们为师,从他们身上获益良多。
书中一些示例取自当代,如此行文其实只为博君一笑而已。大卫·李嘉图当然不曾真正接触《吉利根岛》(Gilligan’s Island )一剧中的角色并对其解释比较优势法则。我在书中以这些落难漂流者为例也并非不敬,只是希望能以一种生动的方式为读者理解这些晦涩难懂的范式提供些许帮助。须知经济学也不一定是枯燥呆板的。
既如此,为什么不让这些已故的经济学家自己出场,来扭转他们所背负的恶名,亲自为我们现身说法,并以这种生动有趣的形式在那位指斥经济学“阴郁沉闷”的卡莱尔那里扳回一城呢?想来这些经济学家若真在天有灵,他们大概也宁可笑对我们这种看似冒犯的引用,而不愿因为自己的努力被世人遗忘而失望沮丧,或因为担心人类社会重蹈 11 世纪的覆辙而在自己的棺材里辗转难眠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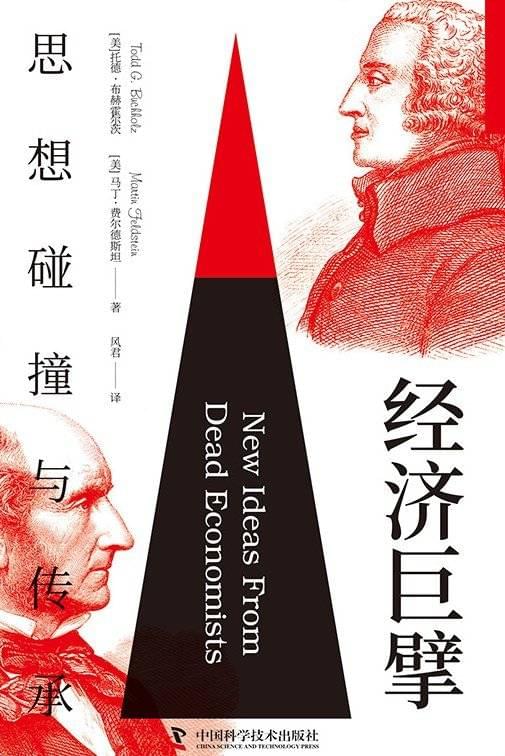
作者: [美]托德·布赫霍尔茨(Todd G.Buchholz) / [美]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
出版社: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品方: 中科书院
副标题: 思想碰撞与传承
译者: 风君
出版年: 2024-1
本文摘编自:《经济巨擘:思想碰撞与传承》,作者:美]托德·布赫霍尔茨(Todd G.Buchholz)、[美]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