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话·世界》是一部交缠着许多灰色地带的电影。起初,这部2022年在中国台湾首映的电影被引进大陆院线时,很多观众以为,它是一部将林奕含的经历和《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复刻下来的影视化作品——电影的主题是师生恋,并以权势关系下的性侵犯为主线展开情理与法理的是非争辩。
自2017年4月27日被警察宣告“本案,死者,绕颈窒息”后,林奕含和她笔下深具自述性质的房思琪就未曾被公众忘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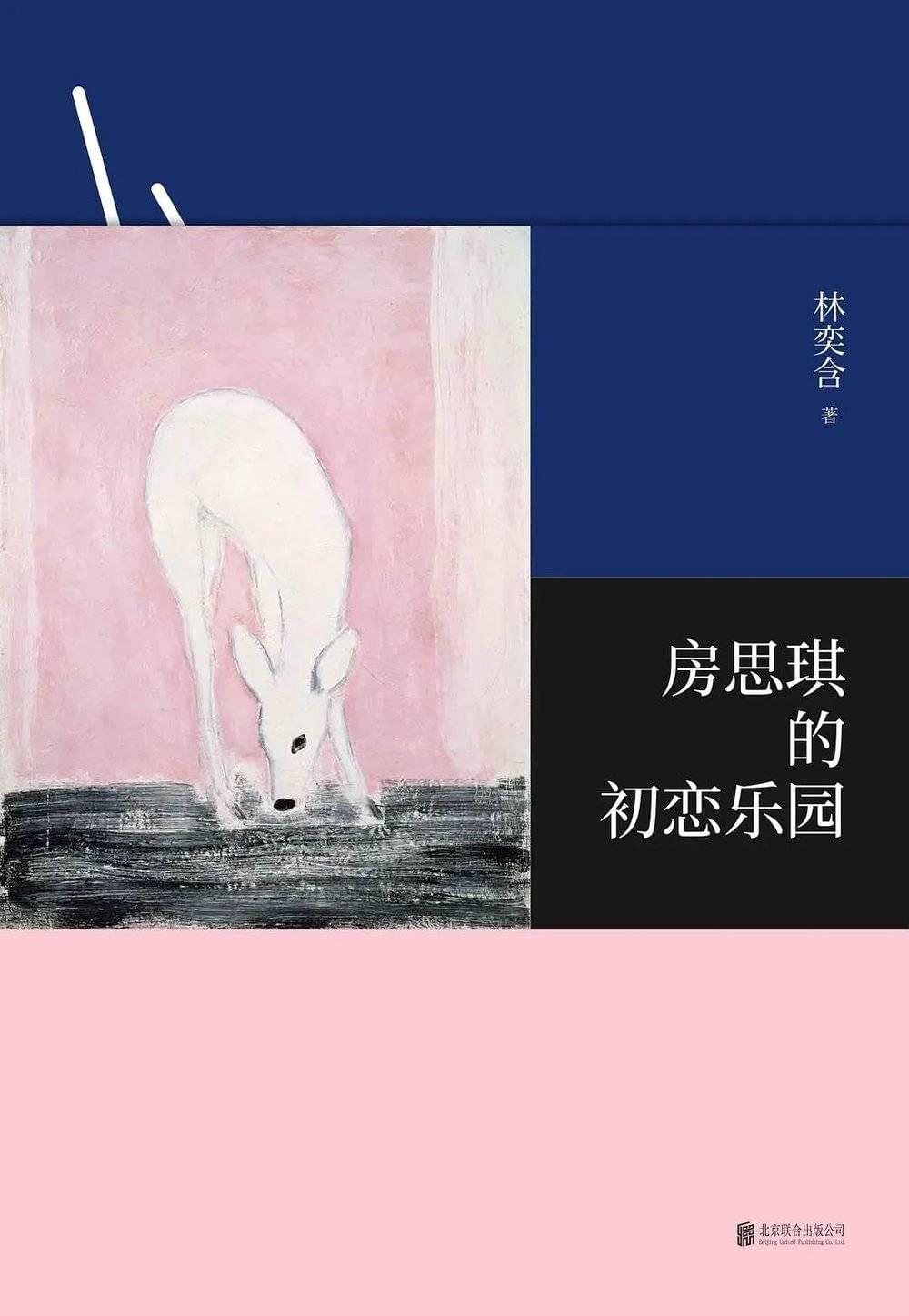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林奕含 著
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这本自传式小说里,补习班老师李国华以巧言令色,利用13岁少女房思琪对文学的一知半解、对人生险恶的不设防范,对她实行了5年的诱奸。
林奕含最终既绝望,又似乎替对方将自己的本能和直觉劝降,说这是“一个女孩子爱上诱奸犯的故事”。
现实中,林奕含屡屡尝试控诉曾侵犯自己的老师陈国星,甚至对自己深恶痛绝,然而,她的抗争并没有得到好的结局。“走在路上我还看得到他的招牌,他并没有死,他也不会死,然后这样的事情仍然在发生。”
一、隐蔽的语言系统,只对天真奏效
《童话·世界》里的女孩们跟房思琪经历相似。她们被补习班老师汤师承以“非暴力”的形式侵犯,逐渐陷入对方用语言和“尊重”罗织的陷阱。
如果李国华是将“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是从刀子般的月亮和针头般的星星那里掉下来的吗?你以前在哪里?你为什么这么晚到?……有时候我想到我爱你比爱女儿还爱,竟然都不觉得对女儿抱歉。都是你的错,你太美了”这套话术作为一种粉饰暴力的修辞,那汤师承就是将更低端、更幼稚却屡次在女学生身上成功的童话故事,作为软化无耻欲望的广告词。
没有一个有着理智判断的成年女性会真的相信汤师承引诱女学生的伎俩——讲童话故事。汤师承带着女学生陈新走进三面合围的居民楼,说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来这里,人家说井底之蛙是个笨青蛙,但是我觉得,它是全世界最快乐的青蛙。呱呱。”
侵犯发生后,他说:“小新,你记得青蛙王子的故事吗?湿湿黏黏的青蛙等待公主来亲吻。只要信守承诺,做那件事也是很美好的。你不觉得童话故事很美吗?”
当性侵害多次发生后,汤师承被提起告诉。在法庭上,另一个被侵犯的女学生被辩护律师步步紧逼。“请问证人,你被强暴后有什么感觉?事发隔天,是否正常上学?”“是。”“是否依然在被告的补习班补习直到联考结束?”“是。”“所以你被强奸后仍然正常上学上课,直到半年后,你才觉得怪怪的吗?”女学生的声音既无措又显得天真:“老师说他爱我。他说他是青蛙王子。女生要蜕变的话,就要接受王子的吻。”
童话故事是汤师承搭建的邪恶的认知框架,以及只流通于涉世未深群体的语言系统。作为一个中年老师,他必须用能让女学生感到没有沟通障碍的,甚至没有年龄障碍的语言,才可以完成最初的捕猎筛选,请天真者或欣赏、感动于成年人用天真来讨好自己的女孩入瓮。
这种语言系统被女学生全面理解、吸收并认可,但当它被曝光于真正的成年人把持的现实世界时,就会失灵。
“女生要蜕变的话,就要接受王子的吻。”成人世界会认为,相信这套说辞的少女们要对自己被侵害的事负起责任,“无知和天真”是她们的原罪。
因此,当汤师承的律师频频发起质问时,已经被洗脑的少女用这套话术来解释自己“不反抗”的行为,只会引来听审群众的不理解和轻视。
汤师承只会在少女们的世界里发行这种天真的语言货币。他一定深深知道,这套语言货币流通的局限性,会让他的侵犯行为变得隐蔽。
因为对未成年人得手太多次,面对自己的律师时,他也会使用这套语言货币,但表情会变得更加市侩、精明、冷漠。
“张律师,你小时候有看过童话故事吗?你知道小红帽为什么替大野狼指路?小红帽和大野狼明明上了床。为什么最后受惩罚的却是大野狼呢?”他此时的表情,和《周处除三害》里邪教尊者诡辩“一场天灾,一场地震,就死多少无辜的人呐。你恨过天吗?恨过地吗?我们只不过多杀几个人,那又怎么样呢?是不是?”的表情,别无二致。
律师们当然不会相信童话故事,他们能听懂的语言是高昂的代理费。“没有证据的性侵算什么性侵啊?”接下案子的杜律师从容地说。
新手律师张正煦从开始的质疑到被前辈杜律师说服,呈现了一种年轻人学习新事物的“高效”。他干脆对汤师承表示:“她(要求公开审理)的目的很明显,不管她说的是真是假,舆论都足以判你死刑。对她而言,这场官司的目的已经不在输赢了,她只想毁掉你。”
“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这就是爱情吧。我们之前一直认为,你和她必须是爱情,但是,如果她是一个荡妇呢?证明你和一个清纯的女学生谈恋爱,跟证明一个荡妇勾引有妇之夫,哪个容易一些?今天她用道德审判你,我们就用道德审判她。”
这正是林奕含曾面对的现实:当她拿出勇气,要从陈国星那里夺回自己的话语权和活下去的希望时,部分舆论将矛头指向她对有妇之夫陈国星犯下通奸罪,需要向陈太太道歉。
二、中年人的“巧言令色”
在电影里,汤师承这个人物从头到尾看下来,没有任何值得人喜欢的地方。这个角色的扮演者是李康生,他在电影里塑造的就是一个普通中年人的形象:说话节奏很慢,对女学生常有一种委屈的、软塌塌的、老实人的语气和表情——“你如果怕我可以停下来”“老师配不上你”“我们是真的在谈恋爱耶”。
电影里只交代汤师承是个段考名师,有自己的补习班,具体有名在哪里、他的讲课技巧和知识储备有多高明,并没有点明。引诱女学生时,他也不是析辨诡辞的人物,只是重复讲青蛙王子的故事和使用“我爱你”“我们之间是爱”这种说辞,像低劣的、没什么信息含量、主打入侵大脑、争夺注意力的广告片。
这个人物的单薄,或许是电影没有描述充分,又或许是有意为之——有些侵害比我们想象的更容易发生,而侵害者并非多高明、多有人格魅力甚至多聪明、多有力的捕猎者。
电影里有一个情节多少填补了这个角色的模糊之处。新的侵害发生后,汤师承去找受害女生郭诗琦的父亲谈和解。他找到郭父的擦鞋铺时,对方一开始没认出他,还夸他脚上穿的是双好鞋。等终于被认出来时,汤师承一副为人着想的柔软语气,但身体还是居高临下的姿势:“郭先生,对不起。这样做,对琦琦好吗?”
过了几天,郭父竟然倾向于和解,并承认自己不会教孩子,也有错——孩子头发剪得这么短,不像会在补习班好好读书的样子;汤老师也不像是会使用暴力的人;而正义是什么,有什么用?
电影里并没有呈现汤师承如何向郭父施压,但他给对方留下了一种“非暴力”的形象,这是他的“软刃”的又一次成功。这种“软刃”让整部电影游走在影影绰绰之间,事情的真相在谎言和柔软的姿态里起伏,造就连受害者都难以识别、难以笃定的迷茫灰色。
郭诗琦最终选择和解:“我喜欢老师,真的。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但失恋,本来就很痛苦不是吗?”这就是林奕含说的“巧言令色”,最终成为暴力的画皮。
“巧言令色”不仅仅停留在精美的语言陷阱层面。在日常生活中,有适用于不同人、迎合不同人的“巧言令色”,或许是“权威”“稳定”“知名”,或许是“我尊重你”“我爱你”“老师配不上你”“我不会强迫你”。
三、一再发生的事件
《童话·世界》导演唐福睿当过律师。一开始,他就希望在这部讲述性侵犯的电影里,由一个律师主角带观众走过所有法律程序,经历被害人的每一个阶段,甚至包含他作为加害者的律师那一段。
张孝全扮演的张正煦就是导演安排的主角。做新人律师时,他忍不住探寻事件的真相,但后来还是被前辈和前辈的成功履历劝降,为汤师承辩护成功。
20年后,他发现,妻子所帮助的性侵受害人,施暴者仍是汤师承。此时,他成为一个想劝受害者坚持告到底的人,否则会有“更多人受到伤害”。他想改写过去作为“帮凶”的经历。
接受《放映周报》采访时,唐福睿说,念法律的,可能七八成都是很自负的,才会想用法律试着改变世界。他上学时亲眼见过美国很多受害女性站出来指控施暴者,看到幸存者、被害者分享自己的经历,后来成为李宗瑞性侵案件中某个被害人的律师。
这些经历让他在撰写剧本时,萌生出要呈现“最有争议的社会事件”的想法。在展示事件和庭审之外,他也用了很多心力去呈现人性的复杂之处——法律始终是有局限的,而故事会将人引入更远的地方。
“我们看主角张正煦一路好像非常努力,看似为了公平、正义的理想,但他更多是为了个人的东西,甚至不惜牺牲无辜的人和自己的家庭与事业,也要做到这件事情。我们就会觉得,那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一定很重要,或是一定能够改变什么——但实际上没有。
我这个结局想要传达的,就是片中的这种伤害,其实是很难复原的,基本上发生过,就会一直在那边。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张正煦的一厢情愿其实更突显了他的英雄主义和父权思想,就是认为女性必须要被他拯救这件事情——他到最后才发现这件事情。”
《童话·世界》出现了三位受害人,被侵害的情况不一样,处理被侵害的方式也不一样,且发生在不同时期。唐福睿觉得,自己拍的电影,反映的不仅仅是特定事件,而是重复发生的现象——电影拍摄结束的2022年,台湾出现了类似的“台中资优班事件”。
据当地媒体报道,台中市立大墩国民中学校长黄纪生被指控在担任台中市立居仁国民中学教师期间,性侵多名未成年女学生。这件事在20多年之后才重见天日。契机是当年8月,台中一名女子召开记者会,指控“黄姓导师”以辅导名义逼迫交往、权势性侵,甚至在她升上大学后还到她所在学院的留言板化名辱骂,使她多年来在焦虑症中备受煎熬。
她的父亲在知道这件事后,如梦初醒:“作为父亲,我却无知且无能为力,还糊里糊涂地对那可恶的狼师说些感谢尊敬的话,真痛心疾首!”
台湾媒体分析,这和过去台湾的集中式资优班办学模式息息相关。资优生和普通学生相比,展现了更好的智力水平和学业成就。
然而,在这种绩效和荣誉的长期压迫之下,学生们会对自身经历的烦恼、伤害噤声,以维持好学生的形象;老师的权威性也日渐稳固,甚至垄断学生话语权。
“台中资优班事件”被曝光后,唐福睿发现,自己在律师事务所工作时的一位同事,正是其中一位受害者的国中同学。在Verse的一篇报道中,唐福睿说,这位前同事羞愧地告诉他,同班三年,自己未曾察觉同学的异状,也没有发觉老师对特定的女学生做出过逾矩行为。
这份无以名状的巨大羞愧感,传递到唐福睿写剧本的过程中,成为他创作的动力。“因为,直到此刻才得知,周遭友人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经验,而自己却浑然不觉般活在另一个世界里。”
四、“法律的极限,就是故事的起点”
很多事情无法通过法律解决,《童话·世界》里的受害者之一陈新这么告诉张正煦。唐福睿没有给陈新安排一个“幡然醒悟自己被侵害”的时刻——陈新似乎是爱汤师承的,同时嫉妒于自己不是汤师承的“唯一钟爱”,而对这份童话之爱心生破灭。
在“侵害”之中,不仅奸猾的施害人认为存在“爱情”,被害人也觉得自己得到的是爱情,并且经历了“失恋”。这部电影带来一种类似《坠落的审判》的暧昧不明——即便法庭有判决结果,双方各执一词,且都很有说服力,但真相和事实未必就是故事的答案,因为人拥有着千丝万缕、难以厘清的感情和感受。
对于两位导演来说,背后的事实,大约也不是他们眼中最重要的电影内核。
“法律的极限,就是故事的起点”,唐福睿的这句话,比电影所呈现的内容意涵更丰富。“法律其实是有极限的,尤其是在人的感情上,当法律针对人的感情去做判断、惩罚的时候,界线在哪里?甚至,有没有可能是误判?”
在一次采访中,唐福睿提及曾被当地媒体报道的“许倍铭”案。“他(许倍铭)是一个特教老师,他的学生,一个七八岁、有智能障碍的小女生,说了童言童语,大家就认为这老师对她做了些什么事情。程序走了,法院也判他有罪,他就逃亡了,因为他认为自己是无辜的。
“后来,经过人权团体调查,确实程序有非常大的瑕疵。我不是在为这个老师说话,因为我们没有人知道事实,而且法院判他有罪。但是,我相信法律不是完美的,它一定有极限,它一定有误判的可能。这些其实就是(我)在写这故事的压力,不是美化这件事情,但是又不能够武断地分配角色给任何人。”
汤师承是可憎的——如果从电影的某些片段和成年人的风险常识来看。但或许,陈新和郭诗琦也没有说假话:“老师没有强迫我,每次看他开心,我也开心啊。”最难分辨的,就是人瞬息的、变化的、后知后觉的、不断成长或不断加固的感受。这感受有时异化了事实,有时又比事实更真实。
就像电影里探讨的“权势关系”,功成名就的杜律师问张正煦什么是权势关系,得到的回答是:上对下的支配,从属关系。“这么模糊的概念,基本上他们要怎么说都可以,不是吗?”
在法庭上,检察官说:“权力不是一个人能做什么,而是他能让人做什么,权力的作用不是只发生在性交的当下而已。”杜律师反问:“什么是曲意顺从?老师要学生写作业,学生不想写,但是还是要写?”
她援引了当地媒体1994年报道的一个案例:师大教授黎建寰四年前被女学生指控性侵,最新的进展是,教授的配偶起诉该女学生“通奸”,最终法院判决女学生有罪。判决理由是:被告虽为被动,但应抗拒而不抗拒,任其发生,以贞操于女性之重要性,应认为符合其意愿,当判通奸罪。
“贞操对女性而言是多重要的一件事,我们都知道。有反抗的机会却不反抗。这不是很可疑吗?女学生跟老师谈恋爱没有错,不是权势性交。”
很多事情和感受纠缠在一起,很多标签彼此汇合又矛盾,让人无法锚定自己的处境。有时接近事实,有时又离事实越来越远。这样的“暧昧”,绝不仅仅发生在《童话·世界》的女生身上。但想来,导演不太乐于看到,观众在观影后就匆忙地审判这几个未成年少女“太过天真”或“太过不清醒”。
看完电影,我恰巧看到台湾女演员杨谨华在最近播出的一档综艺节目中讲述自己的一段经历:“已经签约定下来了,然后又说不要我。直接退我就算了,他们就是很不相信我。要试我的戏,我跟男主角有吻戏,但是又不给我男主角,(而是和)工作人员。而且重点是我这三场戏都演完了,工作人员也亲了,最后他们跟我说要去学什么,看什么电影。
“然后我就在电影院看到我的经纪人接了一通电话跑出去。我后来走出去,经纪人就拍着我的肩膀说,他们还是不要我。我就哇,狂哭。我从电影院的门口一直走,我说我花了这么大的努力,去做他们要求的事情,为什么还是这样子?我就是不想要被看不起的感觉。”
杨谨华说,当时自己的眼泪无止尽地掉,不断质疑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不够好,感觉自己像被全世界遗弃。
事隔多年,不知道她是否看清,自己当时受到的是权势的压迫,而不是社会既定规则下的所谓“敬业”和“不够好”。何况,这所谓 “既定”是如此糟糕。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LJS,编辑:谭山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