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鲁豫是一个常年在路上的人。没有带书的旅途,于她而言,会是一场煎熬。
在这一年的旅途里,陪伴她的是《俗女日常》《南方来信:1980年代上海少女香港沉浮记》《五四婚姻》《偶然的创造》《五爱街往事》《暗影之城:一个女人的喀布尔漫步》等。隔着音频,翻书声窸窸窣窣,她仔细地说着这些书的细节带给她的抚慰与思考。
几十年来,她也关注着各类优质书籍的引进,同时对语言保持着高度的敏锐,“人在一种失语的状态里,会变得非常被动而脆弱”。她同意读者在阅读翻译小说时非常谨慎,但并不同意译者总有悲剧感,因为作者与读者之间不仅隔着译者,还有个体经验。
她惊异于曾在一所小学见到《给女孩读的童话》《给男孩读的童话》这样的书籍。她对关于女性与阅读的粗暴结论存疑,于她而言,“如果阅读也要分性别的话,这件事就特别可笑”。
我们在2023年度刀锋图书奖颁奖礼开始之前,与陈鲁豫聊了聊她的阅读经验。以下为访谈实录。
一、普通人的生活,被重新看见与书写
《新周刊》:2023年,你是否观察到一些新的出版趋势?
陈鲁豫 :从我自己的阅读经验来说,像易小荷的《盐镇》和三胖子的《五爱街往事》,都让我感觉到一种与过往趋势的差异,好像关注普通人的非虚构类作品变多了。一方面是专业作者的视角转向了普通人,一方面是普通人自己书写自己的生活,比如《我在北京送快递》。
当然,纪实文学一直都有描写普通人的传统,比如梁鸿老师写的梁庄人、黄灯老师写的二本学生,都属于这个范畴。但我以前没有特别明确的感受,也许是因为我忽略了这一部分,直到去年才觉得它们像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般出现在我面前。

(图/黄灯《我的二本学生》)
《新周刊》:这几年是否有一些突发的事件,促使你去读了某本书?
陈鲁豫 :有。一般来说,如果出现什么重要事件而我对它不了解的话,我会特别好奇。
比如俄乌冲突发生的时候,很多媒体开始推荐《欧洲之门:乌克兰2000年史》,我立刻就买了。我发现原来乌克兰是长期被夹在一个历史的、政治的缝隙当中生存的。我对乌克兰的了解太少了,所以这次阅读经历让我印象很深刻。
《新周刊》:你曾经在布雷拉国家图书馆解释过“晴耕雨读”这个词,说“当我们不被需要、没有工作的时候,还可以读书”。可不可以讲讲你在低落时期曾读过的书籍?
陈鲁豫 :前年去世的美国主持人芭芭拉·沃尔特斯写过一本书叫《Audition》,非常厚,讲她从业60多年的经历,从大学毕业到进入美国的电视行业做记者,一步步地呈现超过半个世纪的电视生涯。她等于是我的前辈了,所以读她的书会感受到很多鼓舞。
但书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如果说人生走入黑暗时刻能够靠一本书拯救的话,那太扯了。

(图/受访者提供)
二、“一部作品从来都不只是一部作品”
《新周刊》:《纽约客》的编辑E. B. 怀特说“这世界喜幽默,待它却轻薄”。你觉得脱口秀算是一种好的文学文本吗?
陈鲁豫 :我觉得脱口秀是存在于舞台上的。它当然可以说是一个好的文本,但未必是好的文学。我曾经读过伍迪·艾伦写的《毫无意义》和《门萨的娼妓》。可能因为太了解他了,所以我脑海当中会出现他的样子,特别喋喋不休、神神叨叨的,然后我一边读一边自己补充很多笑料进去。可是,如果把它纯粹当成文字来看的话,这些文本也许会变得很啰唆。
脱口秀的搞笑在于停顿。演员需要呈现出一种语言的重复或者缺失,而这个特点放在文字当中不太好。单纯地把脱口秀看成普通文本,会失去很多魅力。我曾经也在台上做过这样的尝试,然后明显地发现,我无法仅仅靠读一个脱口秀的文本就想象出它的幽默。只有当一个人将它以表演的方式在我面前呈现出来时,我才恍然,噢,原来它这么好笑。
《新周刊》:你对方言小说的阅读感受是怎么样的?
陈鲁豫 :我会读老舍先生的京味小说。但如果抛开这种北方语系去考虑的话,以前在香港的时候,我会看到很多报纸是以粤语的路子来写的,不过我还没有读过完全用粤语写的小说或者散文。还有一种是吴语写作,我读《繁花》的时候感觉很亲切。
我是一个很容易被特别的文字或者表达方式吸引的人。小时候喜欢三毛就是因为她描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而且她的语法结构、文字表达跟我在中学时期熟悉的语言风格很不同。三毛是在中国台湾长大的,她受到一种比较传统的中国文学表达方式的影响,再加上中国台湾本土的特点,这跟我在那个年代所学习的作文表达很不同。
后来我又读到了张爱玲。都是中文表达,但她的中文就是让人一读就知道是张爱玲,而且很明显能看到她受到曹雪芹的影响。这种不同之处非常吸引我。
所以我读到《繁花》的时候会觉得耳目一新。在此之前,我很少读到这种大量使用方言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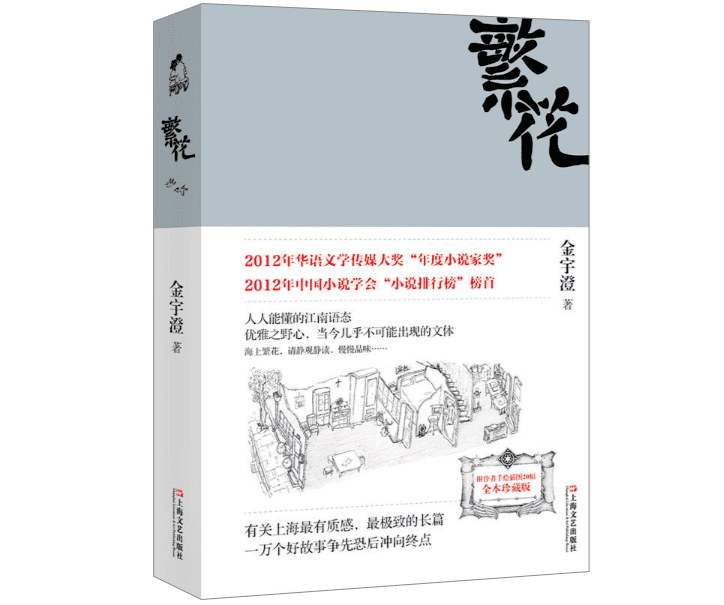
(图/金宇澄《繁花》)
《新周刊》:在读翻译小说的时候,读者会有一种天生的谨慎。而译者也偶尔会生出悲剧感,因为不确定翻译是否能完全传递原文意旨。你如何看待这种翻译的处境?
陈鲁豫 :我能理解读者的谨慎,因为人在一种失语的状态里面,会变得被动而脆弱。
我本身是学语言的,完全能够明白这种心情。当我不了解一门语言时,我需要仰仗别人作为我的媒介和桥梁,并且无从判断我获得的信息是否真实。所以我从小就很抗拒阅读翻译作品,这也让我错过了很多中文、英文以外的作品,特别可惜。
长大以后,我发现其实应该信任翻译,这种信任就转化到我的翻译工作中。我没有那种悲剧的感觉,反而会有一种特别强的使命感,就是我要尽可能地把它传递出去。而至于我能够传递到90%还是80%,这个就不再去想了。
但是,即使没有语言的壁垒,仅仅从一个创作者的意图和读者的吸收来看,中间也会有错位,毕竟个体对同一个事物的理解是有巨大差异的。所以作者在创作时的意图怎么样,读者和观众根本无法想象,而且也不会去想象,只能根据自己的认知、审美、经历去解读。
所以,一部作品从来都不只是一部作品。一部作品最后会幻化成无数的作品,它取决于每一个接收的个体。差异是千差万别的,不仅仅只有语言会导致它错失什么、遗漏什么。
但我作为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会尽我所能。当然,到底是愿意更多地保留文字的顺滑,还是愿意让文字原汁原味,这就取决于译者的个人审美和他在文学上的决定了。

(图/受访者提供)
三、“我喜欢女性的以小见大”
《新周刊》:可不可以谈谈你比较喜欢的女性作家?
陈鲁豫 :如果在中文世界的话,最早的肯定是三毛。然后我比较惋惜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读张爱玲,因为当时她在国内突然翻红。还有池莉,一直到现在我都还会阅读她们的作品。
另外,阿加莎·克里斯蒂、琼·狄迪恩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也非常重要。
《新周刊》:张爱玲很晚才被文坛认可,也许因为她不正面地书写战争。伍尔夫的意识流也曾受到热衷于谈论史诗的男性批评家挤压。这种环境会对女作家造成什么样的创作阻碍?
陈鲁豫 :女作家历来受到的阻碍太多了,她们可能不会真的被某一种“阻碍”给阻碍到。
比如我们谈到18世纪、19世纪的时候,的确有不争的事实:女性作家很少能够去书写大革命、大航海,而是更多地描写乡村生活。像英国的勃朗特姐妹和简·奥斯汀,她们的生活领地就这么大,没法写很恢宏的阶级斗争、革命浪潮。但我认为细微的生活仍然能反映时代。
在我看来,“微小”也是一种对历史的书写。我不认为它就是小了,我喜欢女性的以小见大。
同样,我觉得张爱玲也是如此。她的作品其实有两次“流行”,一个是当年她在上海的时候,一个是我刚刚讲的20世纪90年代之后,她重新被国内的文坛了解。我们以前学习语文,老师不会讲到她,可能就只是提一嘴,张爱玲根本是被忽略的。所以她在被我们认识之前,中间有一段割裂的、中断的时期。
张爱玲在当时是一个非常畅销的作家,但主流学界没有给她足够的认可。这就不单单是两性差异造成的不认可,还存在着政治派别的问题。

(图/张爱玲《流言》)
《新周刊》:这几年,女性书籍的出版数量在上升。是否有表达女性意识比较好的男性作家?
陈鲁豫 :我始终认为,感同身受很重要。你只有跟我有过相同的经历,我们才能够在同一个空间里谈话。
即便是女性也未必能与另外一个女性感同身受。因为我没有她的经历,只能从道义的层面去说“我支持你”。女性之间也会因为各自背景的差异而没有办法完全互相理解。但是女性有一种先天的共情,所以我还是认为女性作者更容易抵达女性的内心。
至于男性作者,我可以说他是一个支持女性、爱护女性、对女性充满善意的人,但他很难写出一个百分之百鲜活的女性心理。再往上要求的话,不太切合实际,因为毕竟他不是女性。
比如曹雪芹写《红楼梦》,他好在没有试图把自己变成一个女性,说“你看,我虽然是男性,但我跟你一样,我能够对你感同身受”。他只是非常客观而且充满善意地记录,不站在任何审美的、道德的制高点上。他可贵的地方在于给了一些无声的女性以声音,他把女性群像画了出来,但是没有完全扭转到女性的角度,声称“我是你们当中的一员”。曹雪芹没有试图做这个改变。
所以我不认为一个男性作家必须要成为一个女性题材写作者,你只要愿意承认自己的困惑、陌生、不了解,甚至是偏见,就可以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许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