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按下回车键确认签署生前预嘱后,48岁的张海蓁坐在电脑前,脑子里回闪过5年前最后一次听父亲回述人生经历的那个午后。
2007年,7月的北京夏日可畏。张海蓁的父亲在一个月前被确诊为晚期肺癌。经过一个月的接受病情,面对病情,以及确认合适的治疗方案,她和家人们最终愿意接受父亲提出的愿望——选择合适的相对舒适的治疗方案,不会强行延续父亲的生命。
父亲跟她提起,自己宁愿战死在沙场,也不愿如行尸走肉般苟活。他曾是新中国的海军战士,他会谈起马克思女儿燕妮夫妇,赞赏他们不愿疼痛直面死亡的勇敢。她也记得母亲对父亲作出最后决定的回应,“你的生命不仅仅是自己的,你的生命中还有我,有我们的孩子,有我们的家人。”
除了癌症晚期病人的亲属外,面对末期生命流逝的无力感也在医生间传递。在公立医院癌症科任职期间,查房遇病房里发生的生死别离时,前公立三甲医院癌症科主任李玉新常常会低头匆匆走过回避此情景。
“不敢直面患者亲属对延长患者生命的期许”,李玉新医生向界面新闻坦言,癌症是生命缓慢衰竭的过程,对此医生常常是无能为力。他通常会劝家属不要对患者进行过度的抢救,避免患者在生命末期遭受不必要的痛苦。
全球仍有太多临终者在痛苦中死去。当前的社会以避免死亡为先,而非减少不必要的痛苦,期间或因为包含了太多亲朋好友违背个人意愿“过度的善意期许”。
与之相反,生前预嘱是人们在意识清楚时做出的预先指示,表明自己在失去决策、表达能力时想要接受怎样的医疗照护。这种行为由患者自己提前决定医疗救治决策,既不加速死亡,也不缓解死亡。
2022年6月23日,广东省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订稿(以下简称《条例》),其中第七十八条提及的“生前预嘱”制度表示,人们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签署的,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的指示文件。
该条例已于2023年1月1日起正式在深圳施行。这是我国首个将生前预嘱以立法形式纳入确立的条例。这意味着,至少在深圳,对那些考虑过临终时刻的人来说,有权在符合医疗标准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最终的医疗手段。医护人员对临终者的救治在临床工作中也有了更规范的依据和更广泛的选择。
如今,该条例已在深圳实施满一周年。据深圳市生前预嘱协会介绍,立法实施后,老年人和肿瘤患者的咨询数量和订立数量比例较前明显增多。不过,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一概念仍是新颖。此外,深圳推行的生前预嘱还仅以法律框架形式存在,更具体的实施细节还需在未来的实践中探索与确立。
与传统的冲突
在16年前,在中国,在生命最后时刻的人还没有做出这个选择的概念与机会。
生前预嘱这一概念属于舶来品。生前预嘱在国内的推广最早追溯于2006年,这是业内人士普遍的共识。当年,罗点点等一众人创立了“选择与尊严”公益网站,首次发布了中国版的生前预嘱文本《我的五个愿望》。
2013年,在公益网站的基础上,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于注册成立。
“选择与尊严”公益网站上的生前预嘱——《我的五个愿望》,是一份医疗护理指示文件,由人们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签署。其主要目的是,在生命最后末期,避免使用不必要的创伤性抢救措施,尽量帮助将死之人自然而有尊严地离世。
这是一份只需要做选做题的文本,一共有39个选项,最早由美国律师协会的法律与老龄化委员会和临终照顾专家共同协商编写。被引入中国后,该文本的部分内容根据中国的法律环境和使用者特点等作出了适当的修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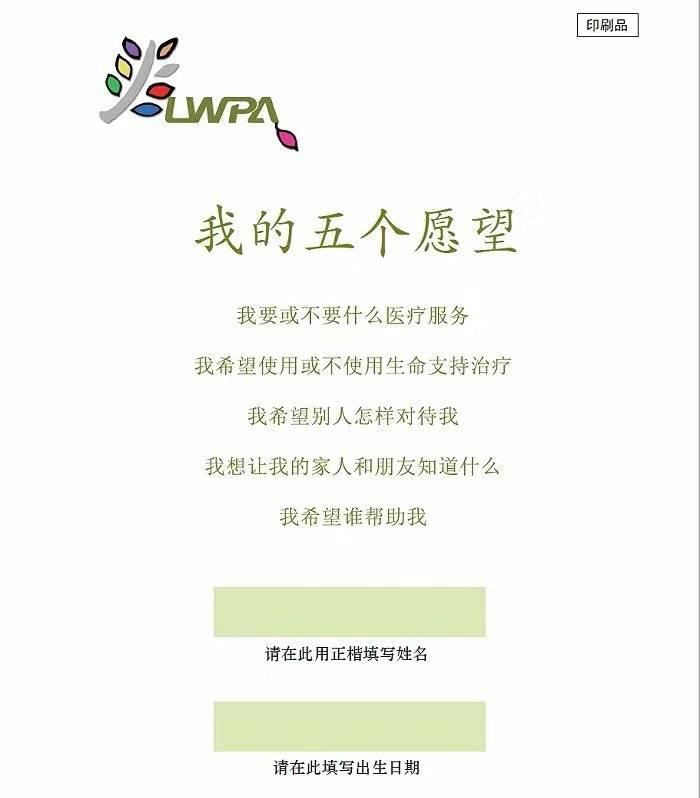
“选择与尊严”公益网站上的生前预嘱——《我的五个愿望》
现任北京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会长王瑛告诉界面新闻,在此之前,国内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有“生前预嘱”这个概念。在现实中,中国人都不太愿意谈及“死”,但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发展转变与上一代人正渐渐衰老,这才促使在中国社会中产生思考——什么才是“尊严死”。
而人们真正面对死亡时,面临的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场景与困境。这不仅让将死之人自己很痛苦,也很大程度上会累及其家庭,甚至还隐含了整个社会医疗资源的配置问题。
国际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于2022年2月13日刊发的《柳叶刀死亡价值重大报告》(The Lancet Commission on the value of death)中表示,当前过于强调通过积极治疗延长生命,全球在姑息治疗可及性方面存在巨大的不平等,并且生命终末期(end-of-life)的医疗费用高昂,这导致数百万人在生命末期遭受不必要的痛苦。
但这个问题在现实的社会中仍很难有一个明确且统一的答案。罗点点曾在多个公开场合与其自述《我的死亡谁做主》中讲述她曾经面对亲人死亡时的道德负罪感。
罗点点回忆,她的婆婆因糖尿病住院,在病床翻身时被一口痰堵住,心跳呼吸骤停。医生第一时间给罗点点的婆婆用上了呼吸机。虽然婆婆的心脏还在跳动,但已没有了自主呼吸,也完全丧失了神志。
她记得婆婆曾告诉她,若病重,不希望被切开喉咙,被插上管子。最后,她和家人作出了停用呼吸机的决定。作出决定后,她陷入崩溃。她不断在心里问自己:我们凭什么决定婆婆的生死?我们作出的选择是正确的吗?
在后续整理老人遗物时,罗点点才最终释然。她看见了婆婆日记本里夹着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希望在生命尽头时不进行过度抢救的字样。
除了内心的道德负罪感外,这个问题甚至还会产生不少非议。在尊重父亲做出的这个决定后,张海蓁和她的母亲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在中国的家庭关系中,由于对事物的看法不一致,每个家庭成员都会有各自的意见表达。”
“这些行为在当时让旁人难以理解。但实际上,父亲是完全相信母亲的。”张海蓁说,母亲是药剂师,专业的理性使母亲清楚父亲癌症病情的实际进展——当时的医疗条件还没办法救治她的丈夫。另一方面,作为妻子的感性,母亲自己也曾怀疑,她也很希望丈夫能奇迹般地战胜病魔一直陪伴自己。
在当时身边不少人给她的母亲提建议:你家的经济情况还不错,怎么不用最新的癌症靶向药治疗试试?但母亲对此“无动于衷”。“每个阶段的治疗方案都是母亲与父亲的主治医生讨论确定的,从最合适有效的基础用药开始递进。”张海蓁还和母亲一起在父亲的病房摆上花瓶插上鲜花,时不时再放上父亲喜爱的音乐。
在父亲去世后,张海蓁的内心很长一段时间处于混沌之中。她空闲间时不时用家里的电脑搜索关于“死亡”、“疾病”等信息,直到她看到了“选择与尊严”公益网站上关于生前预嘱的内容。
那一刻她才真正坦然了。在此之前,她并不知道,她父亲“超社会时代性”的对生命原始的渴望与她和母亲尊重父亲并为他所做的那些行为,实际上是在践行生前预嘱《我的五个愿望》里的内容。
这种无法逃避的无力感与“道德负罪感”也在医生间传递。在公立医院癌症科任职期间,查房遇病房里发生的生死别离时,李玉新常常低头匆匆走过回避此情景。他坦言,不敢直面患者亲属对延长患者生命的期许,癌症是缓慢衰败的过程,对此医生真的无能为力。
为此,他甚至“逃避”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访学一年,“压力真的很大”。访学回国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李玉新接触到生前预嘱与安宁疗护。他明白了,医生救治到最后一定遇到很无能为力的场景,医学的无奈反倒是对生命的尊重。
李玉新曾接诊过一位癌症晚期男性患者。那是在一年春节前夕的某个夜晚,这位男患者最终没能撑过这一天。那天他查完其他病房刚转身出门,看见这位男患者的父亲刚把他孩子的尸体处理完毕。他与这位父亲在病房外走廊迎面相遇,发现这位父亲竟白了头。那一刻某种冲动使他迎上去一把抱住这位父亲,轻轻拍了拍他的背。他能感觉到对方在颤抖,在哭泣,直到现在也仍记得,一个父亲在他怀中显得如此瘦小。
“中国人非常不善于表达感情,特别是对于医生来说更难以启齿。”他在访学期间学到很重要的一课就是拥抱,要学会感受病人及其家属的痛苦,这能缓解他们的焦虑感,也能缓解医生的无力感。他还学会在诊室里准备餐巾纸。“到生命末期,医生再已无法给患者及其家属提供更多的治疗,但听他们发牢骚,给予他们宣泄情绪的空间,这时的倾听比药物都更为有效。”
不是安乐死,更不是放弃生命
在传统观念与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生与死总难免两相憾。在明知任何医疗措施都已经不可能逆转病情,却仍对晚期患者进行“不到最后决不放弃”的救治成为普遍现象。因此,践行生前预嘱也被部分人误解成是对晚期患者实行安乐死。
李瑛向界面新闻记者表示,签署生前预嘱不等于放弃治疗。只有在患者经历了所有现在可及的医疗手段以后,都已经明确患者的疾病是不可逆转的,必定会朝着死亡的方向发展的情况,且至少要有两类职业医生下结论判断,才可以启动生前预嘱。
而如果是急性医疗情况,如一人突发心梗,或在重大的自然灾害导致其生命垂危,均不属于生命末期,不会启动生前预嘱。此外,生前预嘱是可以根据病人意愿随时改变,以尊重患者的选择为前提。
2022年7月5日,在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举行法规解读会上,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林正茂曾回应,关于患者是否处于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期,是由医疗机构作出医学判断,并非由患者个人或家属判定。
王瑛认为,一个人面临死亡时最大的困难是恐惧,无论是个人还是家庭,越早直面死亡才能更理性更从容。生前预嘱让死亡既不提前,也不延后,而是自然来临。“在这个过程中,最大限度尊重将死之人的意愿,不把挽救生命作为首选,而是将无痛、无惧、无憾地离世作为目标。”
此外,也会有人把生前预嘱等同于遗嘱。参与了深圳生前预嘱入法的盈科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刘艳华则解释,虽然生前预嘱与遗嘱名字相近,但这两者的概念相差甚远。她介绍,遗嘱解决的是一个人离世后的财产分配问题与精神遗愿寄托。而生前预嘱是在生前进行的,患不可逆转疾病的患者选择可接受的末期治疗措施,让其在生命末期也能保持有尊严的生命体验。
目前,在现实中是患不可逆转疾病的患者的近亲属——如子女,在代替患者本人选择进行何种医疗措施。实际上,这些医疗措施不一定是符合患者本意的。通过生前预嘱,在生命末期时,患不可逆转疾病的患者可以有权利告诉家人或医生,自己想要接受怎么样的治疗方式。往大的来说,在人权层面上,生前预嘱是对个人自主意识的保障。
不过,在临床上,有生前预嘱也不应该意味着完全由患者决定治疗方案。“比如什么是生命维持干预?临床中哪种程度的抢救需被限制?”刘艳华说,签署生前预嘱时,应该要有专业人员提供指导,以确保患者家属明白生前预嘱意味着什么。
“明确性的条文在深圳立法落地对推行生前遗嘱是非常重要的。”刘艳华表示,相关的法律界人士在针对生前预嘱的法律条文的措辞就经过了详尽的讨论。”例如生前预嘱的意愿的真实性怎么确定?生前预嘱如何进行公证?签订生前预嘱的公证人与见证人又如何选择?这些也都是被提起并进行了严肃的讨论。”
深圳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订稿对生前预嘱的形式和方式都作出了明确要求:在内容上必须要有真实的意思表示,在形式上要求有公证或者经两名以上见证人见证,并见证人不能是参与治疗的医疗卫生人员;此外,要求以书面或者录音录像的方式,有患者签名以及注明时间等,来确保患者意愿的真实性。
据《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订稿第七十八条规定:收到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提供具备下列条件的患者生前预嘱的,医疗机构在患者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者临终时实施医疗措施,应当尊重患者生前预嘱的意思表示。
上述条例明确,经公证或者有两名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且见证人不得为参与救治患者的医疗卫生人员;采用书面或者录音录像的方式,除经公证的外,采用书面方式的,应当由立预嘱人和见证人签名并注明时间;采用录音录像方式的,应当记录立预嘱人和见证人的姓名或者肖像以及时间。
刘艳华表示,签署生前预嘱最好是在意识清楚、环境轻松的状态下,与家人、朋友、医生甚至律师等相关人士一起讨论,充分了解,然后再做出决定。
此外,医生通过什么方式获悉其接诊的患者此前已签署生前预嘱?生前预嘱的内容在患者的病例中又如何显示?“这些也都是需要在实践中考虑的。”王瑛表示,实际上,很多患者在到了需要入院这个阶段,已经没有能力再正常表达与沟通。否则,在生命终末期,亲属肯定都是要求医院尽力抢救的。这些都是需要在实践中探索。
李玉新医生表示,他通常会劝家属不要要求对患者进行过度的抢救生命治疗,避免患者在生命末期遭受不必要的痛苦。“在此过程中进行的过度用药、检查,甚至过度抢救等,不仅加重了自身经济负担,也可能违背患者意愿给其带去痛苦,对医疗资源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浪费。”
但在现实环境下,“很多家属都会在相关签字单中表示拒绝做气管插管等有创操作,但真正到了患者临终时,医生告知患者家属是否决定放弃临终抢救,患者家属的内心又会开始摇摆。尤其对于子女而言,若父母已处于弥留之际不尽力抢救,怕留下遗憾‘自己不够孝顺’。但若进行创伤性抢救父母仍去世,又责备自己是否未让老人“安详离去”。”李玉新这样描述。
不难想象,面对亲人的口头预嘱,普通人通常难以抉择。即便现在已被写进《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生前预嘱仍不能被保证执行,决定权还是掌握在家属手中。
李英表示,目前生前预嘱还仅以法律框架形式存在,还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在深圳,生前预嘱也是先行先试。法律文件里写的是尊重,而非执行。尊重这个词偏软性,也意味着可以商量。若出现签署人意见和家属意见不相同时,医护人员更多也还是会尊重患者家属的意见,以避免医疗纠纷风险。
“医疗机构要对生前预嘱内容进行最终的二次确认”,刘艳华表示,生前预嘱发挥效力的时间是在临终时或者是生命末期,这时候签署者不见得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若签署者处于清醒状态,可以就是否践行生前预嘱的内容做最后的确认。医疗机构可以邀请签署者及其法定监护人签字也同时确认。
若签署者已处于意识不清醒状态,医疗机构也应当让其法定监护人确认是否认可此文件。当法定监护人和近亲都认可,此生前预嘱的效力便无人可调整。若某一亲属不认可,这就需由司法机构来判断该生前预嘱是否有法律效力。
刘艳华建议,理想状态是生前预嘱与城市的社保挂钩——患者去医院挂号看病与医保关联;医生查看医保信息获知就诊患者曾签署生前预嘱。“这是我的个人建议,这样生前预嘱签署者在深圳任何一家医院就诊时,其的生前预嘱都可被医院及时获知,但这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探索。”
向死而生
自生前预嘱立法实施以来,深圳卫健委通过《深圳市生前预嘱服务指引(试行)》,对全市安宁疗护的服务机构进行规范性管理,鼓励提交患者的生前预嘱,或在安宁疗护机构订立生前预嘱。
不过,目前最大的问题或是,许多医院的医生并无精力从平日冗杂的工作中抽身,来承接照看签署了生前预嘱的末期病人。
王瑛表示,生前预嘱必须要有安宁疗护承接,支持将死之人面对与解决死亡这个困境。如果医院内的资源配置不支持进行安宁疗护,生前预嘱的落实也很难进行。“生前预嘱不应该是孤零零的一棵树,它要与安宁疗护、生命教育一起,构成一个森林。”
所谓安宁疗护,是指为疾病终末期或老年患者在临终前提供身体、心理、精神等方面的照料和人文关怀等服务,控制痛苦和不适症状,提高生命质量,帮助患者舒适、安详、有尊严地离世。而事先了解或立下生前预嘱,在临终时更容易选择安宁疗护服务。
目前,安宁疗护在国内的发展还处于试点阶段。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多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建立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中提到按照患者“充分知情、自愿选择”的原则开展安宁疗护服务。深圳于2019年成为国家第二批安宁疗护试点城市。

图片来源:北京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
“安宁疗护与生前预嘱一直都不是医生的份内工作。”李玉新表示,医生的临床工作已很繁重,生前预嘱属于人文关怀,虽能给患者在末期带来较好的生命体验,但没有相应的收费标准,不能单靠医生和志愿者的激情去推动生前预嘱和安宁疗护,需要建立长效机制。此外,一位医疗人士向界面新闻表示,医院体制要求医生创造经济价值,但生前预嘱与安宁疗护付出的精力与获得的经济收益不匹配。
李玉新补充,安宁疗护重在护理,在医院给病人做护理服务收费标准低,与护士的劳动付出不成正比,医生则更缺少动力将安宁疗护在医院推进下去。因此,医护在推动安宁疗护与生前预嘱的过程中更多在于内在的精神需求。
有医疗专业人士向界面新闻对此解释,部分医院对科室主任存在创收要求,既要求医生会看病,还要医生会做营销创收益,因此医院内部也存在很多竞争。“现在医院若经营不善是会亏本的。”他指出,医院的营收大头实际上是给患者做检查。“病人刚入院时做的检查项目是最多的,这段时间是经济效益最高的,但随着病人住院时间越长,做的检查项目也越少,边际利润是递减的。”
李玉新说,曾经有一个同行其在院内推行生前预嘱与安宁疗护并取得非常好的效果,但有一次在医院里看到院长迎面而来,那位医生不自觉地把头低了下去。“末期患者需要生前预嘱与安宁疗护提供的生命末期关怀,但推行安宁疗护的医生也会有一种我在医院没干正事的负罪感。”
此外,医院内也缺乏足够的资源配置来使安宁疗护落地。王瑛表示,安宁疗护是跨学科跨组织的,尤其缺乏相关人才——不管是院校的学生、继续教育中的医生,或是更专业的专家都是不足的。这些建立都是需要时间来沉淀积累。
王瑛表示,各级医院之间的资源配置也存在矛盾:一方面是大三甲医院人满为患,导致医疗资源紧缺。另一方面,级别较低的医院病房出现闲置,导致医疗资源未被充分利用。她建议,大三甲医院可以作为安宁疗护的试点样板,但真正推广要在三甲医院的医联体内,把医疗资源统一地组织起来。
因此也有人建议可以将安宁疗护移动置于患者家中。王瑛也表示,其实大多数将死之人直至临终也不愿意离开家。安宁疗护的护理服务是有机会由医院病床到家庭病床的。不过,李玉新表示,待在家里会缺乏很多专业性的护理项目,部分患者还是会因此而焦虑与恐惧。
这也是一个待解决的双向性的矛盾——医护人员不可能上门到患者家中做护理服务,患者无法得到专业性的安宁疗护服务;而患者到在医院住院进行安宁疗护,但期间患者不做检查、不用药物,导致医院经营“亏本”。
李玉新表示,或许可以学习借鉴中国台湾的部分做法,借助社会或社区的公益力量补充安宁疗护中缺乏的护理服务。他表示,从安宁疗护具体工作来看,专业医生能做的相对较少,而护理师却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安宁疗护团队中的核心。在台湾地区会有社工补充缺失的护理师职能,不过,由于大陆目前缺乏社会公益力量进入医院的基础,这个环节也仍任重道远。
2022年10月8日,深圳市福田区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张清在居家安宁疗护的探索与发展论坛中表示,护士人员对社区或居家安宁疗护的积极性不高。工作量与收入不成正比是关键。在安宁疗护试点城市中或许可以采用补贴的方式弥补医护人员的收入付出比,但最终可能还需要回到政府购买相关服务与医保支付挂钩。
深圳市人民医院副院长梁真也在论坛上说,未来安宁疗护的推广重点在社区安宁疗护与居家安宁疗护。不过,目前安宁疗护在社区与居家的推广还有很大的限制。除储备合适的安宁疗护人才外,安宁疗护上门服务法律范围如何界定,期间提供的居家安宁疗护服务收费又该如何确定均是值得思考与探索的。如什么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提供的服务不同,这都是很复杂的落地实施。
梁真表示,在社区或居家安宁疗护实践过程中药物使用方面,也存在无法避免的问题。部分安宁疗护所需要的毒麻性止痛药品是社区不具备的,且法规上不允许在居家使用的。如何在规范下允许让安宁疗护人员正确使用这类药物也是探索实践中需要考虑的。
2000年5月,中国台湾通过了《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允许患者在疾病终末期拒绝心肺复苏,是亚洲第一个使生前预嘱合法化的地区。2015年12月,中国台湾通过《病人自主权利法》,规定中国台湾民众可以预立医疗决定,是对先前立法中涉及的终末期和医疗措施进一步完善和细化。
据界面新闻统计,全球已经有30个国家和地区允许在医疗护理过程中合法使用生前预嘱以及功能相似的一系列文件。
实际上,除试点城市深圳之外,对于生前预嘱与安宁疗护,中国的大部分医生和患者面临的仍然是空白。据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提供的数据,在“选择与尊严”网站上注册的人数在5万人左右。李玉新表示,在临床中并未遇到过签署生前预嘱的患者。
向死而生,仍是每一个人生中不可逃避的现实。
本文来自:界面新闻,记者:李科文,编辑:谢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