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读《没有面目的人》,书中的观点在我的脑海中一直挥之不去。在这本书中,作者理查德·桑内特着重讨论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对人的品格的影响。他认为,现代企业的组织形式高度强调弹性,提倡工作者拥抱变化和承担风险,这让长期主义的思考和行动越来越不合时宜,带来一种此前不太被讨论的精神危机:
“在一个心浮气躁、只看眼前的社会中,我们如何判断哪些是自我内在的持续价值?在一个专注实现短期目标的经济体系中,该如何去追求长期目标?在不断分裂又不断重组的机构组织中,该如何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忠诚与承诺?”
我会一直想着这本书,可能是因为它戳中了这两年我深藏心底的忧虑。在我的同龄朋友之中,我已经是一个异类——毕业开始工作后从来没有跳过槽,每每提及此事他们总会惊叹不已。这种忧虑在于,即使我在工作中做到了不断精进自己,但我依然有强烈的不安全感,依然怀疑我是否真的在某条职业发展轨迹上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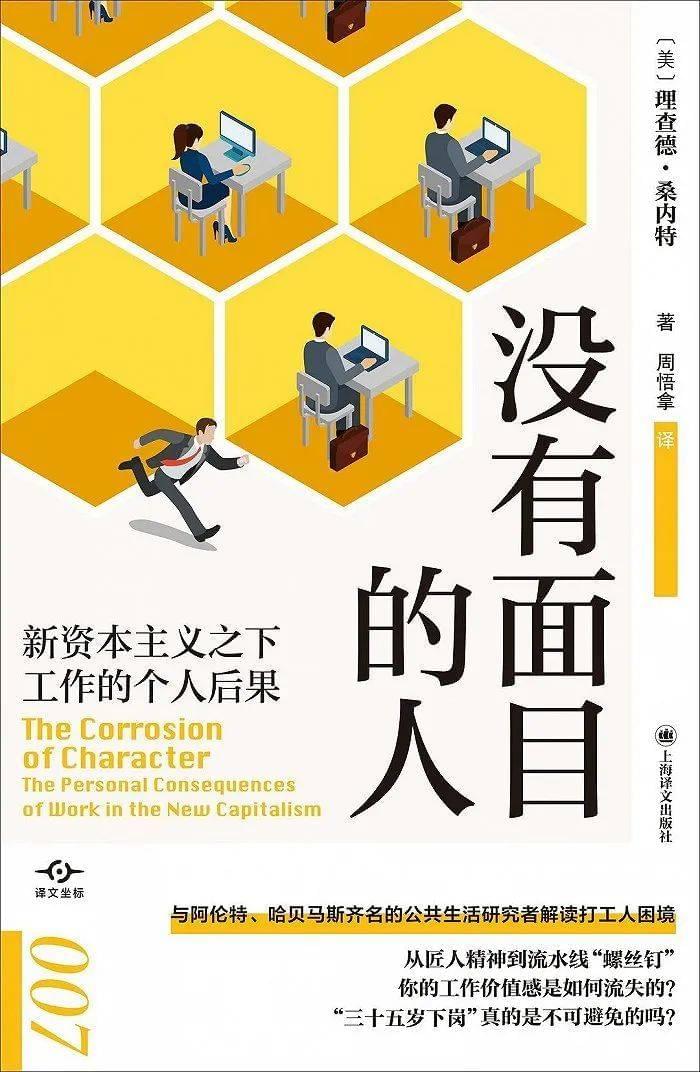
《没有面目的人:新资本主义之下工作的个人后果》 [美]理查德·桑内特 著 周悟拿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3-11
桑内特在书中说,“现代的冒险文化非常奇特,如若原地不动,便被视为失败的标志,而稳定则几乎被视作是行尸走肉的生活。”诚然,“生活即变化”是我们时代的典型人生信条,但我对桑内特的反思产生了深深的共鸣:“随时准备更换赛道”的短期主义心态似乎与我成长过程中接受的价值观并不相符,那一套价值观告诉我们,收获需要长期耕耘和耐心等待,需要表现出忠诚与责任感,需要坚持目标。
但在如今的世界,这些长久持续的美德并不必然能让人实现目标。这种经济环境与个人成长经历中相反的时间观已造成了一种内在冲突。一位接受桑内特采访的父亲就表示,他如今对教育子女充满了困惑,他认为家庭中不应推崇强调见风使舵的新经济价值,但作为家长,他又要如何为孩子做出榜样呢?
桑内特认为,当今社会的不确定感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是源自迫在眉睫的历史灾难,而是源自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日常经验。必须要承认,在当今世界的很多地方,不确定感其实是双重的,生活常态会被打破,没有什么可以真正兜底。
螺丝钉对长期主义无益,职业稳定不一定提升忠诚和敬业
林子人:桑内特说,“有能力放手过去,有信心接受破碎”是当今世界如鱼得水的那些人具备的两种品格特征。我们时代要求每个人都具有“企业家式的自我”,身段灵活地承担应对社会变化的全部责任,冒险是被鼓励的,稳定是被鄙视的。你们是如何看待冒险和稳定的?
徐鲁青:是不是先要厘清“稳定”是指的什么,是生活状态吗?卡夫卡笔下日复一日的公务员似乎是最稳定的,但稳定的螺丝钉工作也不会有益于“长期主义”,反而螺丝钉被要求的是不要考虑意义,把领导交代的事情做好就行。这时候对工作的忠诚与责任感不仅让人变成甲虫,也巩固了整套异化机制。
还有一种稳定是权益保障到位后的生活安全度。谁不想要这样的稳定呢?好像又是没得选的。我想,频繁更换“工作赛道”的人不一定特别缺乏这种稳定,不然用不上“赛道”这个词,对比于五年没有换工作的稳定零工者,也更有机会做一些长期主义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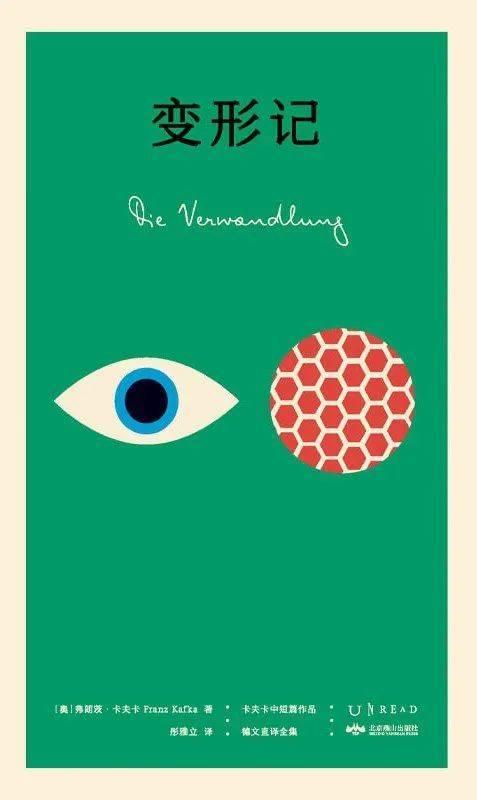
《变形记》 [奥地利] 弗朗茨·卡夫卡 著 彤雅立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20
潘文捷: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大家获得了来之不易的自由,那么当下这个时刻我们得到的自由,已经变成没有选择、非自由不可了,是不可限量也无计可施的自由。所以我们看到又有好多人想要去考公,获得体制内的一席之地,求那一份上一代人可能避之不及的安稳。
但人决意过某种生活也有自己的原因,并不完全是时代使然。冒险和稳定或许都是表象,各人追求的那个“道”才最重要。唐三藏是如来佛的弟子金蝉子,他大可人淡如菊,念佛敲钟安稳一生,可是为了追求西天佛法,却偏偏要走上最冒险的道路。
董子琪:职业的稳定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更为常见,那时,市民生活里没有下海,没有出国,没有“体制外”,可是那时的人很“敬业爱岗”吗?我觉得讨论这点非常有趣,因为总会想起侯宝林讽刺国营水果店店员的段子,还有电影《瞧这一家子》(1979)里刘晓庆饰演的角色——她是国营商场专门销售服装的店员,私下嘻嘻哈哈、非常可爱,一上班就板着脸,对顾客爱答不理。可见,职业的稳定并不见得会提升个人的忠诚和敬业。
然而,街头遛子确实是负面的代表。梁天在《我爱我家》(1992)里扮演的二叔贾志新,就是一个三天两头更换职业、基本上处于危险边缘的人物。像这样的角色,梁天还扮演过一个,就是赵丽蓉和李保田电影《过年》(1991)里的小儿子,没有正经的工作,不仅谈不到对象,也不可能在家获得话语权。
可能这是不同层面的事情。我觉得国内职场对于个人稳定的要求并不低,在社交网络上经常可以看到中国人不许GAP(指gap year,间隔年)、空档期大过一个月就被HR否掉的抱怨帖子。这也许不仅和现代生产方式相关,更来自于人们心中的观念。
与此同时,职场术语也入侵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Papi酱有一期短视频,就是将职场与谈恋爱混淆,情侣分手叫解除合约,想换人叫跳槽,跳槽最早也是妓女和恩客之间的行话,又转喻回来了,摊牌叫brief一下。其实,在人们心中,工作是比恋爱更加正经,用语也更为正式。
最近看一本小说、罗伯特·瓦尔泽的《唐纳兄妹》,讲的是一位年轻人如何频繁更换他的工作的故事,他不停地漫游,在不同的初级入门岗位之间跳来跳去——像是一个永远处于“试用期”的人。他在银行担任职员的时候,认为“春天里的一栋银行大楼无比愚蠢”;在书店当店员的时候,因为书桌不够舒适而必须离开。
他看到身边的同事,心里想的一段话无异于对稳定工作的诅咒:“五十年来,他进进出出同一道门,在商业信函中成千上万次使用同样的用语,经常更换得体的西装。那么现在呢?你能说,他真正生活过吗?难道不是成千上万的人都这么生活吗?”
笃定何为生命激情后,职业更多是关于舒适度和回报率的考量
潘文捷:文科是最需要坚持目标、长期耕耘、耐心等待的吧,这些品质外行不一定能看出门道,但最近旁的人都看得出来。如果说我们自己的工作的话,表面上看,媒体工作是什么热点来了追什么,可以算是某种“随时准备更换赛道”的短期主义心态?
但在具体工作中,反而是子人给了我一种确定感。因为你解决问题都是正面应敌,问题来了直接提刀(笔)迎上去,背后有长期的阅读和思考习惯做垫底。绝对不会利用小聪明,各种找机智的切入角度,来避免自讨苦吃。
林子人:得到文捷如此高的评价,又感动又开心!我觉得成为文化记者的我们属于职场中比较幸运的那些文科生,我们能够学以致用——我们习得的理论与技能(批判性思考、快速学习与写作)与我们的工作内容是高度重合的。
我也同意文捷的观点,记者的工作既要求长期主义又要求短期主义:长期主义是指智识能力与思想储备是无法催熟的,你就是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去积累经验;短期主义是指记者往往需要追随热点事件,快速进入,再快速抽身,投入下一个报道。
我记得之前采访《东北游记》《再会,老北京》的作者梅英东,他对自己在北京的记者生涯做出过一个比喻——“我感觉自己像是一只吸血鬼,突然出现在某人的生活里,从他们那里攫取一点东西(至少是一点可被引用的话语片段),然后飞走,从此不复相见。”——让我深有同感。

《东北游记》 [美] 迈克尔·麦尔 著 何雨珈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年
但这个层面的短期主义尚属个人可控的范围,如今其实是那些驱使我们不得不采取短期主义心态的社会结构性力量让我们焦虑,比如短视频对书籍阅读时间的侵蚀、35岁门槛、难以预测的裁员计划……
徐鲁青:我的感受是,大部分人的职业身份都是流动的,要找一份投入终身的职业,不管在哪里都是很奢侈的事。特别是现在经济不景气,有意义的工作也变得越来越少。之前媒体人熊阿姨在微博上提到了文化行业的现状:走的人越来越多,一走headcount就锁死,全部不再招新人,于是整个盘子越来越小。这些我们应该都能感受到,如果有一天界面文化解散了,国内还剩什么机构能让我们跳槽呢?我认识的一个纪录片机构今年散了,所有人都开始自己接活,没有人找下家,因为不存在“下家”了。
但另一方面,我觉得职业身份从生命价值的层面来说并不是很重要,大多数时候,人能找到什么工作很看运气,也是很难掌控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寻找到和投入到属于自己的生命激情里,有一些事情是我们愿意做一辈子的,没有钱我也做,没有人知道我也愿意做,换一百个职业赛道我都不会变。因为很简单,做的过程本身就是所谓的“回报”了,就像卡夫卡当公务员螺丝钉时的写作,就像波拉尼奥换无数零工赚饭钱时的写作。
大多数人不会幸运到职业身份和生命激情的重合度很高,但没有关系,当我们笃定了这件事,职业更多是一种关于舒适度和回报率的考量。这也可能是我们建立“长久持续的美德”的一种路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 (ID:BooksAndFun),主持人:林子人,编辑:黄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