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中国人来说,35岁变成了一个尴尬的年龄节点。
近年来,一些互联网大厂辞退35岁以上员工的新闻频繁登上热搜。今年7月,一则“多家北京青旅拒绝接待35岁以上中年人”的新闻,再次将35岁的人群推向了舆论中心。35岁的中年危机,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到了35岁的人,开始面对;没到35岁的人,则提前担忧。
供房、养娃、养老、亲密关系倦怠等问题陆续蔓延到每个现代人身上,甚至连尚未30岁的群体也被迫提前自己的人生议程。拂拭掉日常表面上的担忧,被掩盖的其实是更深层的心理问题。
崔庆龙是一名心理咨询师。他从2021年5月开始,在社交平台上持续地分享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上的想法。慢慢地,越来越多人想要在他分享的内容中获得答案,崔庆龙逐渐成了微博上最热门的心理学博主之一。
35+岁的中年危机,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心理?东亚人的中年危机究竟从何而来?在这个“大家都有病”、普遍性倦怠的时代,我们又该如何摆脱无力感?带着这些问题,新周刊和崔庆龙聊了聊。
忍耐一切,是东亚人中年危机的开始
新周刊:对于中国社会来说,35岁似乎是一道分水岭:跨过了35岁的坎,你就应当是世俗意义上成功的、得体的。而事实上,35岁的人们常常过得如履薄冰:担心被裁,还要承担家庭压力。从表面上看,35岁的中年危机似乎是由现实因素撬动的,但从心理学更深层次来解读的话,中年危机究竟是由什么导致的呢?
崔庆龙:一定是先有了像企业裁员、裁员后难就业、家庭经济陷入困境、身体状况变差等这类具体的事件作为前提,中年危机才开始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慢慢地,大家好像越来越认同“人在这个年纪就会遭遇各种危机”的观念,这就是社会意识逐渐建构起来的过程。
所以,一方面是现实的、客观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大家越来越认同“35岁的人会更动荡”的观念。它会让人们对这个年龄有特别的感受,好像35岁就是一条分界线,它“天然”地将人分化成了两个群体。

(图/《海边的曼彻斯特》)
其实人类意识最微妙的就是这一点,社会上一旦形成某种共识,它就会变成一种真实存在的力量。人们遭遇的现实,逐渐就会变成更多人对于现实的预期,预期的力量足够大以后,就会变成一种客观的真实。这个现象在经济学中也有体现。
新周刊:在以儒家文化为根源的东亚社会,家庭和集体的规训构建了东亚的文化范式。在长期受到压抑的情况下,人们变得拧巴、内卷。结合东亚社会的家庭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东亚社会的人们更可能遭遇怎样的中年危机?
崔庆龙:中年危机可能存在于所有经济下行的国家或者社会环境里,但是它会因为文化而有所差异。
东亚的特点是什么?我认为是个人的意义要后置于外部的期待。无论那个期待是源自父母、家庭,还是公司,或者外人的目光,你的自我身份认同都建立在他人认同的基础之上。一旦外部的认同获取失败了,一个人就会失去精神上的立足之地。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一旦脱离这套游戏规则,就立刻陷入了躺平状态,因为行动的意义被抽离了。
东亚的中年危机经常体现为:你已经感觉到不适、疲惫、劳累、痛苦,想要为自己考虑,但此时,很多人内心马上浮现出一种“我要为了家庭、孩子、老人、婚姻继续忍耐”的想法。东亚人很早就从骨子里遵循的一套东西,会反过来去压制和对冲想要照顾自己、想要为自己做些什么的冲动。
这种影响会让你以一种更加隐忍、更加沉默的方式去把这一切承受下来,让一个人变得越来越麻木,形成一种很没生机、很枯燥的中年人的生存状态。
在20世纪的西方,人们展开了一系列诸如嬉皮士运动或者反主流运动的社会运动。这些运动以精神解放为目标,他们在摆脱了一些旧的规训的同时,又走向了以放纵为主的享乐主义。当然,那也是一种精神危机——过于放纵,缺失边界和约束,以至于导向了意义上的虚无和痛苦。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社会学家评价西方的精神危机是失去了必要约束的痛苦,而东亚的精神危机是过度约束的痛苦。
对比来看,我觉得东亚人特有的中年危机属于压抑爆发型的,像一根弦越绷越紧、最后直接崩断了的精神危机。在爆发之前,TA都处于一个不能分享、不能表达、不能宣泄、不能理直气壮地说“我不这样干了”的收缩的状态,直到有一天这根弦终于断了。
人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直面痛苦
新周刊:潜意识中,人们或多或少都会有点希望自己能够是这个社会的大多数,这是一种害怕孤独和被排斥的感觉吗?
崔庆龙:你可以这样理解,人生来就是希望得到归属和认同的物种。
我觉得大部分人们都希望成为“大多数里的极少数”。大多数人都要结婚,都要买房,都要有个好工作。首先人们要进入这个赛道,再在这个赛道跑到最前面,才能成为极少数。我住了多大的房子,我的年薪收入多少,在类似的评价体系下,产生被认为优等生的那种自我价值的满足。
新周刊:优等生这个词就非常“东亚”,我们从以前就会有“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到了现在也是会有“读的书更多,你就是人上人”的观念。感觉在东亚社会,人一出生就会进入一个赛道。
崔庆龙:对,它其实是一种隐性的精英主义。虽然说这是一个名义上强调平等的社会,但从小激励孩子的那种名言都包含着要超越别人的意思,隐含着一种“你要攀爬到金字塔的上层才能被承认”的意味。只有爬到高处,你才是被认为是对的、有价值的。我反而觉得,这个社会对平庸有一种不包容性。
新周刊:在中国社会或者说在东亚社会,一个人想要活得自由还是比较拧巴的。一些人会选择gap year或者是逃回到小镇。
崔庆龙:这个分成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有些人确实是想明白了,现在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他们做出了选择,切换到新的生活状态,这种人不会特别的纠结。
还有一种情况,我觉得更像是一种被放逐或者被驱逐的感觉。比如说,有些人在一线城市里拼搏,看不到希望,生存的成本越来越高,工作上的不确定性越来越明显,无形的压力就越来越大。我觉得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人,会有一种试着找回到一个更安全的洞穴或者小岛的那种心理,这其中包含了一种退缩和逃跑的意味。
但它终归是一个选项,哪怕你做了一个30分、40分的选择,至少还有一个选项让你避开最糟糕的感觉。这种后退至少让人先有了喘息的余地,也许未来有一天人们会回来,再重新出发。
新周刊:换个角度来讲,逃避也是人本能的求生行为。
崔庆龙:虽然说心理学强调,人应该面对自己的痛苦,或者说,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面对。但从另一方面来讲,我觉得人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直面任何痛苦。人合理的、周期性的退缩迂回,我觉得是健康的,是合适的。
因为你总有心理效能低的时候。当你只有20%的心理效能时,面对的困难如果有80%的难度,那么你就是战胜不了它,就是会被它击溃。所以我觉得暂时的退缩就是人会有的反应,不需要去批判。
所有的痛苦,都是在给你一条活路
新周刊:存在主义心理动力学里,人的负面情绪被归结为对四个终极关怀的恐惧:死亡、自由、孤独和无意义。你认为中国人的中年危机和对这四项关怀的恐惧有关吗?
崔庆龙:我觉得肯定是有的。就拿死亡来说,以现代人的健康状态来讲,长期处于996的高压环境下,不要说35岁,可能到30岁以后,很多人就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不如以前了。这种直接反应在身体上的状况,会让他们体验到一种和疾病、衰老、死亡有关的担忧,你可以把它归结到一种死亡焦虑的范畴中。
其次,这个年纪的人上有老下有小,可能还有房贷、车贷、负债什么的。他必须得让自己保持在一个能够持续创造所谓的经济价值的状态下。他不敢辞职、不敢消费、不敢做别的设想,很容易陷入到压抑和紧绷的状态。
在这个阶段,社会关系也会变得特别的单一。我发现很多人在这个年纪基本上没有什么朋友,就算有,双方可能也因为结婚、有孩子了,重心天然地向着家庭倾斜,逐渐丧失了以前那种高强度的情感陪伴和交流的机会,也没有时间和空间再去构建高质量的社会关系,人就陷入到了孤独的局面。
与此同时,无意义感也更容易出现。为了生存,人们也不敢去想“我到底该怎么活”“我是否应该去追求自己的理想”等问题。因为眼下的人生枷锁已经太多了,人们没有办法另辟一条路,去追求有意义、有价值反馈的生活。
新周刊:人的儿童时期,也正是大脑发育的敏感时期,如果经历了情感忽视、目睹亲人逝去、家庭冷暴力等负面事件,会对一个人的长期心理健康状态产生影响。童年创伤对日后的中年危机是否会有潜在的、长远的影响?
崔庆龙:一定会有的。如果一个人小时候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感受,但是被父母批判,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对真实感受表达的极大抑制。儿童会基于这样的经验,习得掩盖自己情感的能力,不去造成矛盾,会规避表达情感所可能带来的风险。长此以往,有一部分真实的、原始的情感冲动就一定会受到阻碍。
还有一种情况是,在成长的环境里,儿童的价值从来得不到承认和认可。这就意味着,如果未来有一天,外界对他学习或者工作方面认可的机制中断了,他无法获得正向价值反馈——这就像是一根极细的杆子支撑着庞大的价值体系,局面必然是岌岌可危的。
例如,有个人一直升学考试都很顺利,但是找工作碰壁了;或者说有个人一直都被视为天之骄子,但是有一天他在婚姻上失败了。这些情况都有可能动摇到他内心最深处、最脆弱的价值天平。
所以,成长中的负面经历,就像是或浅或深地给人生埋下了一颗颗的地雷,它会被一些事件所触发,从而引爆。未来某一天中年危机出现的时候,它可能不仅仅会动摇你的表层,还会把你内心最深层的那个东西也动摇了。
一个在幸福家庭成长起来的人,遇到困难可能只是沮丧一阵,因为他有自我支撑的内在经验。但对于有童年创伤的人来讲,他体验到的是双重痛苦,一重是客观现实上的,一重是他主观现实里对这件事的非常个人化的体验,比如有的人会觉得自己非常无能。这是性质的不同,也是程度的不同。
新周刊:在一个关于中年危机的采访中,有受访者讲道,“对各种关系感到无力,支配不了关系的走向,甚至是夫妻、亲子”。值得注意的是,中年危机中的情感危机往往不是独立出现的,而是伴随着其他危机共同出现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崔庆龙:我把一个人的生存视作一个结构问题,它其实是由很多的要素支撑起来,并形成一种平衡的。不管是亲密关系还是工作,当整个系统受到冲击的时候,也就是所谓的中年危机到来时,所有的方面都会受到波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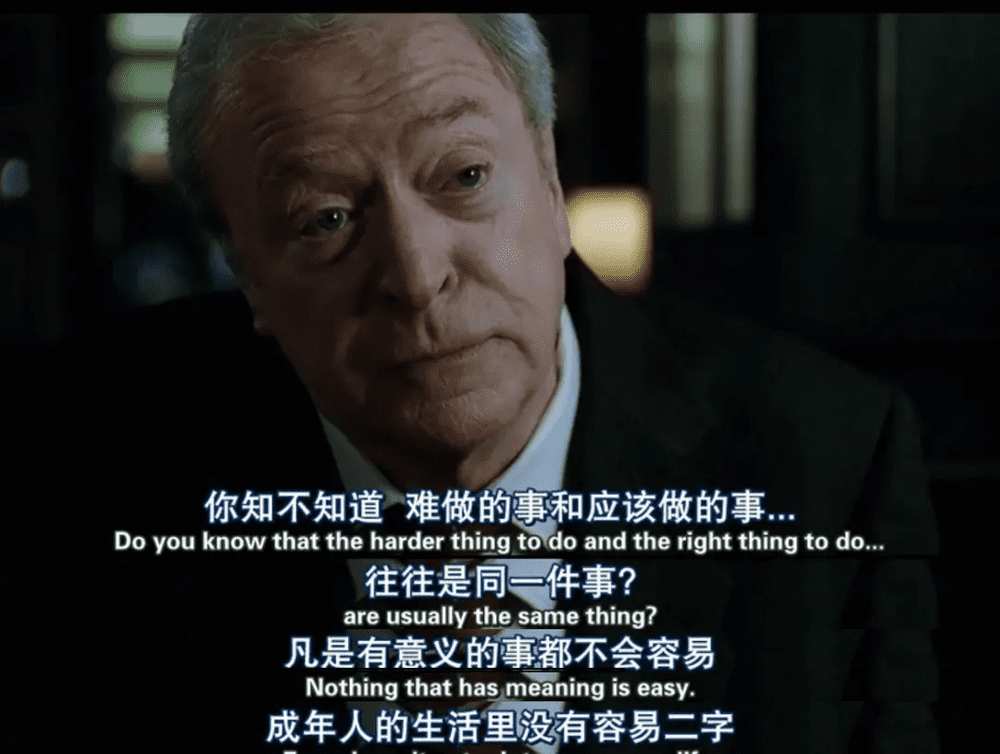
(图/《天气预报员》)
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没有太多价值感,回家以后还要去做饭、洗衣服,还要接受对方在情绪上的一些问题,这时候就会发现对情感更加不耐受,更容易爆发矛盾和冲突。
新周刊:“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到底为什么而活着?”从一出生开始,这些永恒的命题就一直伴随着我们。在成长过程中,这些问题可能被现实问题所掩盖而后置,但却始终挥之不去。这种无意义感可能会在35岁逼近时剧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种无意义感究竟从何而来?
崔庆龙:我以前写过一句话,无意义感来自于一个人最本真的情感冲动和他的生存目标发生脱节的时候。我要喜欢做一件事,我就被这个情感冲动支配着,奔着那个目标去了,整个过程我都是满足的。
但现在很多人感到无奈,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幸运到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当自己的本真冲动不能和指向生存的事务关联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容易滋生这种无意义感。
新周刊:有案例讲到,一些原本对生活并没有目标感的人在经历了濒临死亡的体验后,反而能够更好地珍惜自己的生命,并开始去做一些利他性的活动。对死亡、自由、孤独和无意义感的恐惧,是否有它们各自的积极意义呢?
崔庆龙:我认为所有的负面情绪都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有些东西出了问题,有些事情一定是违背了你最真实的生存意愿。
我以前说过,比起痛苦,更值得害怕的是一种生命的僵局。造成僵局的痛苦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你可以忍受,但是又很不舒服。它长期折磨着你、煎熬着你,但又不足以让你换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痛苦,我觉得是最更可怕的。
反而是那种突如其来的锐痛,可以让你跳起来,马上离开那个地方。所以,我觉得痛苦,某种意义上有一种积极的意义。
我不愿意去肯定痛苦,但是客观来说,有些人从精神危机中走出来以后,他们能够借助痛苦带来的契机,远离不好的关系或工作。所有的痛苦一定是在某种程度上试着给你一条活路,它有时候可能会摧毁人,但它本质上的作用是驱动人去努力求生。
找到自己人生的游戏主线任务
新周刊:在向你咨询的人当中,有没有关于中年危机的案例?能否举个具体例子说说TA的情况,以及最后是如何解决的?
崔庆龙:我觉得还蛮多的。我以前说,如果一个人不被生存所困扰,就一定会被意义和价值的事情所困扰。
我现在的咨询中有很多都是这类来访者,他们已经没有了生存的困扰,甚至已经过上非常优渥的生活,但他们当中有些人的痛苦体验是非常强烈的,就是因为没有价值感和意义感。
我有一位来访者结婚以后辞去了工作,做了一名全职太太。但她很难从全职太太的身份里得到价值。别人都说“你看你老公多好,多有钱,你什么都不用操心”,她会因此有一种自我麻痹和自我说服,觉得自己是不是想太多了,要求太高了。但与此同时,她又觉得好像哪里不对,以至于有一段时间非常抑郁。
我以前经常强调一句话,一个人的主观现实才是真正的现实,外人是看不到自己所感受的那个世界的。我们只有先尊重了自己的主观现实,才能够接受客观的限制,这个顺序是必然的,否则就是一种被迫式的妥协。
后来她重新去找工作。她的忍受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所以她尝试着走出那个僵化的系统。那个工作并不完全符合她的期待,但她觉得自己却像是获得了家以外的另一个空间。在那里,她体验到了另一种自我感,体验到自己在凭借能力做一些事,在和社会发生一些连接,这对她心理上的那种确立感是非常重要的。
新周刊:对一些35+岁的人们,你对他们对抗和度过中年危机有什么建议吗?
崔庆龙:我用打游戏来类比人生的状态,它应该要有些东西吸引你继续玩下去。在系统中,一旦你失去自己的目标,失去自己想做一件事的冲动的时候,这个事情就进行不下去了。
我们需要找到,更准确的来说是创建起自己的生命主线,就是找到一件能锚定你的价值感和意义感的事情。对每个人来说,都有一些生活中不得不去做的事,比如工作和日常社交。但我觉得除此之外,一定要有那么一件事,是你长此以往可以重复去做的、可以积累的、可以迭代的。它最好和你的能力相关,最好是被社会需要的,能让你凭着本能和冲动去完成。人需要把自己的价值感和意义感铆定在这么一条路径上。
新周刊:当外部环境变得越来越不可控,作为个体的我们,应该如何摆脱中年危机带来的无力感和倦怠感?
崔庆龙:现实生活中有一些真实客观的作用力在发生着。我们有时候需要放弃一些比较天真理想的想法,谨慎乐观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态度。
但更多的,我觉得还是需要建构一个自己的个人系统。因为大多数人的痛苦都来自于集体凝视,社会在期待你过一个怎么样的生活,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会让很多人自我怀疑,觉得自己是失败者。所以我觉得人要和这样的评价体系解绑,要去建构自己的评价体系,建立自己的时间线。
人生没有什么事是必须要做的,也没有什么必须执行的标准。前面说的,东亚文化和西方文化认为人们必须要做的事情,这两者都是虚妄的,都是人类建构出来的一套游戏规则。
某种本来不存在的潜在想法,由于大家都这样认同,它就好像变成了一个真实的东西。往深处探究,它是不存在的。所以我觉得人需要去解构很多定义,包括对幸福、成功、人生的定义,这也是很多人觉醒的一次机会。你必须要得审视,你自己是谁,你该过什么样的生活,你想过什么生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ID:new-weekly),作者:张文曦,编辑:萧奉、晏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