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中国人,世界上很少有人喜欢火锅。
这个说法来自作家符中石。确实,中国人恐怕是世界上最爱火锅的人群:一群人吃饭,众口难调,此时火锅是最不容易出错的选择;一家人聚会,图个热闹,还得是火锅;一对情侣约会,西餐厅心形牛排之类的只宜偶尔为之,还是火锅比较日常;一个人,当然也可以吃火锅——不要在意网上流行的那份孤独等级表(按其划分,孤独的第五级是“一个人吃火锅”),也忘了某捞为单身顾客提供的毛毛熊伙伴吧(这样反而显得更孤独),你应该像8岁的重庆男孩唐钱钱那样,怀揣一百多块压岁钱,在众人的围观中,一个人淡定地烫老火锅。
数据也支持了这一说法。辰智科技与口碑联合发布的《2017年度餐饮大数据白皮书》显示,在整个餐饮行业中,火锅的销售额占比名列第一,达到22%——毫无疑问,火锅已经成为第一国民美食。
“围在一起吃火锅的人,不是家人,便是伙伴;不是兄弟,便是朋友,不是极富人情味吗?”
中国人为什么如此热爱火锅?
学者易中天的解释是:火锅能最为形象直观地体现“在同一口锅里吃饭”这样一层深刻的意义,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共食”。“更何况,这种‘共食’又绝不带任何强制性,每个人都可以任意选择自己喜爱的主料烫而食之,正可谓‘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那样一种生动活泼的局面。所以,北至东北,南到广州,西入川滇,东达江浙,几乎无人不爱吃火锅。”
共食制源于原始社会。一个原始部族的日常是这样的:年轻力壮者外出采集和狩猎,年长体弱者留守看火。日暮时分,倦鸟知还,外出的人也回到驻地,大家围着火堆享用熟食,也就是所谓“共火而食”。所以,易中天说,共火而食的人就是“火伴”,见《木兰诗》:“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惶。”后来,“火伴”变为“伙伴”,不同的人因同一目的而结合成群体称为“结伙”,并由此产生合伙、入伙、打伙、搭伙、散伙、团伙、平伙等概念,“火食”也就变成了“伙食”。
“火锅,大概就是对原始时代和古代战争中,‘共火而食’的远古回忆吧!中国菜肴,无论煎、炸、蒸、炒,一般都是在厨房里加工完成后才端上桌来,只有火锅把烹调过程和食用过程融为一体,不但把锅端上桌来,而且让火贯穿始终。这不正是一种最古老也最亲切的方式吗?围在一起吃火锅的人,不是家人,便是伙伴;不是兄弟,便是朋友,不是极富人情味吗?”易中天这样写道。
在易中天看来,火锅热,表示“亲热”;火锅圆,表示“团圆”;火锅用汤水处理原料,表示“以柔克刚”;火锅不拒荤腥,不嫌寒素,用料不分南北,调味不拒东西,山珍、海味、河鲜、时菜、豆腐、粉条,来者不拒,一律均可入锅,表示“兼济天下”;火锅五味俱全,主料配料,味相渗透,又体现了一种“中和之美”。
“火锅不仅是种烹饪方式,也是一种用餐方式;不仅是一种饮食方式,也是一种文化模式。独食难肥,共食才能吸取营养;独食无味,共食才会其乐无穷。这就是请客吃饭的意义了。它不仅是吃喝,而且是共食;共食也不仅是聚餐,而且是同吃;同吃也不仅是同在一起吃或吃同样的食物,更是吃人情,吃血缘。有了人情和血缘,一个又一个群体才得以建立和巩固,个体也才得以生存。显然,中国人喜欢请客吃饭,并不是中国人好吃,而是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群体意识所使然。”易中天总结道。
“‘大同’不远,就在火炉旁边。”
“再一日来,天下起了小雨,寒气逼人的,都添了衣服。午饭时,临时又添了一个暖锅,炭火烧旺了,汤始终滚着,菠菜碧绿,粉丝雪白。偶尔的,飞出几点火星,噼噼啪啪地响几声。半遮了窗户,开一盏罩子灯,真有说不出的暖和亲近。这是将里里外外的温馨都收拾在这一处、这一刻;是从长逝不回头中揽住的这一情、这一景;你安慰我,我安慰你。窗户上的雨点声,是在说着天气的心里话,暖锅里的滚汤说的是炭火的心里话,墨绿的窗幔里,粉红的灯下,不出声都是知心话。”
这段关于暖锅的文字,来自作家王安忆的《长恨歌》。作家马家辉因此感慨道:“严寒里,还有什么食事能比吃火锅更为应景?我不相信有。”马家辉写有一篇《打边炉美学》,他笔下的港式“打边炉”和王安忆笔下的上海暖锅不是一回事,但在给予人们温暖这一点上,并无差别。“温暖之感不必然来自食物和炉火,而大可源起于身边的人,此时此刻此模样,你跟他们挤坐到一起,每人用一双手去做相同的烹调,大家一样,你我他原来没有差距。‘大同’不远,就在火炉旁边。”马家辉写道。
马家辉在文章中表示,火锅的热气蒸腾弥漫,是最好的面具,“让人仍然看见你,但看不见真的你”。吃火锅的美学在于“留白”,“你不必急于用声音填满饭桌,在手忙脚乱里,没有人会迫你表露自己”。当然,如果你的心情够好,吃火锅的美学则从白变红,“那是红尘的红,红得热闹”。
也有人不喜欢这种热闹,比如袁枚。袁枚是著名的火锅一生黑,他在《随园食单·戒单》中有“戒火锅”一说:“冬日宴客,惯用火锅,对客喧腾,已属可厌;且各菜之味,有一定火候,宜文宜武,宜撤宜添,瞬息难差。今一例以火逼之,其味尚可问哉?近人用烧酒代炭,以为得计,而不知物经多滚总能变味。”
袁枚厌恶火锅的理由,一个是心理上的——“对客喧腾,已属可厌”;另一个是生理上的——“物经多滚总能变味”。袁枚晚年的最大遗憾是没能参加乾隆五十年(1785)举办的千叟宴,在诗句中感叹“路遥无福醉蓬莱”。媒体人李舒在文章中表示,其实袁枚用不着这么惆怅,“因为赶到北京城里,他将见到的是自己笔下最令人厌恶的场景:5900多个老头聚集一堂,吃1500多个火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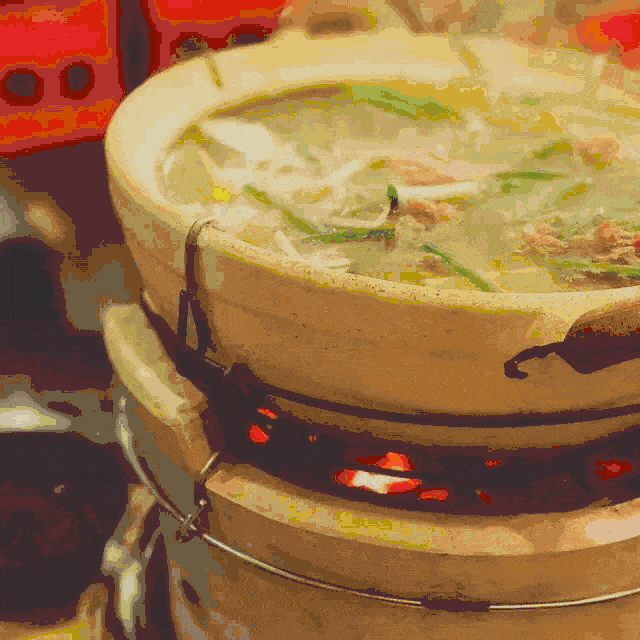
盛行于粤港的打边炉。
点解港片、港剧中有这么多打边炉的场景?
电影《老炮儿》中,张涵予扮演的“闷三儿”从拘留所出来,几个老哥们儿用一顿老北京铜锅涮肉给他接风,一边吃肉喝酒,一边商量怎么解救冯小刚扮演的六哥的儿子。有影评人如此评价:“看一场《老炮儿》,像涮了顿羊肉,或是吃了盘儿饺子,家常但有仪式感。”
电影《无间道2》中,也有一场描绘几个香港黑帮大佬打边炉的大戏。那一天的设定是14号,也就是黑帮大boss向各个堂口“收数”的日子。社团话事人倪坤刚刚被人暗杀,其子倪永孝(吴镇宇扮演)仓促接班,几位大佬遂约起打边炉,密谋“政变”。晚到的大佬韩琛(曾志伟扮演),一坐下就抄起筷子大口吃肉。大佬们各怀鬼胎,眼神诡诈;各路人马在火锅店(据说这场戏是在位于土瓜湾的鸿福四季火锅店拍的)进进出出,感觉随时有事发生。场景、人设、道具、台词都完美匹配,这一幕也因此成为《无间道2》乃至香港影史中最令人难忘的场景之一。

电影《无间道2》中打边炉的经典一幕。
问题来了:点解(粤语,意为“为什么”)港片、港剧中有这么多打边炉的场景?以TVB剧为例,《冲上云霄2》中,cool魔和一群年轻同事打边炉,表示他还是食人间烟火的;《使徒行者》中,佘诗曼扮演的钉姐和“handler”(联系人)卓sir(苗侨伟扮演)第一次接头,就是吃海鲜火锅,桌上摆满象拔蚌、三文鱼、竹节虾、生蚝等好料,钉姐一个人吃得不亦乐乎还要打包,接地气得简直不像拿命去搏的卧底;《心理追凶》中,杨明扮演的自闭症天才每次打边炉,总是一股脑将整盘牛肉倒入锅中,让敖嘉年扮演的Win Sir直摇头。
港片、港剧中,打边炉总是与这几个关键词紧密相关:阿Sir、古惑仔、江湖、侠义。针对打边炉成为古惑仔标配的疑问,作家马家辉曾专门打电话请教过道上的人,原因之一是“吃火锅不用等”——“随来随点随吃,什么时候都可以加入。加个人添双筷,多点一碟肥牛肉便可继续无限时地吃下去。”还有一个原因,应该就是火锅简单、直接到一目了然,又很市井,最适合表达兄弟情谊。
“火锅的确能折射出中国文化的特性——强大的包容性。”
韩国作家金宰贤写有一篇《火锅里的中国》,称自己1998年第一次短期访问中国时,就迷上了火锅。数年后,他来到北京大学读MBA,对中国的了解更深入,他还是坚信,火锅对自己来说是最好吃的中国菜,没有之一。
“通过火锅,我发现中国擅长于接纳新的因素。别的国家类似火锅的料理,如韩国的神仙炉、日本的Shabushabu(即しゃぶしゃぶ,日式涮锅)及泰国的Suki,放在汤里的食物数目远远不及火锅。在这一点上,火锅的确能折射出中国文化的特性——强大的包容性。火锅的包容性才使得它更加丰富多彩,同样的道理能活用于中国文化上。”金宰贤写道。
他还注意到火锅的发展变化,那就是“一人一锅”的小火锅越来越多。他认为“一个一锅”得以出现,最重要的原因是个人主义。“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个人主义已经得到很多人的支持,能尊重对方的、成熟的个人主义当然没有任何问题。可是,我还是更愿意和朋友吃‘大火锅’,因为我觉得大火锅能够让我们交流得更好。”

美食大咖安东尼·波顿(左三银发者)在录制《未知之旅》时来过成都,并大啖火锅。
国人热爱火锅,也乐于看到火锅能够征服外国人。在豆瓣、知乎上,有不少老外如何折服于火锅的绘声绘色的帖子,点击量都不差,网友们在阅读时,往往有一种“与有荣焉”的自豪感。在成都当英文教师的雷蒙(Ranmon)是一个重度火锅爱好者(每周至少要吃两次火锅),他和几个老外合作,创作了一首名为“Hot Pot”的歌,表达自己对火锅的热爱:“Hot pot,hot pot,wo yao hot pot /Hot pot,hot pot,wo ai hotpot/Hot pot,hot pot,you know,hot pot/Hot pot hen hao chi……”(火锅,火锅,我要火锅/火锅,火锅,我爱火锅/火锅,火锅,你知道,火锅/火锅很好吃……)网友们纷纷表示,听这首火锅之歌,会听饿的。
易中天说,白居易那首著名的“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我怀疑那就是请朋友来吃火锅的邀请函”。
来吧,一起来吃火锅!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夜读书课(ID:Read-at-night),作者:谭山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