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 (ID:BooksAndFun),作者:董子琪,编辑:黄月,题图来源:《小丑》
“笑死”,是一个常用语。互联网上很多人对很多事的态度都是“笑死”,以及万物皆可“哈哈哈”。“笑死”有许多变体,像是笑得头掉、笑发财了、笑尿和笑屎等等。中国台湾歌手陈珊妮在演唱会上以滚动字幕讽刺“笑死”:“那些杀不死你的,可能会让你笑死。笑之前要先确定自己到底看了什么。”
可是,人们为什么总是“笑死”?
笑尿、笑屎、笑得头掉
笑具有身体性,屎尿屁的排泄、哺乳期女性泌乳都能成为笑料。郭德纲的相声被批“三俗”(庸俗、低俗和媚俗),是因为当中不乏“芝麻酱攉红糖”、混淆粪便与吃食的笑话,也有妈妈喂奶喂到学校里、搅乱课堂和学校秩序的荤味段子。关于身体的笑话并不是相声的独家发明。
在电视剧《漫长的季节》里,中老年三人组从“厕纸用得多不耽误你擦嘴”的唠嗑当中发现了一种自渎的快乐;殡仪馆也要聊两句骨灰级笑话,秦昊饰演的龚彪问工作人员,“怎么,人犯了事儿骨灰都不给人留啦?”《人在囧途》里王宝强饰演的农民工和徐峥扮演的总经理阴差阳错地挤在小宾馆的同一张床上,折磨文明人的是“乡里人”的磨牙、放屁还有裸睡。
赵本山《卖拐》系列小品展现出的则是,在春晚营造的盛大喜庆场合中,观众甚至期待着范伟饰演的角色从脑袋大脖子粗、站不稳要拄拐,一步步病入膏肓到躺担架。苗阜王声的相声《这不是我的》讽刺贪污官员惯于推脱所贪赃物不是自己的,由车子房子一直层层递进到了女秘书及她产下的孩子。
屎尿屁、乳汁和骨灰都产自人体,这些无法控制的身体现象搅乱了秩序,也使得庄严肃穆的氛围瞬间坍塌。在殡仪馆说出“人犯点错,就骨灰也不给留啦”无疑破坏了宁静哀思的氛围,在课堂上跑来跑去的敞胸露乳的妈妈同样迷乱着师道尊严与严肃意志。
粪便在喜剧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幽默》中写道,因为粪便能将意义与价值的一切差异拉平,成为永远同质的东西,因此,喜剧与犬儒主义仅一线之隔,视万物为粪便意味着摆脱了严格的等级制度,也摆脱了崇高理想的胁迫,获得了一定的解放和自由。人们在大笑后长舒一口气,事物比原来的样子更加轻松、易于理解——原来徐峥扮演的文明人大老板也会在屎尿屁的原始攻击下落荒而逃,而王宝强饰演的农民工傻人有傻福、傻瓜有好运。
嘲笑身体最极致的情况应该是头掉。头掉了的笑话不仅出现在郭德纲与于谦的相声里,更有其文学传承。施蛰存的小说《将军底头》中令花惊定将军猛然惊醒的,是溪边少女的不觉失笑,“喂!打了败仗的吗?头也给人家砍掉了,还要洗什么呢?还不快快的死了。”笑戳破了将军的爱情迷梦,也击溃了他的壮志雄心。并不只有我们喜欢嘲笑“头掉”,美国单机游戏《双点医院》的掉头笑话同样典型——患有光头症的病人来到医院,本来应该是头颅的位置顶着一颗电灯泡,医生需要将这颗电灯泡拆下,替换上一颗随机生成的人头。
最近逝世的作家米兰·昆德拉在《笑忘录》中说,笑是对于一个整齐有序、意义充沛、构思精妙的世界发出笑声,是站在乏味的、永远满面春风、向未来大踏步前进的“天使”对面。所谓天使,并非善的战士,而是造物的信徒,而魔鬼,是拒绝承认世界的理性意义的;人们的世界就在天使与魔鬼的分治之中,两方势均力敌,“如果世界上有太过毋庸置疑的意义(天使的权力),我们会被它压垮。如果世界丧失了所有的意义(魔鬼的统治),我们也无法活下去。”伊格尔顿《幽默》中的观点部分可以追溯到昆德拉对笑的理解。
一直“笑死”,一直苟活
“笑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弗洛伊德所称的死欲,伊格尔顿将死亡和好笑联系在一起,因为就像死亡能够摧毁一切价值,好笑也能够扭曲意义、搅乱等级以及混同身份,因此笑从未远离过死亡与坟墓。米兰·昆德拉在《笑忘录》中描摹过一次在坟墓前的大笑,因为一顶滑稽的帽子盖到了死者的头上,送葬的人们终于忍不住爆发出激烈的笑声。然而,这样抹平一切的笑距离集中营亦不远了,伊格尔顿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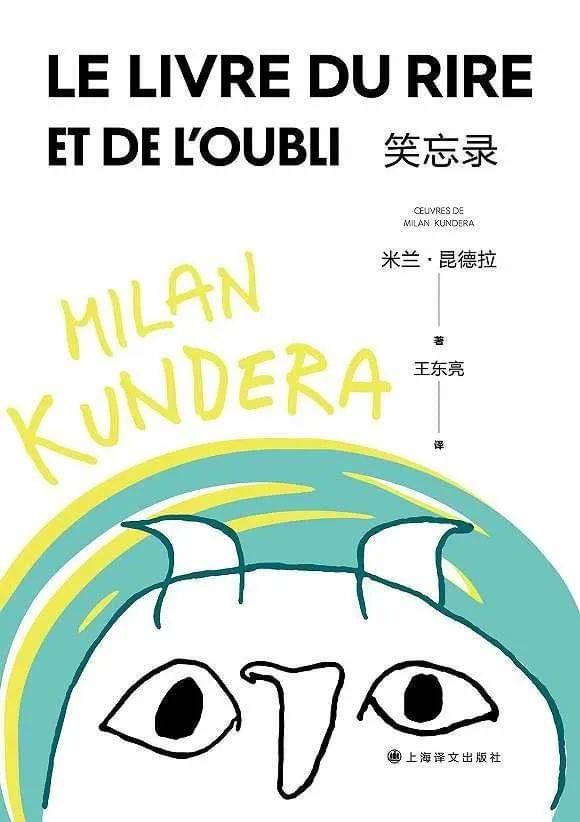
《笑忘录》 米兰·昆德拉 著 王东亮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2年
“集中营”的意味放在今日“地狱笑话”(指以他人的不幸和缺陷开玩笑)盛行的语境里更好理解。低于凡庸日常的麻木无聊的笑话,消解所有价值与意义,同时也渴望荒诞度的飙升和更强烈的撩拨。豆瓣“哈组”用户不断浏览着新的尴尬的经历,弹幕上飘过更多的笑死、xswl(笑死我了),笑的爆炸性在持续的“笑死”中消散。
“社会性死亡”小组的分类按照尴尬级别分为尸体默哀至尸体火化。如果说“包法利夫人”式的阅读被批评为基于感官而非认知,这样的阅读不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社会和人性,而是在文本欢愉中自我迷失,那么这一类观看也是类似的。对于包法利夫人式的读者,好的作品能提供玫瑰花一般的浪漫想象,而对后者来说,好的段落就是能有“笑死”一回的机会。
笑具有魔鬼性质,《笑忘录》写道,对纯洁无聊的天使最狠的嘲笑来自为唯物主义者星象算命的桥段。“我”被开除教职之后,匿名为星象专栏写作,某位位高权重者托人来找“我”推命,“我”一方面很清楚那些议论双鱼座、金牛座和白羊座的散文是胡扯,另一方面又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因为那位高人根本不敢承认自己曾诉诸于星象玄学。“我”的胡扯与偷偷摸摸固然是可笑的,可比这更好笑的是表面上装得一本正经的世界。
这里的情况类似于当代“笑死”的另一种转换性用法,即以“笑死”自嘲和讽刺,而讽刺效果大过于自嘲,像是“我做了很详细的理财规划,结果根本没存款,笑死”。与“笑死”搭配使用的词汇还包括“破防”,“果然破防了,笑死”。令“我”笑死的不是自己的无能和伪装,而是亲眼看到了现实如想象中荒诞,于是这里的“笑死”也如同一种宽慰,等于说,还好,如我所想,这个世界本来就如此。
喜剧要求心暂时处于麻痹状态,以观察到人世间就那么回事。伊格尔顿赞同这类观点: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或许就在暗示,人这个物种就是个笑话,不用太在意。人潦倒至极的时候,反而会产生一种奇特的感觉,好像自己是不可战胜的,这样一来,有限的小人物面对什么样的灾难都能安然度过,苟活着,并且一直“苟”下去。这难道不令人想起卑微却无法战胜的阿Q吗?苟活与声称的“笑死”好像是相反的,同时也指向了“笑死”的另一种结果,用陈珊妮的话来说就是,“笑死”是与世无争的倾向,是活在当下遗忘过去的状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 (ID:BooksAndFun),作者:董子琪,编辑:黄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