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 (ID:BooksAndFun),主持人:徐鲁青,编辑:黄月、尹清露,原文标题:《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断亲”|编辑部聊天室》,头图来自:《四重奏》剧照
“我做得非常坚决,微信不回,问候不发,祝福更是从没有。有时候亲戚提出想来我家小住,或者打电话找我帮忙,我都会直接拒绝。”
在近期《三联生活周刊》一篇题为 《33岁,我带着父母一起“断亲”》 的热文中,居住在大城市、从事文艺工作的作者关于“断亲”的自述引发了许多人的共鸣转发。“断亲”的概念出自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胡小武的论文《青年“断亲”:何以发生?何去何从》,它被定义为人们几乎不同二代以内的亲戚互动和交往的一种现象。这篇论文提到,如今年轻人与亲戚的联系越来越少,大多数30岁以下的年轻人“偶尔与亲戚有联系”,而18岁以下的调查者则大多“基本不怎么与亲戚联系”。
这份研究结果并不让我感到惊讶。不管是身边的同龄人还是自己,也早就和父母以外大多数亲戚几乎没有了交往,连微信好友都很少加,只有在过年回家时草草说几句话,面对着来自生活经验差异巨大、边界感较弱的长辈说教,每年几乎要靠倒数逃脱时间来捱过这些场面。对我来说,血缘远近几乎和关系亲疏无关。当亲属关系不再是重要的社会支持网络的时候,我也会有意识去建构以趣缘和位置为基础的支持系统,我知道在未来大多时候,陪伴我的更可能是朋友、同事,甚至同一层楼的邻居们。
当血缘无关亲近
潘文捷:每次回到县城老家,我总会感受到家族的力量,同时也感受到父权制家庭的束缚。你会感到很多老一辈觉得自己是绝对真理,“怎么可以这么和长辈说话”一句话就可以噎死所有讨论。
最近读到《文学中的人生进化课》,华东政法大学文学教授杜素娟在分析《雷雨》时说,周朴园这个角色原本坚决和女仆恋爱,如果放到巴金的书里,真可谓是个进步青年,而且上了年纪以后,他其实也挺爱孩子的,虽然表现得有点拙劣。可是,怎么到头来,给孩子们的感觉就只剩下压制、控制、威严,别的什么也没有了呢?问题在于社会对父亲的定义。
在中国文化里,父亲就是要掌控全家的人。其实身处在父权制家庭中的每个人,哪怕不是那个“父亲”,都会受到这种文化的荼毒,比如长辈会觉得小辈就应该听话,儿子觉得妹妹就应该为我做出牺牲。“断亲”是主动远离那种有毒的环境,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心理上的“弑父”。
董子琪:What?周朴园是进步青年?还可以这么比较啊?
没有想要特意去“断亲”,但事实上因为生活环境的远离,联络得已经越来越少了,尤其这几年过年回去得少,断不断的都冷淡得差不多了,以至于收到姑姑的红包都觉得不好意思,好像红包是唯一联结侄女和姑妈关系的纽带了,只有钱才能收买我对她的姑姑身份的认可。不过,因为生了小孩的缘故,表姐表妹家的婴儿物品倒是经常往我这里运送,代代相传的婴儿服、小花被、婴儿车都能体现我们亲缘的紧密相依。讨论育儿大概能拉近距离吧,表姊妹又能从育儿聊到婚姻事业种种,像真正的大人一样对话。
读童话《柳林风声》诺顿注解本读出了同感——里面说,鼹鼠从家出发,在远方得到和解。这不也是我所经历的生命历程吗?起初像小鼹鼠一样,从狭窄的洞穴中走出,想要挣脱家庭和亲人的说教、捆绑,经过冒险的旅程,终于抵达了远方,却在这里重新发现故乡。现在的我已经到了和当年的姨妈姑妈差不多的年纪,却远远没有她们慈爱、会照顾人,但多少也体会到了身为母亲和长辈的心情。想起大年夜鞭炮响起时姑姑用绵绵的双手严丝合缝地捂住我耳朵,还有姨妈跑到我家里一边数落我爸一边旋风似地打扫卫生。比起女性长辈,我的生活要更简单、更轻拿轻放,或者说更缺乏情感?
尹清露:我觉得“断亲”有可能是双向的。几年前写过一篇返乡青年回家过年的稿子,采访对象说每次回家亲戚们的烦心事都很多,比如孩子找不到好工作,这与他们对子女二十四五成家的愿望太远了,因而心照不宣地不提相聚的事。孩子代表着希望,是凝聚家人的缝合剂,当孩子长大并倍感失落,作为长辈也不好受吧。
这也让我想起蒋在的小说集《飞往温哥华》,里面人的关系就十分隔膜。中年母亲独自飞去加拿大,陪患有抑郁症的儿子租房,母子俩都很穷,好像也根本不存在亲戚这回事。她看到路过的情侣都会黯然神伤:如果儿子能谈个恋爱,或许就不会生病了。虽然写的是异国经验,读起来却莫名很熟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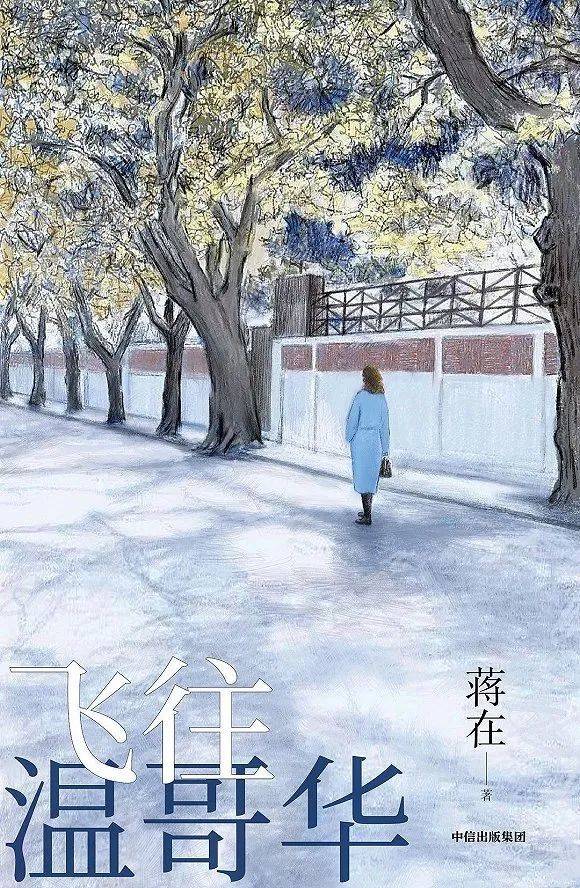
《飞往温哥华》
蒋在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3年
就我和周围人的经验来看,平时我们需要即时的抚慰、建议或者资源互换,而这些社会性支持不要说亲戚了,连亲近如父母也难以给予。另外,人类学者Marilyn Strathern认为,亲缘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基因继承的层面,另一个是知识层面。孩子自己构建的知识世界会导致和亲属的分离,但他们为了在信息更迭的社会上存活又必须这样做。而随着冻卵等技术的发展,我们已经在逐渐步入前者不如后者重要、DNA与亲密感越来越无关的时代,所以年轻人和亲戚关系变淡大概也是一种必然。
徐鲁青:我对清露提及的知识构成如何影响亲属分离还蛮有感触的。每次和亲戚沟通,最大感受是发现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我非常不一样,似乎还活在20年前的场景里。比如觉得十点之后的街道会很危险,但实际上现在十点钟很多人才刚加完班;比如认定一旦拿到博士学位,就可以一劳永逸当大学教授,但现实里很多只能签研究员合同工。
年长的亲戚们因为根本无从意识到已经和现在的世界脱节,又自信于更年长就可以为后代指点方向,所以总是说出一些啼笑皆非的建议。我常常在感到生气的时候有悲哀也内疚,我也是在信息边缘的世界出生长大的人,现在成了拼命想理解信息更迭并迎头跟上的人,但我已经没有余力再告诉他们自己认识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了。
“断亲”是进步还是问题?
徐鲁青:一则媒体采访提到了年轻人“断亲”的想法——“当你没有价值的时候,你也不要想去利用别人。”“有求于人的时候,她一般都用钱解决,极少借用人情。”我们该怎么看待“断亲”所强调的“边界感”呢?虽然边界感为我们带来了个人生活的便利,但现代社会交往中会不会有过分强调边界感的倾向?这是否会导向另一种由交换主导的人际冷漠?研究“断亲”现象的胡小武也在采访中提到,在割断亲缘网络体系后,人们需要建构属于自己的社会资本网络,这种建构的模式理论上来讲会更加理性。
林子人:前些年每到春节,互联网上就会出现关于“过年回家”的吐槽,现在年轻人是直接“断亲”了吗?青年学者罗雅琳对“过年回家”集体吐槽现象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年轻人在谈“边界感”的时候,到底在表达什么:它是一种为适应原子化的陌生人社会而出现的现代价值观,它是在大城市生活工作的年轻人反击父辈的唯一武器——年轻人的真正身份是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的“都市新穷人”,如今的“断亲”叙事与其说是传统故事模板中的“寒门贵子一朝发达就六亲不认”,不如说是对强势的、有更雄厚经济基础和更稳固社会地位的“小城中产”亲戚怀有某种抗拒情绪。
有“断亲”的年轻人在接受采访时说,“当你没有价值的时候,你也不要想去利用别人”。这句话中就流露出了经济实力、社会资源不对等中“我”的窘迫,而所谓的“维护边界感”,不过是用“尊重个人空间”这一绝对正确的现代价值观掩饰自己的失落罢了。
“断亲”现象还让我想到了NHK的《三十不立》。那本书中提到,经历了经济冰河期就业形势不断恶化的日本“三十代”(30多岁的群体)中,出现了一群切断了所有亲友联系,即使流落街头甚至孤独死都不愿向亲友求助的人。调查记者得出的结论是,在一个越来越强调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社会里,那些年轻人内化了“自我责任论”,无法凭借自己的能力在社会中站稳脚跟——即使这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他们的错,而是一个社会结构性问题——让他们深感羞耻,是这种羞耻心阻止了他们向他人求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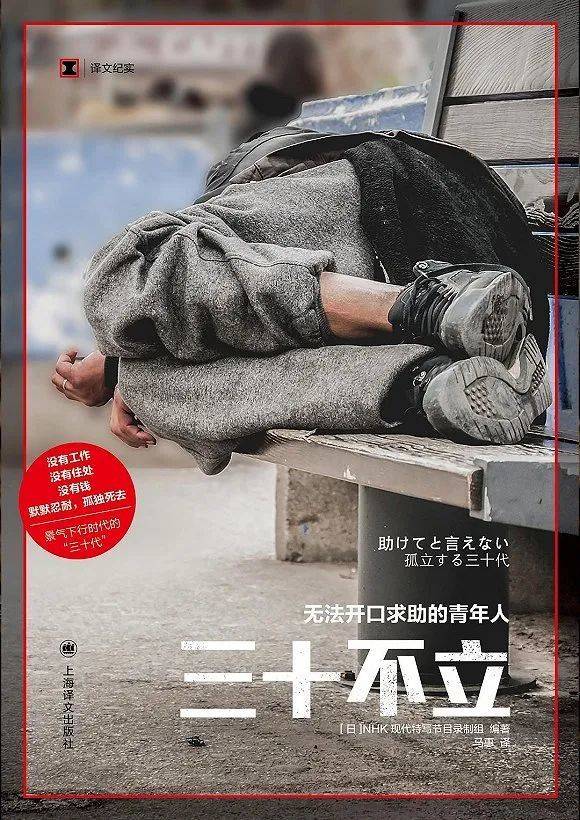
《三十不立》
[日] NHK现代特写节目录制组 著 马惠 译
译文纪实·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2-09
再回到“断亲”这个出现于中国社会的问题来看,我们且抛开绵密的熟人社会对个体意志的压抑这一层不谈(年轻人因此希望与亲戚们划清界限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断亲”现象之下,是否也有经济焦虑的原因呢?《收入不平等》提出,当经济不平等越来越严重,人们会因为不断增长的社会评价威胁而退出公共生活,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会增大,人们会越来越自我封闭,左邻右舍的关系会疏远,人们会因为担心自己遭遇负面评价而倾向于“离群索居”。当“断亲”不再是一个新奇的现象,而是一个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现象时,它值得我们警惕,因为这一定意味着整个社会出现了某些问题。
徐鲁青:我倒觉得,有的断亲不一定是窘迫的年轻人对更强势的“小城中产”亲戚感到抗拒。很多时候,在城市里发展较好的中青年们也会选择和更弱势的亲属断绝关系,即便如此,这种故事套用为“寒门贵子一朝发达就六亲不认”也是不妥当的。
人和人的关系太复杂了,更多的时候牵连着情绪、情境、说不清道不明的偶然性,只涉及到权力高低的描画或许是不够的。华中师范大学的文学院教授戴建业曾拍过一期讲断亲的视频,他认为“断亲”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因为当代社会的亲疏关系不应该由血缘决定。我同意血缘与亲疏的弱相关是现代性的特征之一,也解放了我们的情感关系,但总觉得人们越来越频繁地提及“断”“边界”“个人空间”,这自由里也充斥无奈,对关系的理解除了“断”与“连”、“亲”和“厌”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想象的可能?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 (ID:BooksAndFun),主持人:徐鲁青,编辑:黄月、尹清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