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 (ID:BooksAndFun),主持人:董子琪,编辑:黄月、尹清露,头图来自:《孔乙己》
我们此前在聊天室聊过年轻人去做轻体力活的趋势,今天不妨进一步讲讲眼下流行的“孔乙己的长衫”这个词所代表的集体困境。
近来,不少年轻人在社交网络上发出了“脱不掉孔乙己的长衫”的感叹,哀叹自己无法摆脱“受过教育就应该坐办公室”的成见。“孔乙己”本是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在鲁镇的酒铺前,他是唯一站着喝酒却身着长衫的人,长衫标志着他的身份与穿短褂的众人不同。原来他读过书,只是长年不得志,所以过得愈来愈穷,可令人不解甚至感到可笑的是,他明明穷得已经要去要饭,还执拗地坚持自己的长衫,说些之乎者也的话。
看到这样的讨论时,我感觉有点复杂,因为在小说里,作为孔乙己的观察者,酒铺的小伙计“我”因年纪或职业的缘故,其实与嘲笑侮辱孔乙己的众人是区别开来的,同时也是与孔乙己有过“业务交流”的人,孔乙己还曾恳切地教给“我”如何写字将来做掌柜记账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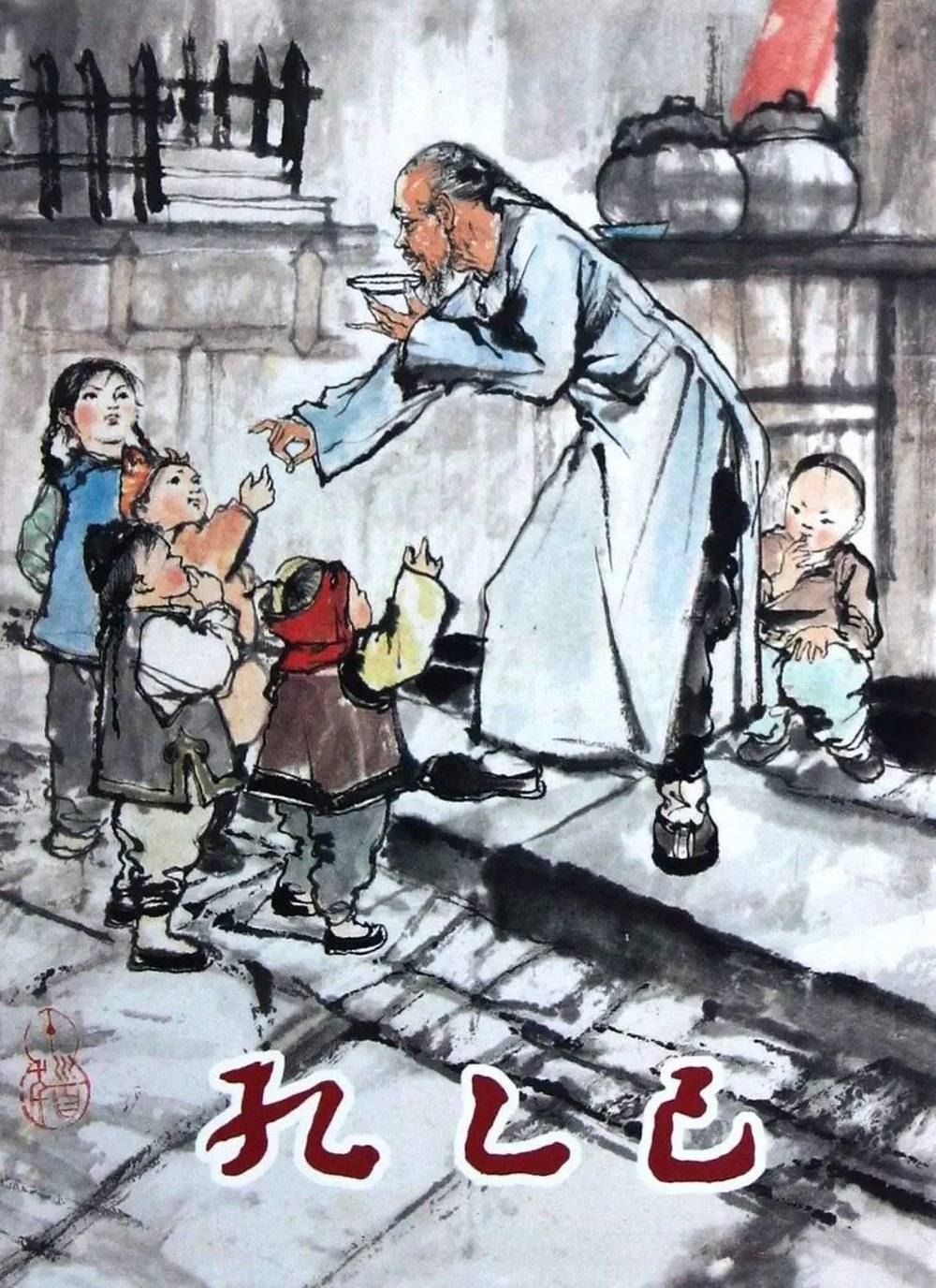
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从小伙计变成了酒铺的看客?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大家这样概括孔乙己的困境,似乎完全否定了孔乙己的存在价值,也拒绝要与这样的人交流似的。
除了孔乙己,鲁迅笔下还有过其他的知识人,像是《孤独者》的魏连殳和《在酒楼上》的吕纬甫,这些处于孤独、痛苦以及失意中的人物也与他自身的经历形成了对照。从当下评判标准来说,这些角色也都不是出人头地的成功者,甚至不是“充分实现自我”或“与自我和解”、“见解通透”的形象。酸腐、拧巴、迂腐诚然是不太令人愉快的读书人品质,但这其中是不是也有一些误解呢?
我最近读到了范雨素的一则采访,她讲到自己成名后,有怀揣着文学梦的劳动者来找她,她劝告大家最好不要有文学梦。“文学梦”本身是有趣的说法,好像直接指向了那些怀揣着文艺梦想、不务正业好高骛远却容易陷入圈套的人。范雨素大概对这个题材思考得较为成熟,在《大哥哥的梦想》里,她就写了一个靠着成功梦想活得颠三倒四的人。农民大哥哥居然想要造飞机,花了很多钱,拜托了很多亲戚之后,才决定要踏踏实实做个农民。
有意思的是,如果说穿着长衫的年轻人陷入困境是因为他们不够“踏实”,就像孔乙己一样认不清现实,那么人们会如何评价那些怀揣着文学梦改变命运的人,写诗的快递员、写小说的月嫂是想要穿上长衫的人吗?这件长衫,脱下了就够踏实,穿上了就不踏实吗?
有人曾努力穿上长衫
潘文捷:竟然要哀叹自己无法摆脱“受过教育就应该坐办公室”的成见!这有什么好哀叹和反思的?农民家庭的小孩拼命学习,考上大学,不就是想要改变命运,坐办公室吗?人们渴望获得文凭的符号价值,凭借文凭所带来的地位做“脑力劳动”的闲职,通过统治结构而非生产结构来获得物质产品。这没有什么可以羞于承认的。
徐鲁青:这段时间很多媒体都推送了关于年轻白领们做副业、降薪转行、从脑力劳动转为体力劳动的内容,他们的生活似乎变得更快乐了,越发显示出放不下办公室工作是孔乙己们受成见束缚的结果,但是,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想象偏差呢?我最近在微博上看到了某工地25万年薪招泥瓦匠的照片,下一张图就是一段新闻报道的截图,说的是一位泥瓦匠被欠了25万工资。
叶青:也许有些人确实从“脱下长衫”和体力劳动中获得了乐趣和解脱,但也有很多人正是因为早早领略到了“踏实”的苦闷,才选择努力“穿上长衫”。
我想到在小说《斯通纳》里,斯通纳在父母的坟地回望他们耕种了一辈子的农场:
“想到年复一年被这片土地压榨付出的代价,而它一如从前——更加贫瘠,也许,更加歉收。一切都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在毫无欢乐可言的劳作中延续着,他们的意志崩溃了,他们的心智麻木了……慢慢地,潮湿和腐烂将侵扰那副承放着他们尸体的松木棺材,慢慢地,这些将触碰到他们的肉体,最后将消蚀掉他们最后的物质的痕迹。他们将变成执拗的土地毫无意义的组成部分,而在很久以前,他们就把自己献给土地了。”
斯通纳如此渴望知识的部分原因,也在于他不愿和恐惧于献身给土地,而此时规劝斯通纳们脱下长衫是否有些过于苛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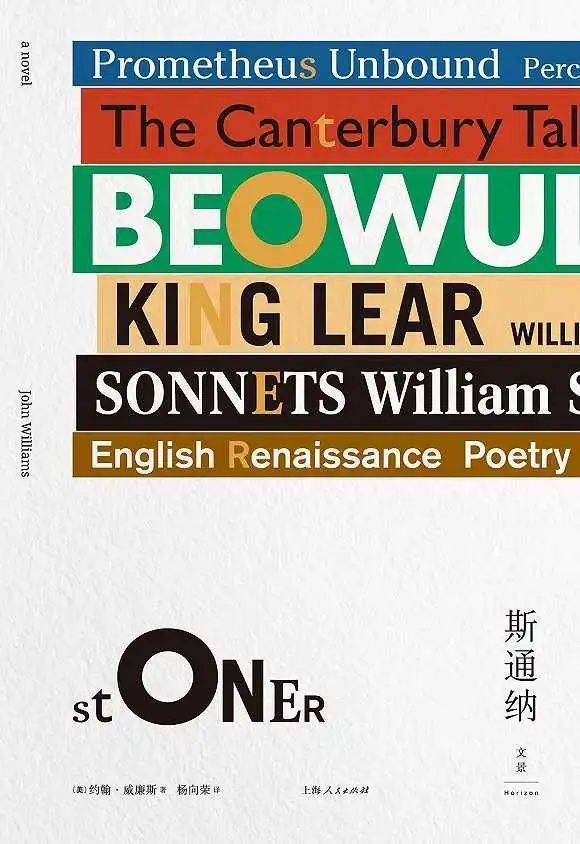
[美] 约翰·威廉斯 著 杨向荣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董子琪:斯通纳这个例子太好了!斯通纳就是典型的选择穿上长衫的人,他本来是学农学的,后来才转成了文学专业,虽然这会让父母有被背叛的感觉,他们来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却被告知他将不同他们一道回去。听到这个消息时,他们在黑暗中无声地抽泣。
对“智识”和“懂变通”的双重崇拜
潘文捷:知识者被常常批评“酸腐”“不懂变通”“没有眼力见儿”,都是因为没钱。有钱的知识分子哪怕真的“酸腐”“不懂变通”“没有眼力见儿”,也会被赞扬成有书卷气、坚持自我、不畏权威。真正的知识分子会有评价知识分子的内在标准——记者就是要写出好稿子,老师就是要传道授业解惑,学者就是要在本领域进行新的研究发现——可是这些内在的标准如今已经被别的标准取代了,这个标准就是金钱。
董子琪:我怎么觉得好像比有钱没钱要更微妙一点点……
徐鲁青:好真实,还有社会地位。有没有正经工作,有没有大学教职,说白了就是要进入体面阶层的门槛。要是符合了,爱看书是锦上添花,没符合,爱看书就是不踏实或酸腐。一个人把文学梦看得比金钱梦还重,就是“文艺病”“不负责任”,大概还是觉得世俗成功是追求文学梦的前提吧——一个人要是穷,有什么资格去“够”这些呢?
还有一种看似相反的叙事也颇有问题,常常出现在“底层书写”的营销里,类似于快递员写诗、农民工读海德格尔。底层“穿长衫”的动作被上等人凝视成某种感动奇观——你看,虽然他们是工人农民,却有志向去“够”这些更高级的精神追求,真是难能可贵啊。
这些写作者仅仅作为一个群体代表被讨论,但他们的书写有何独特的质感、书写方式和气质是什么样等问题却极少被认真对待。好像思考/知识/审美,天然就同体力活/底层/贫穷存在二元对立,当它们并置在一起,唤起的要么是嘲讽,要么是猎奇。
董子琪:如鲁青所说,现在一般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感动”,另一种是“批评感动”,两者都会湮没这首诗到底好不好的真实评判。
但比起怀疑“感动”,我更怀疑对“感动”的批评。如果说“感动”会引导人们肤浅地、多愁善感地消费这样的书写,那对感动的批评也会导致诗人和评论者都不敢出声,因为批评总会说这么写不全面、不真实、不能反映整个劳动群体的生活,这就无解了。一个常识是,好或不好不是因为任何身份。我最近在一个平台上看一位快递员写诗,有的句子还是不错的,但没有初看到余秀华时那么震撼。
徐鲁青:梦想和对美的向往、精神追求,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吗?在流水线工作,不代表一个只是螺丝钉。孔乙己研究“茴”字的写法、杀马特设计好看的发型,人们的嘲笑是不是觉得他们没资格呢?杀马特教主罗福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他说,审美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起点。很多人会从社会层面理解这句话,但对个体来说也是这样的。
尹清露:“酸腐”“不懂变通”的意思是不是说,这个人只知道理论知识、缺乏可操作的现实经验?以前实习公司的上司就是这种思路,他在评论作家这个职业时说:“别看他们很有情怀的样子,其实有名的作家都是社交牛逼症哦,很拎得清的。”言外之意还是只有世俗成功能确证知识的有效性——或者,世俗成功比智识更重要。想起两年前和朋友吃饭,席间一位活泼的ins网红女孩听说我有读博的打算,笑着说:怎么那么想不开的哦。
董子琪:她可能觉得读博就是“拎不清”了。
尹清露:这种对于“智识”和“懂变通(所以能成功)”的双重崇拜十分诡异,就像我们讨论过的“时髦知识分子穿搭”,它必须是有品位的洋装而不是落魄的长衫。“孔乙己”的原罪在于拥有过剩的知识但没能准确识别时代趋势,所以是不懂变通的,只能自认倒霉。然而,对学历重要性近年来一边被持续强调、又一边遭受贬值的事实却绝口不提,只在形势确实无法逆转时才跳出来指责大学生“酸腐”,实在是很不公平。而且就算“懂变通”了又怎么样呢,这么多年轻人的确开展了零工副业,但结果也可能是变成廉价劳动力,风险仍然在自己身上。
仅仅让年轻人降低就业期待就够了吗?
潘文捷:问题是,今天的我们处在文凭的通货膨胀中,获得高学位的人越来越多,工作岗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学历贬值了。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在《文凭社会 : 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中指出,学历贬值和“文凭凯恩斯主义”有关,也就是说,如果年轻人太早进入社会,政府就需要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这给政府带来很大的负担。如果高校扩招,越来越多的人有一层一层的文凭要拿,就给政府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缓冲时间。
人们对这种行为也并不反感,甚至乐于获得这些文凭。只不过拿到这些文凭之后,哦豁,贬值了。我上学的时候,很多老师都是当地中专毕业,年轻老师偶有师范大学毕业的本科生,现在,一些博士朋友都在商量着能去哪家中学教书呢。

[美] 兰德尔·柯林斯 著 刘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林子人:直白来说,“脱下孔乙己的长衫”就是说,年轻人们,在你们成长过程中曾憧憬过的、被家长老师耳提面命要为之努力的那种体面白领工作,已经越来越少了,你们需要降低就业期待。
文捷提到了《文凭社会》的作者柯林斯,《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一书收录了他的一篇文章《中产阶级工种的终结:再也无处逃逸》。柯林斯认为,科技对人工劳动的取代是资本主义长期的结构性弱点,而这种取代正在威胁并会加快中产阶级工种的终结。柯林斯指出,过去对中产阶级工种的保护要强于对体力劳动工种的保护,但现在已不是如此。
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一,新型就业机会的创造不如中产工种的自动化来得快,中产白领工作者恐将像工业革命后的手工业劳动者那样面临结构性失业;其二,互联网让更多的劳动者可以参与就业竞争,如果不需要移居到别的地方就能就业的话就更是如此,这意味着就业竞争的进一步加剧。
根据柯林斯的预测,现行经济体制的危机将由技术对中产阶级的取代机制引发。想到ChatGPT推出后引发的各大科技公司在AIGC不断加码,着实让人担忧。技术奇点是不是正在加速到来?而我们有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来应对?仅仅让年轻人降低就业期待就够了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 (ID:BooksAndFun),主持人:董子琪,编辑:黄月、尹清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