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阿祯,编辑:晏非,头图来自:电影《青春派》
“一张张成绩单被重重叠叠张贴在窗边,每当有一张新的覆盖上旧的,全班同学都会迅速围过去,大家的心情总是跟着排名起起伏伏。窗外不是风景,是对面墙上一条条鲜红的横幅。上面写着不外乎是类似‘两眼一睁开始竞争’这样打鸡血的句子。”
新闻报道中有关胡鑫宇生前学习生活的描述,勾起了林琳这段不算美好的回忆。不久前,她刚和朋友激烈地讨论过《衡水二中学生的发声,救救我们》一文。

高冉毕业五年后,生活在千里之外的林琳步入了高中生活。
作为一个因升学率突出而在全省乃至全国闻名的西南教育重镇,本地多所公、私立学校都是衡水模式的受益者。它们通过援引这种模式快速提高了升学率,从而成为了数一数二的名校。在名校效应下,除了本地学生,越来越多的外地生源开始聚拢,学位的竞争变得尤为激烈。
在此背景下,无论是学校的宣传还是家长的叮嘱,都在传递着一种强烈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对于能够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围城的学生来说,如果不能在此完成学业,就是一种对自我努力、家庭付出和优质教育的辜负。
“刻进脑海的是分数线。”林琳说,“所有考试都有班级、年级排名,每张排名表上都画着三条线——211线、一本线和本科线。当半数以上的同学都能上本科线乃至一本线时,211线就成为了大家争相瞄准的目标。这种单一的量化标准让人格外焦虑。”
为了挤出更多时间复习,外地生和部分本地生都成为了寄宿学校里的“留守儿童”。周末回家不再是一件必要的事情,外地同学大多到过节才会离校。父母也会劝说学生们尽量别回去,把赶路的时间用在学习上,“尽最大努力把分数稳在线内”。
除了频繁而密集的考试,让她更具象化感知到这种模式的东西是一本英文字帖——衡水体作文范文。
也许真正生活在衡水学校的“高冉们”也未曾想到过,在遥远的南方城市,会有人一遍遍模仿他们的笔迹,直到能够写出圆润得恰到好处的弧度。
无论是就读于衡水模式发源地的高冉,还是从完成了衡水模式本土化的私立中学毕业的林琳,在描述这种教育模式时都用上了“紧张”“量化”“寄宿”“刷题”“打鸡血”这几个词。在她们眼里,这些词汇就是衡水模式的“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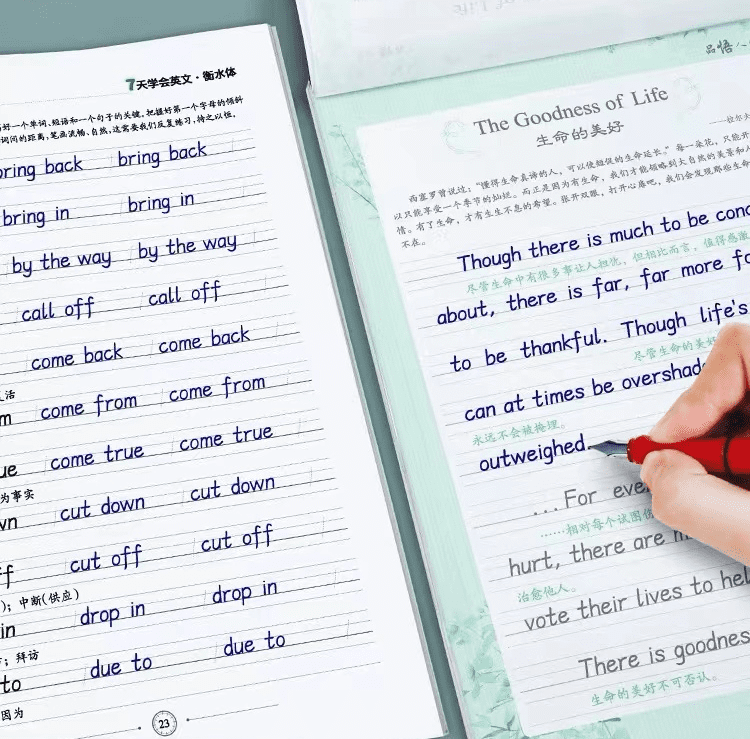
林琳的老师罗丹告诉新周刊记者:“衡水模式在教育方面最大的特点,就是集约化的人才培养机制。”
作为一名执教30余年的教师,罗丹见证了地方中学从通过引进衡水模式谋求初期生存,到逐渐跻身名校的全过程。
据他回忆,学校刚成立不久,就曾分批、分期把老师送到衡水中学考察,而他自己也曾两度被派往石家庄的某学校深入学习。那时,去衡水中学“取经”称得上是基础教育界的潮流,考察者络绎不绝。
他表示:“如果说好处,这种模式规范了学生的行为,让他们专注学习。但严格、量化的管理方式确实让本应充满丰富色彩的高中生活只剩下一种颜色。”
对于注重升学率的学校和老师来说,衡水模式是长时期内应对考试的最优解。通过将时间完全模块化的方式,让自控能力不足的学生集中所有精力来提升高考成绩。看似去个性化的模式,也是最具性价比的选择。
离开“衡水”,人是灵活的
反观学生,是否所有人都必须在这种模式下死守?
“我依靠幻想自己睡在桥洞里入眠。如果不按照既定的模式学习就考不上好大学,从而成为社会游民,我能想到最坏的结果就是睡桥洞。这个结果都能接受的话,其他困难于我而言就都不存在了。”何山用睡桥洞论来消解对未来的迷茫和焦虑。

在衡水模式严格的秩序下,什么时间该看什么科目都被一一规定。曾就读于某市一中的何山,就曾因不按模式化的步调复习被针对。并非优生的他,被要求一定得把不合群的学习习惯纠正过来。
在老师的反复暗示和强调下,何山产生了“想要争取自由,只能拿出成绩;学习模式不被包容,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的极端想法。
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下,何山开始每天熬夜学习。当同寝室的同学都入睡后,他还会借着寝室走廊微弱的灯光背书。
但随之而来的就是整夜失眠,白天精神恍惚。“在高三的紧张环境里,失眠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第二天无法集中精神学习。如此反复,就会陷入恶性循环。”
饱受折磨的他:决定自救,“首先,我必须活下去。”

一次放学回家途中,他路过一个黑暗、幽邃的地下通道,发现有流浪汉躺在里面。当天晚上,何山再次失眠时,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了自己未来和流浪汉们一起睡桥洞的生活场景。
长时间和成绩、老师及自尊心对抗的他,顿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解脱。桥洞,成为了他逃离期待和压力的“庇护所”。
当老师察觉到何山长期的消极后,便渐渐不再关注他。在以成绩来衡量价值的标准里,何山被贴上了“无可救药”的标签,这个分类无疑是可放弃的。
每条分数线上的世界就像容量有限的池子,但鱼也可以选择是否游进池中。何山选择向老师、家长甚至自己彻底证明已放弃入池,以此换回了解脱。

“现在我再回顾衡水模式里的经历,发现自己记住的并非苦闷而是希望。”她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从不曾被这种高度秩序化的模式束缚,“我看到课本上遥远的风土人情时,就觉得总有一天会亲临其中。外面的世界让我一直存有期望,我的思想在模式之外。”
在邱鲤大学毕业时,学校规定论文和自主拍摄短片都可以作为毕业设计。很多人选择了可以独立完成的论文,但她决定和别人合作拍摄短片。
“如果按照应试模式的惯性,我大概率会选择论文,就如过去独自做完一张张试卷一样。但我想做更多元的探索,所以最后选择了和同学合作,寻找故事、与人交流碰撞,最后在银幕上呈现出一段有主题的生活。这就是两种教育模式的差异在个体上的体现。”
升入高中的林琳,则因为课外兴趣和飘忽在分数线上下的成绩,成为了老师的重点关注对象。
衡水模式里,强调集中精力提升成绩的内核,是痛苦的根源。
“我恐惧考试,主要是害怕被看见。如果成绩在线上,我可以获得短时间的平静。如果在线下,就会被老师、家长轮番谈话。在他们的角度,是‘救’我,但我内心充满了抗拒。为什么成绩和兴趣之间,必须牺牲兴趣?”
最后林琳向任课老师罗丹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出于一种信任和寻求帮助的心理,试图寻找一个‘盟友’”。也正是这一次尝试,让林琳得以脱困。一句从老师口中说出的——“爱好,也可以成为安身立命的本事”,帮她破开了围城的高墙。
随后,罗丹一面约见了她的父母,一面和班主任沟通交流,最终说服了他们。考试结束后一轮轮要求她把全部精力放在学习上的谈话场景,终于没再出现过。
衡水模式里的优与忧
高冉在毕业后从事乡村教育方面的工作,对于城乡教育的差距感触颇深。在很多地区,衡水模式依旧是学校和学生能把控未来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在这种模式下,有希望在那个人生阶段借助外在环境,让自己考上名校的学生;也有完全顺从于模式,被师长推着走的普通人;还有不适应学习环境,想要挣脱束缚的学生。如果因为同情其中一方而完全否定另一方的想法和做法,也是一种不公。
对于学校坚持的衡水模式,一线教师同样感到矛盾。
一方面,大家看到了这种教育模式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有越来越多的学生提出了个性化思考和需求。
“当你不再用一把尺子去衡量所有学生,不带任何滤镜去看他们,就会发现每位学生都是优秀的个体。这样,老师就能够朝着保护和发扬不同学生的优势的方向努力。”
但要求老师抛开外在因素,单纯依照人本思想来开展工作,也绝非易事。
当冰冷的成绩数字在量化学生时,学校同样用升学率、尖子生人数等数字来量化老师。学生提出的个性化需求、家长殷切的期盼和学校的教育评价机制等,都让教师时时刻刻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教师在三方间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分裂感如影随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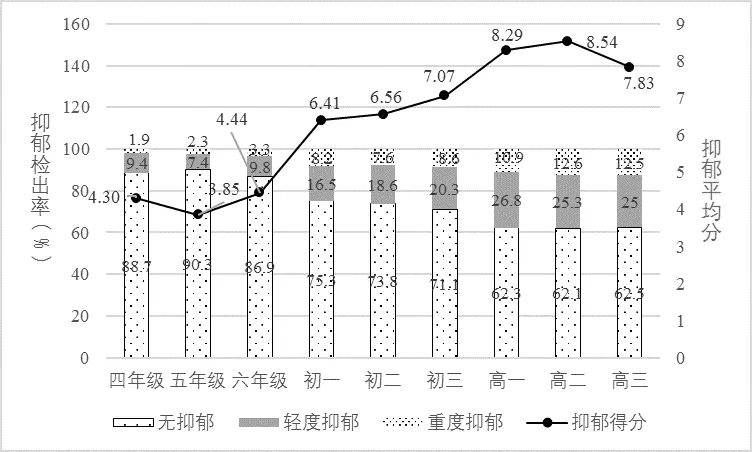
和任课教师一样有着强烈分裂感的,还有校内的心理老师。
迄今为止,大多数中学都配备了一位或多位心理老师,也有的学校专门设立了校心理咨询室,而这些心理老师就成了全校师生的心理健康卫士。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心理老师告诉本刊,比起学校庞大的师生群体,目前大部分中学配备的心理老师远远不够。
任职的短短两年内,她添加了近百位校内短程咨询来访者,以及表现出自杀倾向的“危机”学生。但学生对心理老师的倾诉,大多是有保留的。因为在他们潜意识里,老师和学校是“一伙”的。
“被学生删除拉黑是常事,还有的学生可能来找我几次就突然不来了。因为他们无法完全信任我,对我的教师身份有着强烈的戒备感。”
在她看来,被大多数家长和老师关注的厌学只是一种外在表现,原生家庭、学业压力、校园人际关系等,都可能成为学生产生心理问题的诱因。要想仅仅靠着断断续续的几次谈话,就让学生“恢复正常”,无异于痴人说梦。
工作第一年,她还会惦记着每个来找过她的学生。随着失去回音的学生越来越多,她内心的无力感也越来越强。
“校领导对心理老师的工作仍缺乏认知,让我们给任课老师做心理知识讲座,以便更好地筛查学生的心理状态。必要时,我们联合班主任开展工作,劝服家长将问题严重的学生接回家休养,或是送去医院精神科治疗。学校希望我是过滤的纱布,其实我只是在做筛子,而不想孩子休学的家长,则希望我的筛孔能再大点。”
“衡水模式,注定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在衡水模式这种高强度的学习生活中,学生们得挤出时间来照顾自己的心理健康。
每天晚上的10点到12点间,是大多数高中生结束晚自习后、入睡前难得的空档时间。校外的心理咨询师阿童,常在这期间密集接诊。
阿童观察到,这群来主动寻求心理帮助的孩子,往往不愿意家长在侧旁听。显然,他们不想让父母完全了解自己的真实情况。
“孩子害怕面对父母表现出的失望、自责。一些父母会将孩子生病归咎于自己的失职上,并且常常在孩子面前提起,无形中也越发加重了孩子的心理负担。”
一个饱受心理疾病折磨的孩子、一对咄咄逼人的父母和高压的教学模式,是阿童接诊以来最常见的组合。“有时候我帮他们打破了一层墙,很快他们又在心里筑起了另一座高墙。有些影响并不会立刻消失,更多时候,它们伴随一生。”

“衡水模式,注定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罗丹看来,现代基础教育一直在变化和发展。当下,许多青少年依旧被困在传统的衡水模式中,也有他们的父辈还未真正脱困的因素。
这些家长未必是衡水模式盲目的信徒,而是他们仍然生存在这种模式的惯性中。大多数00后、05后的父母在根据他们当年的认知选择教育模式,而非现在子女所处的新形势。与其说他们是在为孩子择校,不如说是在为自己择校。
但无论如何,教育的意义终究不是筑起高墙困住学生,而是帮助每个人寻找到属于个人的幸福生活。

今年春节,已经在外地成家立业的何山回到老家。当他再路过那条地下通道时,曾经的流浪汉消失不见,只有两大袋臭不可闻的垃圾。
何山和所有路人一样,快速掩鼻走过。离开之前,他仿佛又在垃圾堆里看到了那个必须自我放弃才能获得解脱的十八岁少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阿祯,编辑:晏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