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楞个想(ID:lenggexiang),文章摘编自《我们如何思考》,作者:西蒙布莱克本(Simon Blackburn,1944- ,英国哲学家、评论家。2011年以剑桥大学哲学教授身份退休,被誉为“英语世界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头图来自:《伪装者》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交谈的动物。无论是应对日常工作生活中的人际关系,还是处理亲密关系,我们都需要与他人沟通、表达观点、有时还需要说服他人。然而,我们往往发现,沟通并不总是那么有效,人际关系的困恼也由此而来。问题出在哪里?
一个可能的答案是,由于认识的局限,我们根本没有真正互相理解。这正是《我们如何思考》想要解决的问题。通过作者清晰有效的指引,你将学习到哲学逻辑严密的思考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辨析观点隐含的前提是不是有效,论据是不是可靠,清晰地表达自己,理解他人,从而使我们更加有效的交流。
真实的关切
很多实践思维本质上是技术性的。我们有一个目标,问题是如何满足这个目标。我们努力让手段适应于目的,而目的是预先给定的。目的被设定好了:我们想修理冰箱、养花或建桥。显然我们都或多或少擅长这些事情。没有一种“思考方式”能让我们全面地实现所有目标,正如知道如何修理冰箱的人未必知道如何养花或建桥。为了实现所欲求的目的,就要获得必要的技能,而这又要求理解有关系统,并知道要实施哪些更改以及如何实施。
一般认为,我们的目标是由欲望来决定的,因此目的—手段推理就在于有效地满足我们的欲望。这个说法往往是正确的,至少近乎正确。但是它可能也会令人误解。如果欲望被看作渴望某个目标的状态,那种让我们眼睛发光的东西,那么,当欲望不是恰当的措辞时,我们往往是因为具有特定的关切(concern)而行动。
在我想去航海的时候我却在剪草。为什么呢?真的不是因为我渴望剪草。也许我讨厌剪草,但剪草的时候到了,或者必须要剪草。我关切着剪草这件事。我着手采取有效的方法来完成这个目的。在这里,我有一个“关切”意味着我被“要剪草了”这个想法所鼓动。我可能认为剪草是我的职责。又或者我可能只是认为“剪草的时候到了”,而没有自觉地思考我作为房主的职责。尽管如此,我通常会意识到,别人家也需要剪草了,自己却没有动机来做这件事。因此,正是我作为房主的角色让我特别敏感于“我院子里的草需要剪了”这一想法,即使我并未自觉地思考这项职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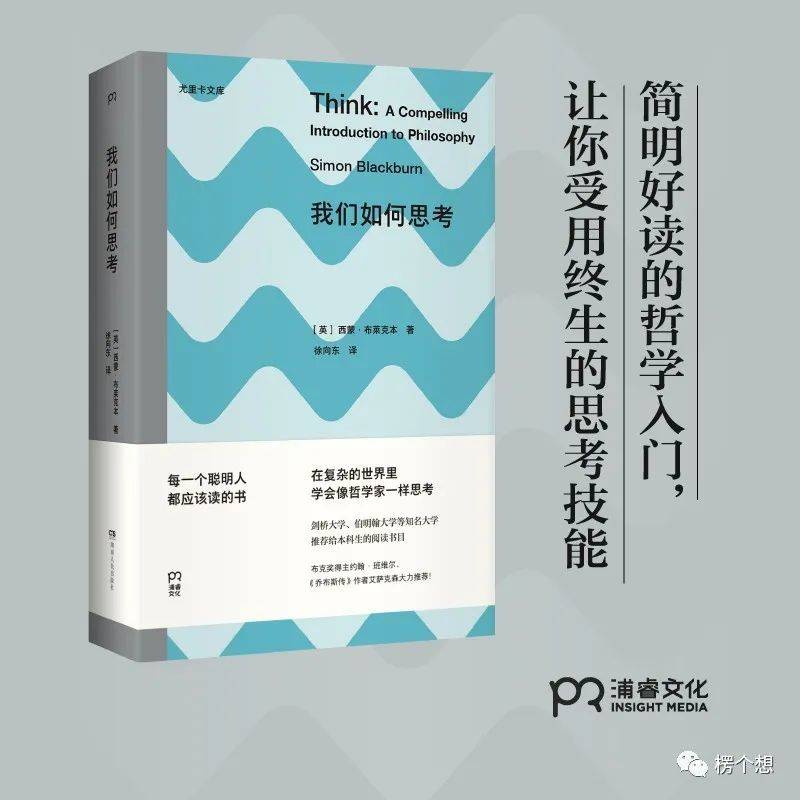
作者:西蒙布莱克本(英)
译者:徐向东
出于某种关切来行动和出于想做某事而行动之间有一个重要差别。当人们在相互争论的时候,这个差别有时会被刻意忽视。我们可以想象一段陷于困境的关系。安妮觉得自己因为某个缘故而必须离开伯蒂,也许是因为她对其他人负有一项责任,或是因为她的一项生活计划要求她移居。为了使二人之间的情绪升级,伯蒂可以坚持这样说: 如果安妮不想离开,那她就不会离开。“你肯定是想这么做,否则你就不会这么做。”这些都是伤人的话,因为这里提出的指责是,离开伯蒂的想法让安妮的眼睛发光,或者算得上是其行动方案的一个正面特点。这些说法可能毫无根据。安妮可能一想到要离开伯蒂就很沮丧。但是,就像剪草一样,必须这样做。
有人或许会说,当我们有一个关切的时候,也必定有某个我们所渴望的东西。假设我关切剪草却不想剪草,那么,如果我去剪草了,必定是因为我的确想要某个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我想获得内心的平静。这就引入了另一个非常危险的错误,即认为每当一个人有某个关切,她“实际上”渴望的是她自己的某种状态,比如内心的平静。特别是,心理学家历来喜欢按照一种张力的累积来思考欲望,行动者被驱使去做释放这种张力的事情。于是他们就容易认为,释放紧张才是欲望的真实目的。这也会带来伤害性的话语:“你其实根本不关心挨饿的孩子,你只是想让自己感觉良好。”一切行为都被诊断为在根本上是自私的,就好像始终是你自己的状态让你牵挂,其他的目标和目的都是一种掩饰。
这套想法(有时被称为“心理利己主义”)完全是错的。假设你想要食物。按照上一段话中的思路,我将你解释为想要解除自己想要食物的紧张。于是我就往你的肚子上揍了一拳,让你很不舒服,因此不再想要食物。我让你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吗?完全没有(即便你忘了那一拳曾让你很难受)。你想要的不是随随便便地解除紧张。你想要的是食物。同样,一个被性欲唤起的正常人想要的不是随随便便地解除那种欲望。一种溴化物可以让他解除那种欲望,但他不想要一种溴化物。他想要的是性行为。
考虑一下更为广泛的关切。假设我是一个黑手党老大,我觉得自己受到了路易吉的辱骂。我命令你——我的亲信——去除掉他。你转身离开,因为这项危险的任务而有点畏缩。但是,你反思了一下,我实际上想要的是解除路易吉的存在给我带来的紧张。你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除我的紧张:给我制造一个完全成功的幻觉,让我相信你已经干掉了路易吉。于是你就谋划了一些令人信服的假象,这就是你所做的事情了。你做了我想要的事吗?显然没有。我不想生活在错误地相信路易吉死了的愚人国之中(而且,请想象一下,要是我了解到这是你给我制造的假象,结果会怎样!),我想要你干掉路易吉。
我们或许会说,我们的一项关切就是,在我们的关切是否得到满足这件事上,不要受欺骗。
还有,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争吵和误解的一个核心原因,即交流往往就在于提出彼此的关切。如果一方有一个关切,而另一方将这个关切本身当作问题或障碍,当作一种要加以控制或治疗的东西,那么交流就无法达成。假设安妮关切自己的事业和自我发展,而在回应安妮的时候, 伯蒂不是想着如何鼓励她的事业和自我发展,而是想着如何压制她的关切。“亲爱的,别伤心了,只要我们出去吃顿晚餐 / 手牵手 / 要一个小孩……,你就不会为此发愁了。”
这种回应是不合适的,就像为了消除饥饿而往你的肚子上揍一拳一样不合适。但是,这种回应是不合适的这一事实大概不是很明显,至少对伯蒂来说不是很明显,而且,即使安妮离开了他,大概也是如此。按照我在第三章中的说法,我们可以这样说,伯蒂把安妮的关切“对象化”了,将它本身当作问题,而没有看到安妮的关切是什么。但在安妮看来,她的事业而非她的关切才是问题所在。只要伯蒂并不分享这个视角,他们就不会达成一致。
这一点在“治疗”的整个文化和产业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再讨论一两件事后,我会回到这个问题。
我说过,我们的一项关切是,不要在自己的关切是否得到满足这件事上受欺骗。有一个类似的要点:不要失去自己的关切,这也是我们往往具有(尽管并不总是具有)的一项关切。假设那个真想让路易吉死的黑帮老大被告知,只要他等上十年,他的这个愿望就会消失(有人或许会说,“最终一切都会好的”)。这就像告诉关切自己事业的伴侣,只要她等到自己有了一个小孩,那个关切就会减弱。但是,她不希望自己的关切减弱。我们可以这样说,那个黑帮老大将自己的欲望认定为复仇,而那位女士将自己的关切认定为她的事业。
现在确实有一些情形,在其中,我们并不认同自己的欲望和关切。我们可能希望自己尽可能摆脱那些欲望和关切。一个渴望吸烟的人也许不仅想要香烟,也想要尽量摆脱这种渴望。通过治疗或某种手术来消除这种心理状态也许会有效果。如果你发现自己“痴迷于”某人或某事,你可能最终会将你的痴迷看作你需要摆脱的东西,而且会尝试摆脱它。
把你已经确定为某种渴望或痴迷的欲望或关切进行分类,是一种让你远离它的方式,如果你开始将它对象化,那就意味着你在寻求某种策略来摆脱它。在上述例子中,那个关切自己事业的妻子最终可能会分享丈夫的认识(把她的事业抱负当作问题),并且更热情地尝试用其他消遣来摆脱那个抱负。但是她也有可能不这样做,而且,只要她真的这样做了,她可能就犯了一个错误,因为在她的自我认同中,与其他人导致她持有的想法相比,那个关切可能占据更加核心的地位。
这表明,我们自己认同的关切不同于我们能够对象化的关切,但这种差别并不总是很明显。我们可能不知道这种差别,直到我们试试看让自己摆脱某个关切是不是可能或合适,或者继续尝试去满足那个关切是不是可能或合适。
那么,关切是什么呢?我说过,有一个关切就是被某个想法所鼓动。事物的某个方面让我们产生动机,并成为对我们具有分量或者令我们在乎的一个方面(有趣的是,这个自然的比喻是一个重量或压力的比喻)。显然,当我们决定要做什么时,事物的某些方面就对我们有了分量。它们也可以通过影响我们的态度(例如欣赏或蔑视)或情感(例如希望或恐惧)而对我们具有分量。比如说,在阅读一部虚构作品时,我或许发现某个人物令我厌恶,这意味着作者描绘那个人物的方式对我产生了影响。英雄人物的美德让我有了欣赏之情,坏人的恶习则令我厌恶。
当我们有了关切的时候,我们所敏感的事情的那些方面就可以被描述为我们选择某事或者感受到某种态度或情感的理由。我剪草的理由是,草需要剪了。安妮离开伯蒂的理由是,她的事业要求她移居他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理由就是某种状况的这样一些方面:在慎思要做什么或如何感受某事时,它们对我们产生了影响。在一个稍微宽泛的意义上,我们的理由可能超出我们在慎思时的考虑。它们可以包括事实上对我们产生影响的方面,即使当时我们没有意识到(或只是不知不觉地意识到)究竟在发生什么。在这个更广泛的意义上,安妮离开伯蒂的理由有可能是他让她烦了,即使她自己当时不承认这一点。
在谈论让其他人产生动机的理由时,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需要注意。我们既可以用描述性的方式来谈论,也可以用规范性的方式来谈论。也就是说,我们既可以描述让他们产生动机的某种状况究竟如何,也可以说让他们产生关切的东西实际上是不是一个理由,这样就表达了我们对那个关切的认同或拒斥。记住这个区分很重要。
在说安妮没有理由离开伯蒂时,我们可能是在对安妮的心理提出一个(很可能是错误的)评价:她行事冲动,既没有经过仔细考虑,也不存在她当时试图满足的任何欲望或关切。或者,我们更有可能是在拒斥那些实际上激发安妮行动的关切:她离开伯蒂,是因为她想追求自己的芭蕾舞事业;但在当时的情况下,那是一种不明事理的抱负,或是一种不应对她产生影响的东西。当我们用规范性的方式谈论时, 我们应该指明,我们是在用“应当”和“好的”之类的措辞做什么。但有时候,我们不说“她没有好的理由”,而是说“她根本就没有理由”,而这种说法可能会被误解。
表面上看,我们的关切可以是一堆杂乱无章的东西。敌人的死亡、对某种事业的追求、草的状况、亲朋好友的福祉等,这些关切都很常见,就像很多其他的关切一样,比如这些事实:你做出了一个承诺,某人曾对你做了什么,你是某人的伴侣或是一位医生或律师。就像存在着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民族一样,人们有着不同的关切。而且,我们已经拒斥了一种尝试,即将这种多样性归结为某种统一性。这种尝试将我们看作总是只关心自己的精神状态(从某个关切所导致的紧张中解脱出来)的人。然而,这是一个错误,而且严重损害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区别——我们所认同的关切和我们实际上能够摆脱并且希望摆脱的关切的区别。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楞个想(ID:lenggexiang),文章摘编自《我们如何思考》,作者:西蒙布莱克本(Simon Blackburn,1944- ,英国哲学家、评论家。2011年以剑桥大学哲学教授身份退休,被誉为“英语世界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