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4日,91岁的法国神父马塔索利(Roger Matassoli)被发现死在了位于瓦兹省Agnetz小镇的家中。
一个十字架深深卡在了他的喉咙里,尸检报告如是说:
腹部、颅骨和面部受到猛烈打击,死亡原因为窒息。

随后,一个名叫亚历山大(Alexandre)的19岁年轻人被捕,当时他开着马塔索利神父的车子出逃,精神错乱,直接被送进了医院。
当他走上法庭接受审判的时候,却表示: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
剧情的反转在一个月后。
2019年12月5日,嫌疑人亚历山大的父亲在接受采访时声称:
我儿子,甚至是我小时候,都受到过马塔索利神父的性侵和虐待,是他毁掉了我的家。
就酱,一场谋杀案牵扯出了数桩耻辱痛苦的儿童性侵案,马塔索利事件就此而生。

受欢迎的马塔索利神父
曾经的马塔索利在一个叫做Saint-André-Farivillers的小村子里当神父。
彼时,他40岁左右,总是穿着合身的衬衫,剪裁得体的裤子,坚持日常锻炼,有着小麦色的肌肤,看起来很英俊。
不仅如此,他还用拉丁语做弥撒,语速很快,也很有趣,有无数人都争先恐后地来参加早间礼拜,每个星期五,他都被邀请吃午饭,孩子们也会不遗余力地讨好他。在小村子里,他是名人,甚至成为了一个嫉妒的对象。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才让长久以来的罪恶被深深地掩埋了。
他说:上帝同意了。
而马塔索利神父被杀,恰好为这场罪恶打开了一个缺口,受害者们开始有勇气从沉默中走出,说出自己的遭遇。
55岁的米歇尔(Michel)就是其中之一。
今年3月13日,米歇尔参加了瓦兹教区组织的一个会议,天主教会内的性暴力受害者们都出席了会议,在那里,他第一次讲出了那些不堪回忆的过去。

他与马塔索利神父的最初记忆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中期,那时他只有8岁,是唱诗班里的一名小男孩。
每周,他都会去Saint-André-Farivillers的长老会,自1967年开始,马塔索利神父就一直住在那。
第一年,什么也没发生。他和唱诗班里的其他四五个小伙伴经常去长老会的花园里玩,那里有好吃的,也有孩子们都爱的小火车。
第二年,年近50岁的马塔索利神父开始每周三单独接待他。在那个时候,米歇尔的父母压根就没觉得有什么不对,他们乐于将自己的孩子交给神父,非常高兴能找到一位能够向他们灌输良好礼仪和基督教慈善的家庭教师,谁会产生怀疑?
起初的单独相处不过是学习射击步枪或修剪教区的草坪,但铺垫之后总有下一次。

马塔索利神父让米歇尔和他一起洗了澡,然后带他去了一楼的一个房间,四处都是黑暗。
这就是开始的那一刻,他们躺在床上,抚摸,穿透。
之后,这样的痛苦每周都会有一次,从米歇尔9岁直到14岁,整整持续了5年。
对于这一切,马塔索利神父威胁米歇尔不准告诉任何人,并解释:
我获得了耶稣的同意,是他把我送到地球。

至于为什么只持续到了14岁,马塔索利神父表示:
你变得太老了……

从那之后,米歇尔解脱了,但他受到的创伤却丝毫未减,一直到神父去世,他都不敢说自己遭遇了什么:
我很惭愧,害怕不被相信,或者说,我只是相信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我的错。他以为他是上帝,但他是魔鬼的化身。

但即便不提这场长达五年的破碎记忆,米歇尔成年之后的生活也依旧受到了影响。
他一直尽可能避开马塔索利神父,但结婚和施洗总是要去教堂的,难免会碰面。在马塔索利神父的办公室里,神父就很卑劣地当着米歇尔的妻子问:
你没告诉你老婆什么吗?
此后,米歇尔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变得咄咄逼人,然后把自己孤立起来,不再和他们一起去度假。
他甚至在自己一个女儿8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她,后来那个孩子被诊断出患有双相情感障碍。

其实,在米歇尔被性侵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以为自己是唯一被选中的那个,所以他羞愧内疚沉默,直到马塔索利神父被杀,他才敢痛哭着揭露出这些秘密。
而这一刻,他用了近40年的时间。
他说:我是上帝的化身。
雅克(Jacques)是另一位受害者。
同Michel一样,他从6岁开始遭遇马塔索利神父的性侵,结束这一切的时候也是14岁,但相比之下,雅克的命运更凄惨,因为他再也等不到正义了。
雅克的故事,还是他的姐姐柯莱特讲出来的。
1967年,科莱特还只有8岁。她是十三口之家中的第八个孩子,父母是农民,既谦虚又虔诚。每天晚上睡觉前,一家人都会围坐在壁炉旁,面朝十字架祈祷。
彼时,她是羡慕家里的男孩子的。因为他们可以去长老会做园艺、除草或砍柴,作为奖励,他们也有权享用可口可乐或橙子酒,这是当时现代社会的最高境界。
他们有时也会登上被称为“天堂之钥”的阁楼,有时也能去参加童子军营地,在帐篷下展示男子气概和信仰。

每个人都爱马塔索利神父,没有人会起疑心。
初次怀疑是在1984年初,那时柯莱特已经28岁了。
他们一家人路过市政垃圾场时,科莱特的一位堂兄在垃圾堆中发现了一张奇怪的照片:
马塔索利神父未着寸缕,一只脚搁在椅子上,大方地拍着果照。

当时科莱特的父亲很是惊讶,他直接去长老院寻求解释,马塔索利神父尴尬的笑着:
那是我服兵役时的一个玩笑,仅此而已。
柯莱特把这一幕记在心里,然后跟她的兄弟们聊了起来,她想:没准儿他们知道些什么内幕,毕竟以前他们经常去长老会玩。

果然,已经20岁的保罗(Paul)最先松了口,他讲述了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马塔索利神父是如何鼓励他们和他一起洗澡的。
听到这话,已经22岁,性格腼腆矜持的雅克,突然泪流满面:
在我6岁到14岁的年岁里,神父不仅仅跟我一起洗澡,他还会抚摸我,用各种暗示的姿势给我拍照,有时在长老会,有时在童子军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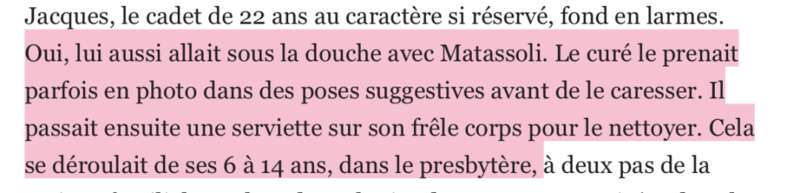
更明目张胆的是,有时在周五的午餐时间里,神父还会把我抱在腿上,趁没人注意的时候,把手伸进我的内裤。
他说,他是上帝的化身。
我曾经把这件事告诉一个朋友,但他一直大笑,无论如何,父母永远不会相信我。

柯莱特立刻就察觉出了不对劲,她打算和她的姐姐奥迪尔(Odile)一起上诉。
但是,在当时的小村子里,马塔索利神父太有影响力了。奥迪尔思虑再三,开车开了25公里,在另外一个小镇的公共电话亭里给巴黎司法警察局打电话。
然而,Saint-André-Farivillers村依赖于Creil市的司法警察进行调查,这场投诉没有任何进展,没有邻里调查,没有传票,柯莱特和奥迪尔在那一刻确信:神父受到当局的信任,他甚至有时间删除有危害的照片。
几个月后,调查被撤销,马塔索利神父屹立不倒:
只有上帝才能审判我。

神父的逍遥法外,让雅克寸步难行。
他独自住在巴黎郊区的一间简陋公寓里,在邮政分拣中心找到了一份工作。但他的精神状态不断恶化,变得粗暴,变得无法发表连贯的言论。
几天后,27岁的他又一次发疯,偷了一辆自行车,然后掉进了塞纳河,溺水身亡。

柯莱特说:
如果雅克的生活没有被这些恋童癖行为摧毁,他今天可能还活着。
是谁纵容了神父?
其实,漫长几十年的时间里,马塔索利神父不可能滴水不漏。
1986年,当时36岁的让-保罗(Jean-Paul)就写信给Beauvais教区,讲述他在9岁时曾遭到马塔索里神父侵犯的事。
彼时的副主教乔治·德布罗意(Georges de Broglie)回应:
我们收到了你的来信,它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几天后,我们将更详细地回应您报告的事实。
但几个月过去了,石沉大海。
直到2000年底,托马佐主教(Guy Thomazeau)才有空写个回复:
在我在这个部门工作的六年里,我没有收到任何马塔索利神父的受害者或任何有关他的邮件。我不记得有人对我发表过任何关于他的评论。

看吧,就好像教会必须在信徒面前受到保护一样,没有人会揭穿这一切。
不过,几十年里线索还是有的。
村里的几位居民曾看到神父带着孩子在他家赤身裸体地走来走去;也看到年轻人在做园艺的时候除了简单的围裙,其他的什么也没穿;
1990年代,一位当地猎人在路上看见神父把一只手放在方向盘上,另一只手放在孩子的内裤里。
可他们都选择了沉默,在这片人人皆知的土地上,让这一切变成了谣言。

所幸,2018年,让-保罗终于决定采取法律行动,要求梵蒂冈展开规范调查。
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里,就找到了五名受害者,检察官也最终传唤了马塔索利神父。
本以为就算时间流逝,正义也一定会来。
但命运就是如此,法律没来,马塔索利神父的死期却先来了。
忽然想起去年10月,法国独立委员会公布的那份爆炸性的、指向明确的天主教教会内部儿童性侵报告:

70多年来,天主教会内部,大约有2900至3200名恋童癖者,他们是神父、神职人员;遭受虐待的受害者至少有10000人。
而这只是最低程度的估算。
哎,这世间的罪恶啊,总是深不见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