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Tatler的朋友们(ID:Tatler-info),作者:王火火,视觉:riscal,题图来自:《情诗》
2020年,青年导演王晓振凭借电影作品《情诗》获得了第14届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剧情长片和最佳演员两项大奖。2022年,王晓振在家里十点睡,四点起,每天负责接送女儿王小说上下学,给妻子周青做饭。他没有拍摄新片的计划。
作为2021年Gen.T上榜人,王晓振似乎没有那么“成功”,拿奖对他来说是个顺势动作,而非某种状态,一旦离开这个身份远一些,他好像又变回了那个拧巴的、较真的、迷茫的、虚弱的普通人。但另一方面,他在艺术表达上所表现出的苛刻的自我要求和极致的自我审视,又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几乎所有创作者心底的难堪与纠结,欲望和理想。
他认真、笃定、不容置疑地说:“我拍东西最主要的,确实是要过自己这一关。”这时的不拍,就是在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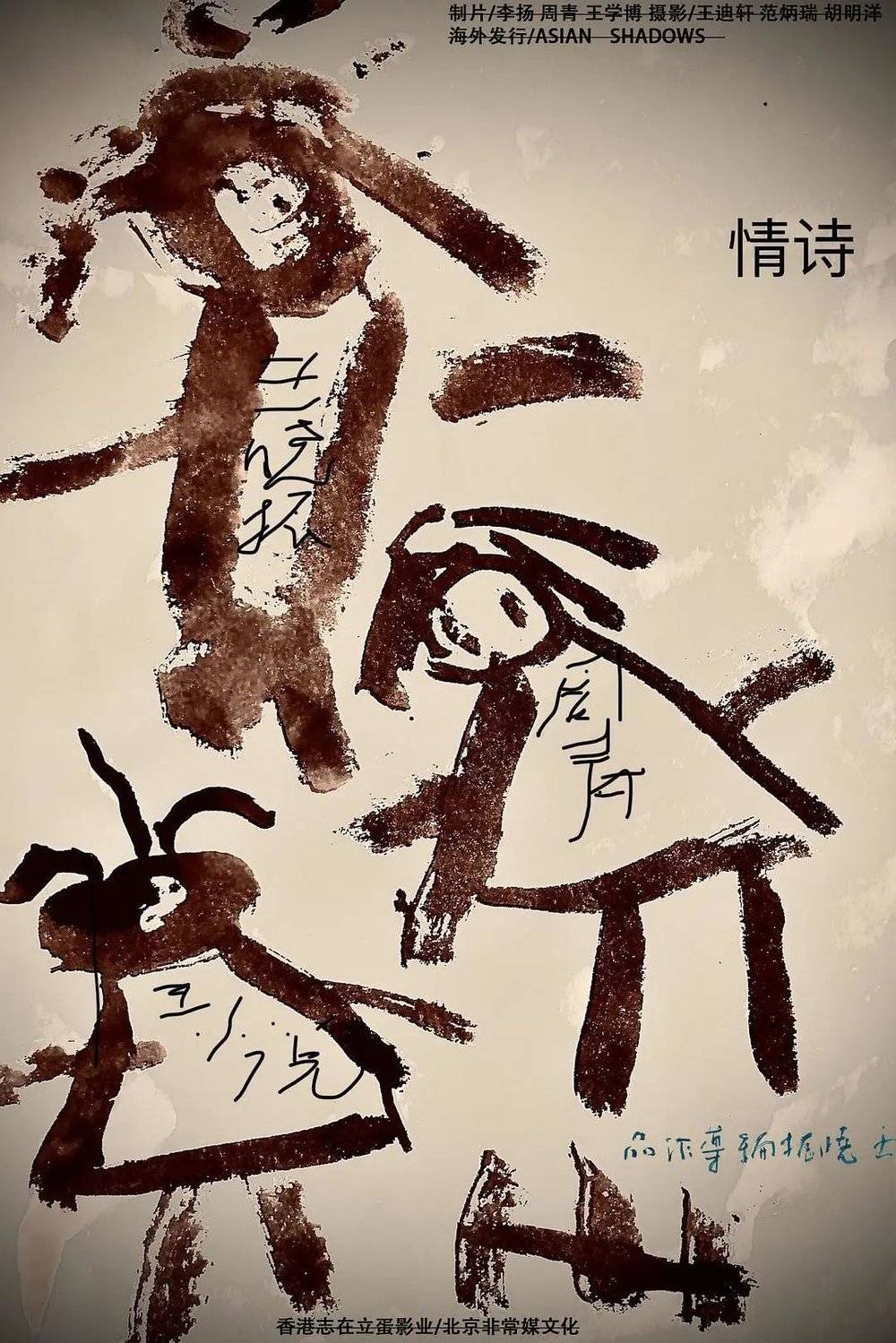
用他自己的话说,拍电影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你很虚弱嘛,就需要别人来认可你。”《情诗》获奖后,王晓振产生了一股巨大的拍电影的热情,打算一年拍十部,“我自己积累了好多剧本,而且也不拍那种特别复杂的电影,所以感觉十部也能拍。”
很快,资方找到了他,约他出去聊聊。有人提出要王晓振翻拍《情诗》,他们可以出钱,这次可以找一些“更专业更知名的演员”,呈现出更精致的效果。王晓振敏锐地理解了话里的意思:“要么,他们想要靠这个项目赚钱;要么,他们想让有些演员通过演这样一部作品,提升自己的形象和品牌。”
王晓振干脆地拒绝了,“他们的需求很简单,但我没有兴趣去做。对我来说,无非就是多赚一点钱,但我又不是特别需要。这都不是我的需求。”
另外一拨人带着商业项目找到他,问他是否有兴趣,本以为王晓振会回避,但他并不排斥。甚至还专门研究过商业片,对于拍商业电影这件事,王晓振觉得自己应该也可以做。然而,在仔细看过项目后王晓振还是拒绝了。“我感觉那几个项目并不太好——作为商业项目也并不太好,其实好多商业影片,我觉得是很好的。”

趁着热情的余温,王晓振确实拍了部片子。但拍着拍着,他发现自己要考虑很多事情,作为一名导演,他很难避免自己不去想“拍出来后别人会怎么看”这件事。“比如说我想拍一个商业一点的,我就会想,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让大众喜欢,怎么样才能够调动观众;如果我要拍一个所谓作者一点的,我就会考虑,这个东西在当今艺术电影的格局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会受到什么样的认可……我动不动就会想这些。”
想来想去,较真的王晓振干脆不拍了。他停止了手头的拍摄工作,给自己的要求是“尽量少输出垃圾”。

王晓振喜欢看很多类型的电影。但从电影制作的角度来说,他还是更喜欢简单一些的导演风格。当然了,对于那些制作复杂、调度精准、门槛较高的电影,他“很佩服”,也认可那样的电影会成为经典,但另一方面,他始终相信有一部人如他自己,是将电影看作一种表达媒介的。在探索媒介的过程中,会尽量选择用极简的方式来成全更多的表达内容。
“像侯麦啊,洪尚秀啊,他们的电影都是很‘简单的’类型,你单拿出他某一部作品,很难说一定在电影史上怎么样,而且整个的制作方式也没有说一定把电影特别当回事,但同时,从这样一个角度,他又是很当回事的。”
他口中的导演洪尚秀确实足够特别与简单,与王晓振的拍摄风格非常相近,“几乎不做任何准备就开拍电影”,通常只准备两件事:“地点和演员”。他们创作剧本的逻辑也几乎一样,除了必要的梗概,剧本细节可以说没有。
此刻的2022年的王晓振,手头没有在拍任何一部片子,但是有好多框架,有的可能是一个关系结构,有的甚至只是一个场景,“今天写一个,明天就会想另一个”,有的刚写完,立刻便没有兴趣去丰富了,快感迅速消失。他称自己并不是一个习惯创作完整剧本的人,“我如果写得特别详细的话,基本上就不会去拍了,写完了,那个热情也过去了。”而在没有热情之后依然去拍,“就会显得特别功利”,只是把一个写好的东西“复制”出来,他很难说服自己。
他希望自己能够像喜爱的那些导演一样,在拍电影的时候,明显让人感到“他在享受拍摄”。而他杂念太多,“我如果真的很爱做这个事情本身,像这些想法,可能根本不会有。”
类似的情况可以在宫崎骏的电影里找到。《魔女宅急便》里,魔女琪琪遇到了画家欧思娜,欧思娜每天看看树林、晒晒太阳、喝喝茶,却没有在画了。琪琪不解,而欧思娜对她说:“当我再也画不下去的时候,就什么也不画,出门散步、喝茶,做别的事或什么也不做。总有一天,会再有画的想法。”
2021:高光时刻
当初,《情诗》在FIRST电影展放映后,豆瓣开分8.1,备受瞩目;但现在你去豆瓣搜索,会看到分数变成了6.9。周青说王晓振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而这样新锐的导演,和他创作出的作品,从来就不缺争议。
大众对他的质疑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消费情感、形式大于内容、男性侵犯视角以及剥削妻子。王晓振对于这些“罪名”的看法始终没变过,所谓的道德伦理问题“不过是程度的问题”。他问:“你作为创作者,你没有消费过身边的人的感情吗?你没有从自身取材吗?不可能。我们只能创作出我们熟悉的故事。”他曾在过去的某次访问里坦言:“我在通过骂我自己,骂所有人。”
至于男性侵犯视角和PUA妻子,他的看法是,你这样理解,也没毛病。因为那只是电影里的表演。生活中他和周青的模式是吵吵闹闹的轻松型,没有谁剥削谁,更不存在谁PUA谁。“我们俩有点像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推上去,掉下来,推上去,掉下来——但是反正一直在往上推,我觉得这也挺好的。”
2021年,他没有拍摄自己的片子,却给快手拍了一个商业短片。他意外地享受那次合作。因为快手的工作人员没有给他提任何要求,反而他会去为对方考虑是否安全,是否利于传播等问题。最后片子出来,对方很满意,王晓振对整个过程也颇为乐在其中。但是到了自己的片子里,他就会觉得“刻意”,“不自由”,“拍不下去”。
没有人知道他是从哪一刻开始转变的,变得小心翼翼,充满警惕。青年导演在获奖后的意气风发只短暂地在王晓振身上出现了片刻,就被他脑子里的自我诘问覆盖了。在我们的一再追问下,他说是因为一些私事,改变了自己的认知,让自己“不得不谦卑起来”。一直被诟病将隐私和感情进行消费的他,反而说道:“这个还是不要讲了吧,谢谢。”

或许很多人会认为,作品得奖是王晓振的高光时刻。但他自我感觉最好的一次体验发生在去年,他在朋友的片子里饰演一个读研的大学生,导演一声action,所有的镜头与焦点立刻全部对着他。原本他以为,自己这种不自信的人,面对镜头一定会慌不择路,但真实情况是自己很快就沉浸到了表演状态里。
这与拍摄自己导演的片子完全不同,“我演自己的片子,更多的都是在考虑导演的事情,很难全身心地去演一个角色。但当时你能感觉到,你在彻头彻尾地体验表演这个事情。”他喜欢这种“全身心”。
在那个场景里,王晓振感到纯粹的自由与热爱。他不需要做任何繁杂的统筹,也不必去承担电影的解释权,他只是一个男大学生,对女朋友讲着对白,“就像歌手在唱歌,运动员在打球,你好像在控制着节奏。你在享受拍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Tatler的朋友们(ID:Tatler-info),作者:王火火,视觉:risc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