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让一部分青年先X起来(ID:youthsX),作者:谢家铭,口述:艾明,头图来自:《伯德小姐》截图
“他们理解不了是他们的错误。我会投入到我自己的哲学世界中,去抚平生活带给我的种种创伤。”这其实就是一种自我孤立。哲学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城堡。在这里,我有我自己的规则,并免于外人的打扰。
我大学毕业于某985院校的会计专业,这个专业是父亲当时给我选的,可能是觉得实践性强,今后比较容易就业。
但我对会计一点兴趣也没有。在大学,我经常逃课,然后在寝室打游戏或者去图书馆看书,考试也只在前几天突击复习一下,保证不挂科就行。这种强烈的厌学情绪在初三就有了苗头,并且经过高中一直伴随着我。
我清楚自己一直处于一种抑郁的病态之中,对周围的一切失去了兴趣,做每一件事情都提不起精神,必须要鼓足绝对的勇气才能做好。每天,我的身体都很疲惫,只想躺在床上睡觉。
但是我没有选择药物治疗。我对这个世界感到失望,仿佛自己没有任何的出路。而唯一能够让我短暂喘息的地方,便是哲学世界。哲学对于我来说,就像是面对这个功利现实世界的一条退路,是自己逃向世外桃源的一个出口。
而哲学也正给予了我想要的。一些激进的哲学家认为整个世界都是病态的,在此之上生存的人也是受压抑的、甚至是神经质的。所以抑郁的人反而是正常的。渐渐地,我明白这一切通过药物是无法解决的,因为我自己没办法改变这一切。
这是应试教育对我带来的无法修复的创伤。
矗立山巅的精神胜利
在我的家乡河北,应试教育相当严重。封闭化管理的校园,每天都被明确地切割为各条块,然后按照要求严格执行,没有任何自己的时间。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像是流水线上的工人,完成每一道被要求做的试题,成为一个真正的提线木偶。
哪怕像我这样应试能力比较强的,学习对我来说也成为了一种沉重的负担。我中考那年是全县的第一名,并且进入了市重点中学的尖子生班。但我从来没有感受到快乐,每天都是在强迫自己学习。
可是我并没有能够逃离这一切的办法,像我这一类的小镇青年,只有应试教育这一条竞争渠道。除了做题之外,再也没有实现社会上升的途径了,我无法选择。
我就这么挨着。
由于我的性格比较内向,也找不到朋友去倾诉,只能把这一切憋在心里。而只有在真正看书的时候,我才能缓一口气,觉得这才是我想要的。
我所在的高中不允许带课外书,哪怕像哲学这类严肃读物。但是学校会给我们每个人发放一个学习用的平板电脑。我只能趁每月放假的时候,用平板电脑拍一些书上的内容,然后在课间偷偷摸摸地看上两眼。

读这些书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像是傲然立在山峰之巅,有一种慷慨激昂的感觉。觉得面前的一切都是小问题,自己都可以承受下来。这其实就是一种自我欺骗,但至少支撑我走过了高中这三年。
当然,这些哲学书都相当的艰深和晦涩。而这恰恰能给我带来某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读下来会有一种自我满足和成就感。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被消磨,自己得以从做题之中抽身,从而缓解压力。
用哲学黑话来自我安慰
上大学之后,我接触哲学的途径变多了。当然主要还是自学。我在读书过程中时常会眉头紧锁,有时候也会大声朗读出来。因为只用眼睛看的话,时间一长眼神就飘了。读书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没有规划,兴起了就随手翻上几页,让心情平静下来。
有时我也会写日记。这些日记中充满了哲学的黑话,看起来好像是一些深奥的哲思。但是我明白这只是一种自我安慰的病态。我用一系列高超的黑话串联起的内容,只是为了表明这个世界是错误的。而我有我自己的一套玩法,哪怕只是自娱自乐,但至少能让我感到放松。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教马哲的老师。在他的课上我试图去接近他的思想,并且经常主动发言。但是这门课却并不被其他同学所认可,在期末评教的时候,他的评分极低,只有我一个人给了满分。我感到相当失望,发现哲学并不是能为所有人理解的。
曾经我满心好奇地加入了学校的哲学社团,希望在这里能够自由交流,并且找到对象去倾诉。但是后来我发现这里其实也充满了强制性。他们有一套自己的认知和规范,并不宽容,我依然没有办法展现真实的自己。
所以,我的大学,依然像高中一样,痛苦没能减少。世界仍然是功利的,充满着强迫。
扮演正常人去讨好世界
在大三的时候,我决定要考研,考哲学的研究生。但是这只是我逃避的借口,用以向父母交代我对未来的打算。
虽然我希望通过深造,经受专业的学术训练,但是我对考试的抵触并没有缓解。我认为学习哲学应该是一个自由的状态,但考研却又把人逼到一个有标准答案的模式之中,不得不去面对那个唯一正确的权威,这让我每次拿起教科书都想睡觉。
所以我并没有真正备考。在第一次考研的时候,我甚至连政治科目的考场都没有去。最后的成绩也自然惨不忍睹。但是我为了给父母一个说法,自己用PS把成绩改到刚过线的水平,让他们觉得我确实是在努力,只不过运气不好罢了。
我在父母面前一直努力表现出一个努力认真、人畜无害的正常人形象。我不会把我病态的一面展现给他们。我身边曾经有朋友也因为受不了应试教育的折磨而被诊断为精神病。我心疼他的遭遇,并且不想像他一样被送进精神病院。我一直在克制我自己,甚至我有时还会享受自己扮演正常人的感觉。
所以,我始终觉得有一种特别强的分裂感。在人前,我是一个谨小慎微、兢兢业业的演员,不得不去讨好这个世界。但是当我独处的时候,我才能回到真实的自我,真正拥有学习哲学的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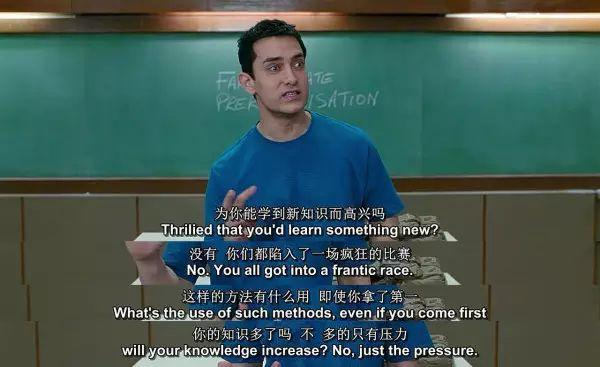
在去年毕业之后,我就一直在家准备二战。名义上是备考,甚至有时候把自己关在房间内大声读书,但我根本没在学习的状态上。我觉得自己真的病得太重了,需要时间休息。而考研正好能成为我逃避的借口。通过表面上的努力,让我的精神真正放松出来。
凭借我的演技,我始终努力地维护自己正常人的形象,并成功瞒过了我的父母。其实,我的这些创伤性的经历,或许在我童年时就已经有了踪影。从小面对来自父母的期待,化作沉重的负担。
面对来自父母的绑架
我的父母都是老师,对我的教育属于“鸡娃”。虽然没有那么硬核,但凡事都会操心,为我规划好人生方向。从小我父母就特别看重成绩,曾经我母亲因为我作业抄写不工整而直接撕掉我的作业本,并让我重做。这些经历都对我造成了特别大的阴影。
虽然我很委屈,但是我不敢反抗,我感觉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逼迫着我去这么做。渐渐地,我就学会了有意识的伪装。在稍小的时候,我还会认为这确实是我自己做错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不再认同这样的教育方式。久而久之,分裂感便产生了。
我的妹妹也同样如此。她期末考试成绩哪怕九十多分,都会被批评,被质问为什么没有考更高。我当时站在旁边,其实特别心疼。但我没办法上前阻止。因为我知道这样做没有用。

这种来自外在的规训已经深深地内化了。小时候我曾经因为去过一次网吧,而认为自己罪大恶极。“我为什么这么小就可以违背父母的意志?做出了只有坏孩子才会做出的事情?”从那天开始,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生活在一种恐慌之中,每天放学回来都害怕自己去网吧的事情败露而提心吊胆。
但是我从不会给我母亲解释,让他们去理解我。我和他们的关系有些疏远,因为我有我自己的哲学。“既然在阅读哲学的过程中很开心,那为什么要费劲去解释吗?让他们接受我这个努力去装模作样的自己就足够了,我不需要他们认识一个真实的我。”
免于外人打扰的安全城堡
二战没能成功上岸后,我开始找工作。可能也是在家休息了大半年,我觉得自己终于将内心积攒的郁气倒腾出来了,自己的心态也捋顺了许多。我逐渐从过去只是作为分数性的存在走了出来,并且有了明显的改变。
虽然我对会计没有兴趣,但毕竟是专业对口,至少能做起来,不是零基础。选择来到北京,一方面是父亲想让我来大城市看一看,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北京相对而言更加宽容。
在家乡,一个人读哲学会被看做是很奇怪的事情;但是在北京,大家可能会当作是一个正常的爱好,甚至被认可。被承认对我而言非常重要,因为之前身边总有人将我称作是异类。
我听到这些评价自然会有情绪,但我也只是憋着,不理会他们。“他们理解不了是他们的错误。我会投入到我自己的哲学世界中,去抚平生活带给我的种种创伤。”这其实就是一种自我孤立。哲学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城堡。在这里,我有我自己的规则,并免于外人的打扰。
只有当进入这里时,我才觉得自己是安全的。

我大概用了一周多的时间就找到了工作,海投了上百家企业,最终进入面试的有5家。其中大多数都是和科技制造相关的,并且我个人更倾向于国企。最终,我成功入职。除了包食宿、八小时工作制、班车接送外,我更看重的是单位氛围。我喜欢那种踏实沉稳,同事之间简单随和的风格。
我对未来没有明确的职业规划,只想先安顿好自己的生活,然后慢慢来。“我就想着在别人面前像那么回事就行,凑活着能过。然后剩下的时间,自己能够静下心来读读书。”
在我入职后的一天晚上,我和母亲在电话中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当然只是因为一件特别无足轻重的小事。我认为,自己既然已经找到工作,可以养活自己之后,就不再需要依靠父母。我无法再继续忍受,和父母的关系自然也需要重新调整。
打开城堡,大方地生活
在我接触到的所有哲学家中,我目前比较喜欢的是齐泽克,包括拉康。他们在精神分析领域都有很独到的分析。齐泽克认为,这个世界本身就是充满创伤的,不和谐的,我们要做的就是直面它。
这让我获取了一种走入现实世界的勇气。
作为小镇青年,从小生活在四角天空,也没有丰富的经历,我知道我这种心境的出现也是必然,没有解决的办法,只能顽强地去支撑。
但是齐泽克告诉我,我应该开诚布公地去承受,而不是被动地挨着。越逃避反而越痛苦。曾经我比较喜欢海德格尔,也想诗意地去栖居。但后来我觉得这仍然是一种对现实的掩盖,我不应该继续把自己关在这座城堡里。
我要去感受我的痛苦。
*根据受访人口述整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让一部分青年先X起来(ID:youthsX),作者:谢家铭,口述:艾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