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赵钊、潘文捷,编辑:黄月,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在我们的惯常印象中,死亡是吵闹的,伴随着唢呐哭丧甚至歌舞仪式。然而在历史学家看来,作为一种社会事件的死亡是缄默的,这种失声一方面体现在传统文化对死亡叙述的限制,另一方面则是社会下层群体在丧葬管理和死亡记述上的历史性空白。
死亡既被认为是伟大的平等,无人可以逃脱这一终局,同时却又是社会巨大不平等的彰显和认证。《红楼梦》中详细记述了秦可卿的“七七作事”,仪式包含哭灵、哭俑、供祭三个部分,葬礼更为隆重,包括告别、送葬、入葬等仪式,送葬队伍规模宏大,王孙公子不可枚举。中国传统文化对殡葬礼仪有着严苛的规范,周礼中就已经明确了“贵贱有仪,上下有等”的丧葬仪式。
在西方文学中,作家在描述死亡之悲痛的同时,也揭示着社会不公的残忍一面。如果说《魂断威尼斯》中托马斯·曼描述的只是个体所面临的瘟疫死亡威胁,那么加缪在《鼠疫》中则进一步刻画了瘟疫来袭后奥兰城中群体性的恐慌无助。许多平民悄无声息逝去,许多人甚至没有体面下葬的权利。在19世纪的巴黎,停尸房一度成为被随意观赏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公共景观。一些因机器爆炸、火车事故、煤烟窒息而意外死亡的工人,因无人认领而最终成为太平间“死无人知”的展览品。
死亡不仅事关个体,更关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如何界定概念、规则和仪式,它们构成对待死者的个人信念和处置标准。著名的上海城市史专家、法国历史学家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的《镰刀与城市:以上海为例的死亡社会史研究》日前中文版问世,为我们构建了从晚清到20世纪60年代上海的一部死亡社会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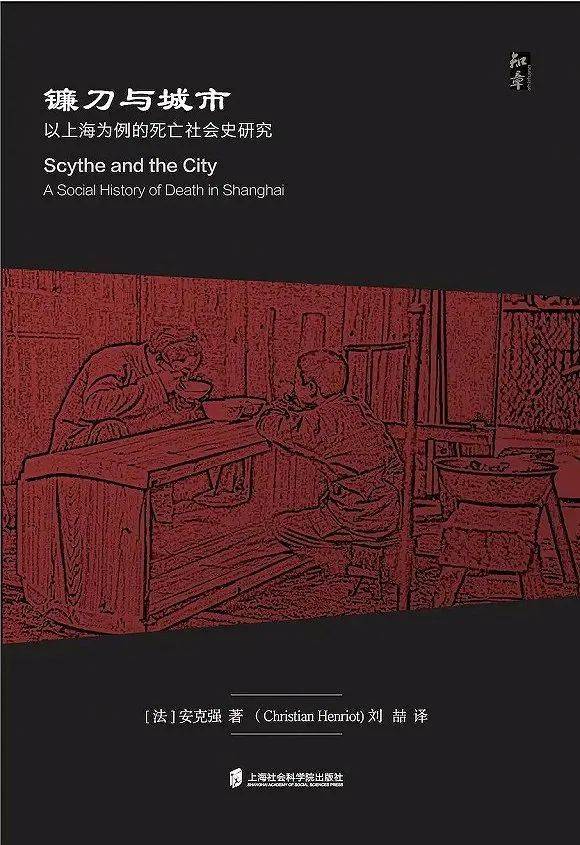
在作者看来,“死亡”不仅仅是情感上的感知与表达,更提供了一个思考社会如何构建生命观念、自我组织并应对死亡的切口。19世纪中叶上开埠之前,上海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商业港口,许多旅居者在此贸易,同乡组织遍地开花。上海经历了人口的集聚与增长,死亡人口也随之不断攀升。在这座城市的历史上,人的死亡和丧葬仪式经历了怎样的混乱和变迁?殡葬业如何反映了这里巨大的贫富差异和种族鸿沟?解放后的人民政府是如何管理和革新上海的死亡规范的?从公墓到火葬,这些推动死亡世俗化的方式又为何遭遇重重阻力?让我们跟随安克强的研究和分析,走进这段关于死亡的历史之中。
死亡:近代上海人口的消失
中国社会建立在集体关系网络中,个体永远是宗族、职业、地区性关系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看重落叶归根,十分忌讳“死无葬身之所”。19世纪50到60年代,数万人来到上海,广阔的农村与城市接壤的区域容纳了不断膨胀的人口。
晚清和民国时期,孤苦伶仃的穷人死后很可能被遗弃在上海的街头、后巷等公共空间,成为城市中“看不见的死亡”——这些死亡事件不仅“看不见”,也“听不见”。穷人和儿童在街头的死亡在公共话语中被合理化,有时被阶级话语包装,例如《上海泰晤士报》曾采访善会人员,后者认为乞丐死亡多半源于沉迷鸦片,不值得多加记述。法国心态史学者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在《死亡文化史》中将这种阶级区隔称为“沉默的分量”,并指出没有比死更不平等的事情了,他翻阅了含括12-17世纪墓地情况的《盖尼埃尔全书》,发现其中只有圣人权贵,那些通过教区登记簿记录进入坟墓的穷人直到近代才被“看见”。

被遗弃在田野上的棺材
近代上海究竟有多少人“死无人知”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数据。安克强认为,整个民国时代的上海就像一个巨大的葬礼,吞噬了成千上万的生命。这种高死亡率来自于战争、犯罪和糟糕的居住卫生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死因是传染性疾病,包括肺结核、天花和霍乱,后来疫苗接种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这种情况。直到1937年战争爆发,时任政府才不得不去处理已经严重侵占公共空间的死亡问题。
疾病是死亡原因的表象,真正折磨中国人的是那些“贫穷病”,贫穷给疾病的扩散创造了条件,也使治疗遥不可及——尽管上海有当时中国最好的医疗基础设施。上海居民不仅因为种族不同与西方的旅居者有所区分,在信仰和居住模式上也有所区别,这些西式的标准成为当时都市空间的准入要求,因此中国人常常无法在市政公墓内安葬。

1940年代的上海棺材店
来华的外国人也遵照着等级差序格局。墓地的使用清晰地反映了租界里的种族和社会界线。能否使用墓地也取决于国籍、种族、宗教和财富的尊卑等级,那些下等群体和穷人,只能依赖他人的善心或自己有限的财力解决丧葬事宜,锡克教徒、越南人和犹太难民等群体就可能面临难以落葬或缺少明确机构安葬的窘境。墓地割裂了城市空间和社会景观,成为争夺权利之所。
丧葬:商业化加剧阶级分化
随着近代上海需要处理更多的死亡问题,殡葬作为一种新商业形式应运而生。如果说死亡创造了生产葬礼用品和服务的完整系统,那么这种等级与价格又建立在另一种社会等级——“财富”——之上。
中国传统的丧葬仪式并不低调,民众仰视精心安排的出殡,视其为社会成就的标志。穷人无法支付商业化的殡葬服务,只能交由公会或善会来处理后事。大批外乡移民带着成家立业的憧憬来带光鲜的城市,艰难讨生活,只有付得起丧葬费用的幸运者能够落叶归根,其余只能埋在慈善机构或公会公墓里。能否被体面殓葬,成为不同群体的区隔形式之一。

南京路上一位高级官员的出殡队伍
精英群体为了让亡者享受更好的阴间生活,会通过仪式为其提供丰富的物质补偿,甚至比生前实际享有的更丰富;平民只能带着敬畏来观看精英群体精心策划的宏大的仪式和表演,逝者的财富与地位也通过仪式得以物化呈现。
20世纪初,追悼会作为新形式的悼念服务而兴起,死亡的纪念仪式进一步进入公共讨论空间,把私人领域的追思活动引入另一个层面,意味着有名望的人在死后能继续享受大众的瞻仰。不论是丧礼还是葬礼,其性质、规模和公众关注程度基本如实反映了逝者的社会和经济等级。以近代上海规模最大的出殡仪式之一、清末商人盛宣怀的葬礼为例:作为前清大臣,他在清朝崩溃后仍然享受了准国葬待遇,出殡仪式吸收西方军事典礼的形式,吸引了众多旁观者在道路两旁观看,这种混合性质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社会和政治的不确定状态,这次葬礼也成为了中国第一部纪录片《盛宣怀大出丧》所展示的题材。另一次盛大的葬礼则属于民国著名影星阮玲玉,约10万人围观了她的出殡仪式。

出殡队伍中的大型纸质人偶
在精英名流声势浩大的葬礼仪式之外,更多的普通百姓只能举办一场简易的葬礼,葬礼上通常有一位撒纸钱者、一座简单的置放灵位的亭帐、几位乐手、抬棺者和哭丧的人。城市工人的收入水平无法匹配最基本的商业殡葬安排,穷人和低收入群体只能将遗体交给公会或善会负责。同乡会组织为这些“无声的死亡”提供葬礼服务时所扮演的角色,无论是廉价的棺材、墓地,还是运回祖籍地,都是建立在一种权力剥夺上。随着殡葬商业化的发展,传统的习俗被改造和重新诠释成一种现代性和商业化的变相折射,富人和穷人在葬礼上的差距也进一步加深。
改革:规范公墓,推行火葬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更多人负担得起殡葬服务。为了将殡葬行业的商业服务转变为公共服务,政府首先选择与私人公司、同乡会和善会合作,建立统筹组织逐渐接管前者的殡葬运作,因此殡葬公司的数量迅速减少,公会和同乡会被从慈善机构中分离出来,并最终废除。在上海,除了有着悠久历史的普善山庄和同仁辅元堂外,其他慈善团体被禁止从事与死亡有关的事务。至20世纪50年代,被保留下来的极少数商业殡仪公司也最终全部被纳入政府管理。

上海郊区的送葬队伍
除了对殡葬商业化的改造,政府意识到,是土地紧张导致了墓地价格上涨,致使许多平民无法支付安葬费用,造成了上海周边未下葬棺材的堆砌。上海公墓因为长久以来和慈善坟地联系在一起,被认为是穷人遗体随意丢弃的地方,那些遗体没有名字也没有尊严。随着人口增长和人口构成日益复杂,租界亟待规范对死亡和殡葬的管理,上海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决心将墓地由私人管理变成受政策和规定管控。把公墓作为主要下葬地成为了一个重要转折,这意味着不再使用单人坟墓置于一块单独土地上的传统葬法。公墓的推行,成功地满足了中国人两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即死留全尸和葬于生前定居的地方。当然,选择不同公墓及墓地位置,依然体现着社会等级的差异。
另一个解决方法是推行火葬。一方面,火葬是一种节约土地花费、保障公共卫生并有效降低葬礼成本的选择;另一方面,战争造成的大量非正常死亡给城市管理留下巨大挑战,穷人及儿童的高死亡率对上海工部局的清尸工作造成极大负担,在这种情况下,火葬是高效而便宜的上好选择。
然而现实状况是,除了自上而下的政策,强大的民间传统仍把控着大多数人对丧葬仪式和形式的选择。1927年后,国民政府吸收西方新的公民文化并推动死亡世俗化,但在中国的城市中,推动葬礼习俗转变的动力很有限,火葬在上海的推行就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唐宋时期因为佛教传播,火葬曾盛行一时,但是明清以降为了推行符合统治要求的意识观念和法律设置,土葬依然是主要丧葬形式,火葬一度被视作异端,入土为安的死亡观不断巩固。在90年代经典电影《孝子贤孙伺候着》中,赵丽蓉扮演的母亲因为害怕死后被儿子火化,联合亲戚假扮死亡考验儿子,引发了一出荒诞闹剧。在近年的First青年电影展中,一部名为《吉日安葬》的短片也展现了村长老王因不想把老伴火葬而想到偷尸代替火化的故事。火葬与土葬的争议在当下依存在于中国许多地区,但不可否认的是,火葬为人们提供了另外的丧葬选择,已有越来越多人开始选择这种丧葬方式。

《孝子贤孙伺候着》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英国巴斯大学死亡与社会中心近期在研究中提出,在英国,越来越多的人拒绝正式的葬礼而选择直接火葬。仪式的简化并不意味着亲人没有得到认真的纪念,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于一个家庭或社区来说,举行葬礼并非最重要之事,更加珍贵的是围绕死者分享共同记忆的群体能够聚集在一起,死者可以选择符合自己价值观和信仰的丧葬形式作为进入另一个世界的启始。
文中图片(除注明外)皆来自《镰刀与城市》一书,经出版社授权使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赵钊、潘文捷,编辑:黄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