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没人会想过,成绩的好坏能和堕胎有关。
最近,佛罗里达州的两名法官做出了令人满头问号的判决,
他们拒绝让一名17岁的高中女生堕胎,理由是——“她的GPA太低了”。


根据法庭文件,这个化名叫简·多伊(Jane Doe,等同于“匿名女子”)的女生与男友恋爱后,意外怀孕,因为年纪太轻,经济来源不稳定,他们决定把孩子打掉。
多伊是未成年人,包括佛罗里达州在内的美国38个州规定,想要堕胎必须告知父母。其中21个州还规定,堕胎前必须得到至少一名家长的许可。

在佛州,多伊不需要提供家长的许可书,但必须提供知情书,可是她的父母都是保守派人士,他们知道后肯定要求她生下来。
她的父亲曾经说过,除非被强奸,不然堕胎是不可接受的。
在询问了男友的母亲后,她发现唯一能合法堕胎的手段,就是启动一个叫“司法绕行”(Judicial Bypass)的法律程序。

这个法律允许未成年人在不告知父母的情况下自行堕胎,只要她们能说服法官,自己足够成熟理智,能承担堕胎带来的后果。
就这样,多伊走上了希尔斯伯勒县的巡回法庭,她说自己询问了男友的母亲(她恰好是护士)以及其他大人,已经了解堕胎的风险。
虽然诊所拒绝给她提供堕胎相关的信息,但她上网查了资料,把诊所官网的堕胎注意事项都看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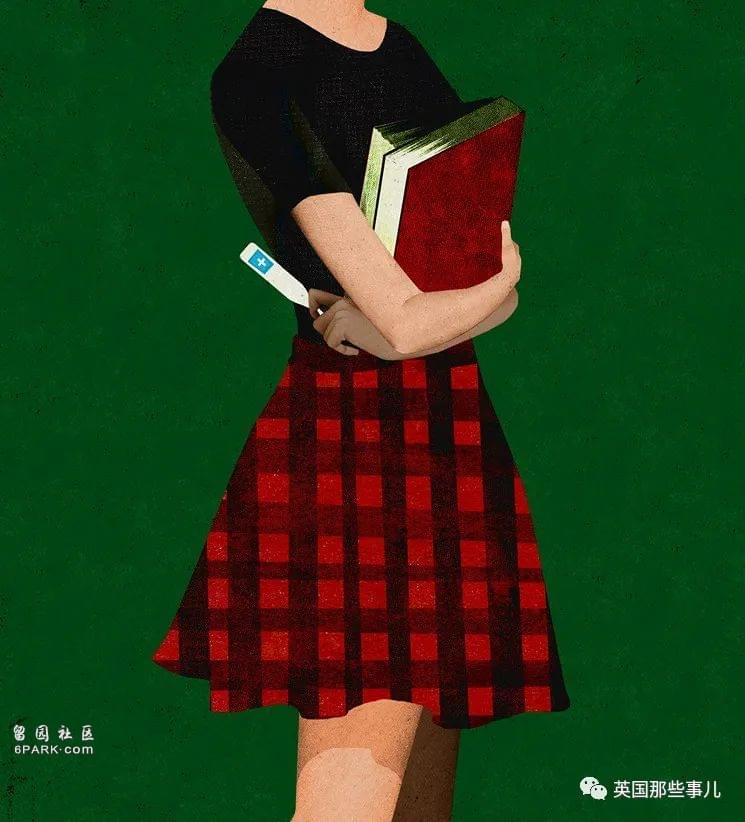
最后,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她还年轻,她梦想高中毕业后进入军队,之后去上大学,进入护理行业。她真的不能在17岁就有孩子。
法官点点头,然后拒绝了她的堕胎申请。
这个名叫贾里德·史密斯(Jared Smith)的法官在判决书中说,多伊缺乏这项法律所需的“成熟度”,因为她不关心家里的弟弟妹妹,情感比较幼稚。
 (贾里德·史密斯)
(贾里德·史密斯)他特别质疑多伊的成绩,因为她之前说她在学校的成绩是B级,但目前的GPA是2.0。
“很显然,B级的成绩不等于2.0的GPA,她的证词要么是缺乏智力,要么是缺乏诚实。这两者都不能得出她成熟的结论。”
为了证明多伊不够成熟,史密斯法官还写道,“多伊从来没有承担过任何经济责任,她甚至连自己的手机话费账单都没有”。

因为这几个理由,史密斯法官拒绝让多伊堕胎。
收到判决结果后,多伊马上上诉,由佛罗里达州第二区上诉法院的三名法官审理这个案子。
在详细看了所有法律文件后,法官达瑞·卡萨努瓦(Darryl Casanueva)和苏珊·罗斯坦-尤阿基姆(Susan Rothstein-Youakim)驳回了初审判决,允许多伊堕胎。
 (达瑞·卡萨努瓦)
(达瑞·卡萨努瓦)判决书中写道:“一般来讲,我们把C级视为高中生平均能达到的成绩,所以B级、C级都不算差。至于描述不一致,可能是由于律师问的问题不同导致的。……总之,没有证据能证明,她的智力低于平均水平。”
两名法官反驳史密斯说她没有经济责任,说多伊在过去一年每周工作20小时,已经存了1600美元,有两张信用卡,除了话费是妈妈付外,其他基本都是自己花钱。
至于不照顾弟弟妹妹,这就更好笑了,因为“她根本没有弟弟妹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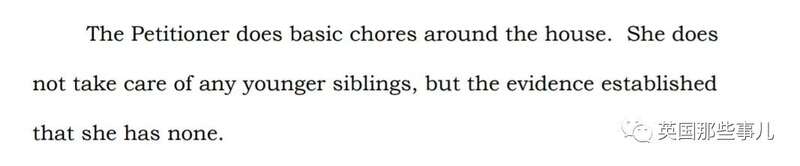
唯一不同意堕胎结果的,是法官约翰·斯塔格尔(John Stargel),他把史密斯的论点又搬出来说了一遍,还特别指出多伊的申请书中存在语法错误,拼写老板名字的时候也拼错了。
“虽然这可能是因为她出庭太紧张,但是法院也应该考虑其他可能性。”
 (约翰·斯塔格尔)
(约翰·斯塔格尔)无论他怎么嚷嚷,2:1的结果已经出来,多伊可以放心去堕胎了。
这起案子被媒体曝光后,美国网民又好气又好笑,什么时候法院靠看GPA来决定堕胎权利了?
另一个显而易见、且让此事显得荒谬的是,既然女孩因为“不够成熟”、“智力不高”、“没有经济来源”不被允许堕胎,那么幼稚、愚蠢、贫穷的女孩当妈妈,反而是好事了?

女性杂志《Jezebel》讽刺地写道:“意外怀孕的青少年太不成熟,因此不能堕胎。可矛盾的是,这意味着一个不成熟的人应当被迫生育,成为母亲。既然史密斯法官如此关心多伊的成绩,我很怀疑强制分娩带来的压力能提高她的GPA。”
这种不合逻辑的情况,其实从美国最高法院给“司法绕行”定标准时就埋下了。
最高法院规定,怀孕的未成年女孩要么证明她足够成熟,要么证明堕胎符合她的最佳利益,这样才能被批准堕胎。

如果严格地按照“符合最佳利益”来判决,其实女孩们几乎都会获胜,但实际的审判中,法官有很大的操作空间,把重心放在“证明足够成熟”上。
如果这是变性、整容手术,评判未成年人的成熟度还是有些道理的,
可这是堕胎手术,对未成年人来说这属于“自救”,有什么评判成熟度的必要呢?

每年,美国有数千女孩想通过“司法绕行”堕胎,她们要么是孤儿,要么是非法移民的孩子,要么是父母坐牢,更多的是父母因为信仰反对堕胎。

“司法绕行“是她们让人生重回正轨的救命稻草,可很多人被法官以奇怪的理由拒绝,只因为法官自己的反堕胎立场。
在多伊的案子中,反对她的斯塔格尔法官被人发现是州议员凯莉·斯塔格尔(Kelli Stargel)的丈夫。凯莉是佛州反堕胎运动的先锋,她之前提出过一项法案,禁止怀孕15周后所有的堕胎,对强奸和乱伦也没有例外。
 (凯莉·斯塔格尔)
(凯莉·斯塔格尔)斯塔格尔法官自己也是“父母参与法”的编写者,这项法律要求父母需要知道未成年女儿堕胎。
《琼斯母亲》的记者调查40多个案子中,有法官因为少女没有和牧师讨论堕胎决定,拒绝她的申请。
2008年,佛州法官劳尔·帕罗米诺(Raul Palomino)拒绝一个17岁的女生申请,说如果她的天主教父母知道她悄悄堕胎,该多么痛苦。

2013年,内布拉斯加州法院拒绝让16岁女孩堕胎,原因是她经济上依赖养父母,没有工作,也无法养活自己。
虽然父母不在后,女孩靠自己一人养活了弟弟妹妹,证明法院说得不对。法院希望一个“无法养活自己”的女孩成为母亲,也更是奇怪。
那个女孩上诉后,内布拉斯加州最高法院维持了原判,她没有多伊那么幸运。

2000年,阿拉巴马州法院驳回一个少女的堕胎请求,哪怕她说得很明白,父亲说过如果她敢怀孕回家,他会杀了她。
最让人崩溃的案子,发生在阿拉巴马州一个17岁女孩的身上。
女孩照着法律的最高标准,让自己成为一个完美的堕胎申请人,事先询问过6名成人关于堕胎的注意事项,其中包括两名护士、一名卫生部官员,和一名堕胎女性。

在法庭上,她详细描述了堕胎手术会是怎么样的,说出所有手术器械的名字,还展示自己有两项奖学金和优异的成绩单。
法官问她是否做好堕胎的心理准备,她回答:“是的,我对这个决定非常坚定”。
但法官还是拒绝了她的堕胎申请,理由是她没有和做堕胎手术的医生谈过。
虽然女孩说过,医生拒绝与她交流,因为诊所规定员工不能在法庭听证会之前与未成年少女接触。

“我是一个母亲,在我看来,这些人只对一件事感兴趣,那就是得到这位年轻女士的钱。”法官如此说道。法庭文件没提法官的名字。
“这是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士,她有着光明的未来,不应该陷入屠夫的圈套。”
女孩提起上诉,但是上诉法院支持法官的决定,这个优秀、理性又聪明的女孩只能去生孩子了。

很多法院在推高“司法绕行”的门槛。拉斐特学院的法学教授海伦娜·西尔弗斯坦(Helena Silverstein)调查了三个州后发现,超过一半的法院不知道,或者假装不知道存在“司法绕行”程序。
许多法院职员,包括一名法官,告诉她没有“司法绕行”这个东西,有的人直接把她介绍到反堕胎机构,让她去听那里的讲座。
 (海伦娜·西尔弗斯坦)
(海伦娜·西尔弗斯坦)有法院说,就算上头有这个法律,他们本地也不执行。
2012年3月,密歇根大学的学生复制了海伦娜的实验,打电话询问佛州的67个县法院。
结果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法院都不能,或不愿意向来电者提供“司法绕行”的信息。
有的保守派官员还要让事情变得更难。
2014年春天,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人通过一项法律,允许地区检察官盘问想要堕胎的少女,原本简单的听证会变得更像审判犯人。

法官还能长时间休会,不断拖延听证会的时间,让少女错过堕胎期(超过一定时限后,堕胎是违法的)。
法官还能把少女的身份透露给“任何需要知道的人”,包括她的父母。虽然,美国最高法院 要求保密。
更狠的是,这项法律允许法官给胎儿指派律师,让律师在庭上争夺胎儿的生命权。

胎儿雇律师,听上去有点荒唐,但在阿拉巴马州通过这项法律之前,已经有一些法官这么干了。
从90年代到2000年初,阿州法官沃尔特·安德森(Walter Anderson)任命当地的反堕胎领袖当胎儿的律师,在几十场“司法绕行”听证会上代表胎儿利益。
1999年,新闻讲述了胎儿律师朱利安·麦克菲利普斯(Julian McPhillips)如何盘问一个17岁女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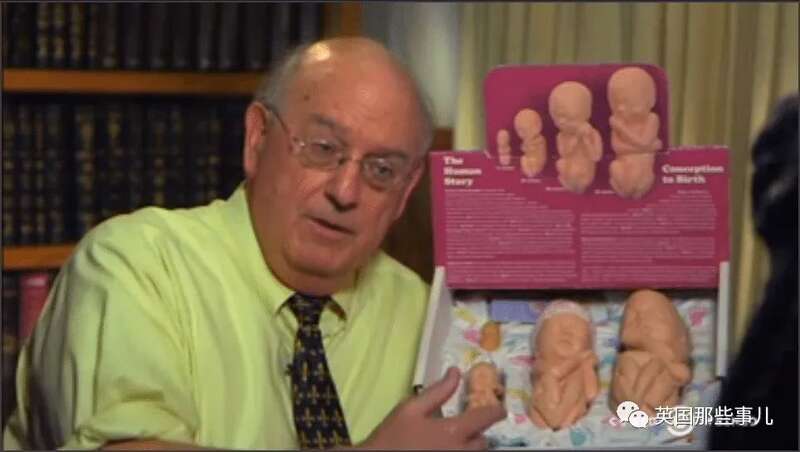 (朱利安·麦克菲利普斯)
(朱利安·麦克菲利普斯)女孩说她不敢生孩子,因为她的父亲经常用枪威胁对她感兴趣的男生,如果他知道自己怀孕,可能会杀了男朋友。
朱利安咆哮着孩子也想活下来,他甚至给那个7周大的胎儿取了名字,叫它“阿什丽宝宝”。
安德森法官权衡后,认为少女足够成熟,能够自己决定堕胎。朱利安代表胎儿发起上诉,幸好,上诉法院裁定胎儿没有上诉权,“阿什丽宝宝”就此消失。

不过,这起案子激发阿州的另外两名法官效仿,在所有“司法绕行”听证会上安排胎儿律师。
佛州也有法官这么做过,在一个16岁女孩的听证会上,律师说他的当事人是“婴儿特蕾莎”。
包括美国公民自由联盟、Jane's Due Process等组织,都在抗议法官的任意裁决,抗议胎儿律师。Jane's Due Process更是让几名从未批准过堕胎申请的法官,移出听证名单。

但不少媒体表示,从2010年起,要求父母知情的38个州中,有11个州的“司法绕行”程序变得更加严格。
佛罗里达州、堪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等5个州提高了听证会上证据的标准,
俄亥俄州和俄克拉荷马州限制少女只能在特定地方发起申请,
亚利桑那州和阿肯色州通过法律,禁止律师和法院工作人员以外的人帮助少女“司法绕行”……

随着美国的反堕胎势力越来越强大,女孩们注定要打一场煎熬的战斗。
她们可以准备得很完美,从全A成绩单到充沛的手术知识都有,
但想要挑错,法官永远都能挑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