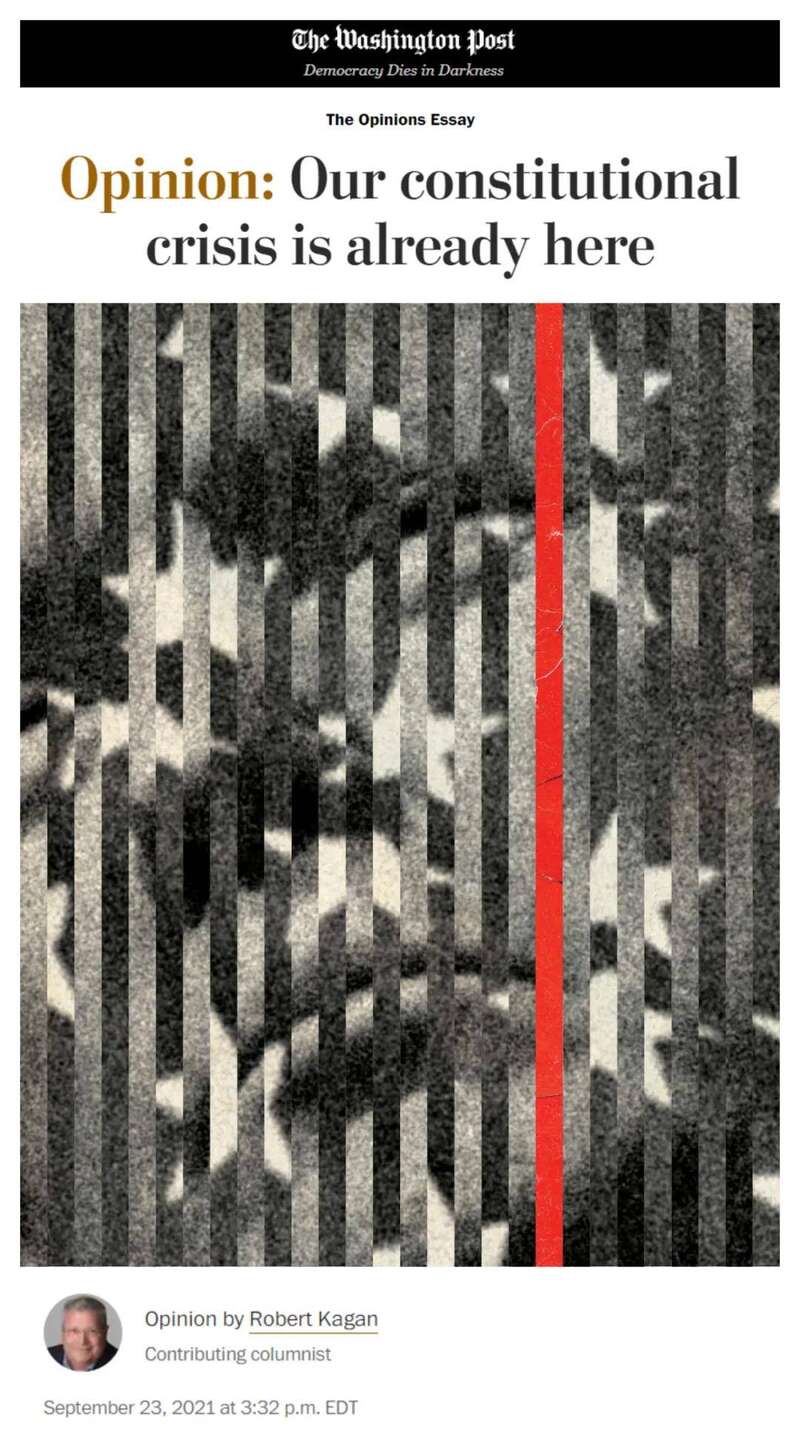
“难道在美国已无美德可言了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的处境将十分悲凉。”
——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
美国正陷入内战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和宪法危机 —— 未来三至四年里,极有可能发生大规模暴力事件和联邦权力崩溃,而国家也极有可能分裂成交战的红蓝飞地。受政治、疫情、经济和全球危机影响,加之人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和否认,警告信号可能会被掩盖。但下面这些事的发生,已经毫无疑问:
首先,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将成为共和党2024年总统候选人。期盼他影响日衰、偃旗息鼓的人可能要失望了。特朗普在民调中遥遥领先;他正筹集大量资金用于竞选;而当前,民主党各候选人看起来不堪一击。除非身体有恙,否则特朗普将如期参加大选。
其次,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盟友正积极备选,不惜以一切代价确保胜出。特朗普对2020年大选的舞弊指控现在主要是为其未来可能的败选进行铺垫。而一些共和党候选人已经开始准备在2022年宣布舞弊,正如拉里·埃尔德(Larry Elder)在加州罢免选举中的所作所为。
与此同时,2020年业余的“停止舞弊(Stop The Steal)”运动已被一个有组织的全国性运动取而代之,以确保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拿下他们在2020年丢失的州和地方选票。而那些否认2020年大选存在舞弊,拒绝为特朗普“寻找”更多选票,实际上拯救了美国的、“负隅顽抗”的共和党州官员,正在其党内被系统性地清算、撤职和赶出办公室。共和党的立法机构正在赋予自己对选举认证过程更大的控制权。

截至今年春季,共和党已在至少16个州提出或通过了一系列举措,以把某些选举权力从州长、州务卿或其他行政官员转移至州议会。亚利桑那州的一项法案明确指出,州议会可以通过简单多数投票“撤销州务卿颁发的总统选举认证书”。有的州议会试图对涉嫌“技术违规”的地方选举官员处以刑事处罚,这包括挡住选举观察员的视线。
因此,混乱的局面正在形成。想象一下,当两党议员均宣称获胜,并指控对方试图违宪夺取权力,多州爆发长达数周的大规模抗议。相比2020年,此时的两党准备更充分,更有可能加害对方。州长们会召集国民警卫队吗?拜登总统会将警卫队国有化,并将其置于麾下吗?他会启动《叛乱法案》(Insurrection Act),派军队去宾夕法尼亚州、得克萨斯州或威斯康星州镇压暴力抗议吗?在州行使联邦权力通常会被谴责为暴政。
拜登(Joe Biden)将发现自己来到几位前总统——拒行联邦法危机时期的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南部各州独立后的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等——曾经所处的位置,在没有规则和先例的情况下航行,对拥有和不拥有的宪法权力做出自己的判断。
如果美国的政治体系陷入一场宪法没有提供补救措施的危机,那么今天关于“拉布”(filibuster,以阻挠议案为目的冗长辩论。参见《纽约时间》相关文章:《Filibuster 的前世今生》)的争论在三年后就会显得过时了。
几乎所有美国人——除了个别政治家——都拒绝认真看待这个问题,没有试图阻止其发生。正如在其他出现法西斯领袖的国家中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潜在的反对者在困惑与惊异中被这个富有魅力的独裁者所折服。他们遵循标准的绥靖模式,而绥靖总是始于低估。自特朗普于2015年首次亮相以来,两党的政治和学术机构便一直在低估他。他们低估了特朗普的人气,以及他对追随者的控制度;他们低估了特朗普控制共和党的能力,然后,又低估了特朗普为了保有权力能走多远。
特朗普未能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的事实让很多人长舒了一口气,这表明美国的制度仍然是安全的。但如果拜登没有在所有四个选票都接近的州安全领先,如果特朗普更有能力,对其政府、国会和各州的决策者控制力更强,那么结果会完全不同。事实上,今年早些时候特朗普差点就发动了一场政变。阻挠这起政变发生的只是少数几个有胆有识,不愿服从自己认为错误的命令的州官员、两名检察长和一位副总统。
当然,这并非是制宪者在制定宪法时所考虑的制衡,但特朗普却暴露了这些保护的缺失。开国元勋们没有预见到特朗普现象,部分原因是他们没有预见到全国性政党。他们预料到了煽动者带来的威胁,却没有预料到全国性的个人崇拜。他们曾推断,新共和国幅员辽阔,13个竭力想独立的州将会阻碍全国性运动的发展。但他们却认为,“小小”的煽动者凭借其名气和影响力可能会对他们自己的州施以影响,但由于人口众多,加之利益分歧,他们无法撼动整个国家。
因此,制宪者制定的这种制衡完全取决于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分权的分立程度。他们相信,每个分权都将积极地捍卫自己的权力和特权。制宪者没有立法防止全国性党派团结超越州界,因为他们认为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他们也没有预见到,国会议员,或许还有司法部门的官员,会拒绝检查他们自己党派的总统的权力。
然而,近几十年来,对政党的忠诚已取代了对分权的忠诚,在特朗普时代更是如此。正如两次弹劾特朗普所显示的,如果议员仅仅因为总统是他们的政党领袖就为他作辩护或忽略他的不当之举,那么定罪和罢免几乎是天方夜谭。在这种情况下,除共和美德外,制宪者没有留下任何其他可以防止政府夺权的制衡法律。
批评人士和支持者一直未能认识到特朗普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多么独特的人物。由于他的追随者基本上都属于保守派,很多人认为特朗普只是里根革命的延续或顶峰。
这是错误的。尽管特朗普的大部分支持者都是共和党人,但他们信奉的理念不一定是所有共和党人都认同的。特朗普的一些支持者还是前民主党人和独立人士。事实上,推动特朗普运动发展的激情由来已久,并曾在两党中盛行过。
对联邦政府的质疑和敌视;种族仇恨和恐惧;对现代世俗社会破坏宗教和传统道德的担忧;在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的经济焦虑;惟我独尊怨恨对方的阶层张力;对更广阔的世界,尤其是对欧洲的不信任,以及对欧洲颠覆美国自由的隐密影响的担心 —— 自反联邦主义者(anti-Federalists)、威士忌叛乱(Whiskey Rebellion)和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以来,这种观点和态度一直是美国政治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主党曾是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大本营,直到他们于1968年加入了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阵营(铁腕白人至上主义者,曾利用公权实现了他的种族隔离主义愿景——译者注),而后又加入了共和党。自由派和民主党尤其需要区分他们与共和党政策的持续斗争和特朗普及其追随者所带来的挑战:前者可以通过宪法制度的程序展开;而后者则是对宪法本身的攻击。
特朗普运动在历史上的独特之处不在于其激情和偏执,而在于对于数百万美国人而言,特朗普本人即是对他们的恐惧和怨恨的回应。在美国以前的政治运动,领导人和追随者之间的纽带从未这么强有力。尽管开国元勋们曾担心美国会出现国王或另一位“恺撒(Caesar)”,但两个世纪以来,事实证明美国人对政客并不盲目崇拜。他们并不认为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格兰特(Grant),乃至华盛顿(Washington)是完美无瑕的。伟大的民粹主义领导人也是如此。

一个世纪前,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因提出了某些思想和政策而备受推崇,但他的追随者并不认为他是绝对正确的。即便是里根也曾因兜售保守原则、赤字开支、在堕胎问题上模棱两可,以及对苏联“软弱”而受到保守派抨击。
特朗普则不同,这就是政治体制难以理解他,更别说遏制他的一个原因。美国自由派倾向于用物质和经济来解释万事万物;毫无疑问,特朗普的许多支持者有理由抱怨他们的生活遭遇。但他们与特朗普的关系还扯不上经济或物质问题。他们认为,美国政府和社会已被社会主义者、少数群体和性变态者所俘虏。他们认为共和党建制派腐败无能——用特朗普的话来说就是,“Loser”,无法挑战执政的自由派霸权。
他们认为特朗普强势且有魄力,胆敢与建制派、民主党、自由媒体、激进组织、科技巨头和“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式的共和党人”较量。他超凡的领导力给了千百万美国人使命感、赋权感和新的身份认同感。虽然特朗普的批评者认为他太自恋,不可能成为任何类型的领导人,但他的支持者却喜欢他的毫无歉意、好战逞能和自私自利。与共和党建制派不同,特朗普代表的不仅仅是白人,而是一群愤愤不平的美国人,他们觉得自己受够了欺负与压迫。而这就是他需要做的全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