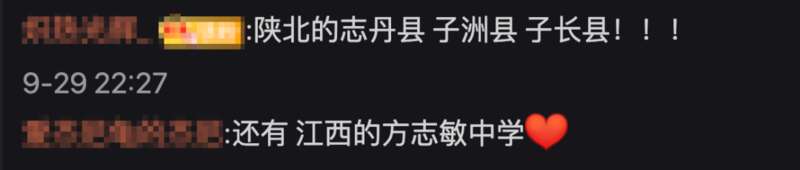在一曼村村民的身份证上,“一曼”二字如一个恒久鲜明的章戳,印刻在上面。人们用这种直接而深情的方式,纪念出生在这里的抗日英雄赵一曼,也纪念那段铭刻于心的历史。



类似的纪念方式,还在中国更多地方存在着。总被说“赧于表达”的中国人,在怀念英雄这件事上,却总有最动人最直白的宣告。
何以念英雄?
是以英雄为指引的路标,而路标上的字,简短、厚重——那是你的名字。
这,不啻另一种“浪漫”!

在哈尔滨,也有一条一曼街,除了一曼街,靖宇街、尚志大街、兆麟街、兆麟公园,也都是当地人熟悉的地名。





今时今日,民族英雄赵一曼、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等,以这样一种融进人们日常生活的方式,活在人们每天的烟火气里,见证着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而人们对英雄的怀念,也潜移默化地化作一种入骨入心的习惯:是导航地图上的清晰标记,是公园遛弯时的抬头一瞥,是每次看到路标时心头的微微一动。

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延乔路”,在电视剧《觉醒年代》播出后,许多人自发来到这里,悼念陈延年、陈乔年两兄弟。
当地的地名规划专家说,最初想将陈延年、陈乔年命名为两条路,可终究不忍将两兄弟分开,于是有了现在的“延乔路”。



“延乔路”很短,与它平行的“集贤路”较长,它们前面是一条特别宽的大道“繁华大道”。如今人们说:“延乔路短,集贤路长,它们没能汇合,却都通往了繁华大道。”冥冥之中,这仿佛是一种美好的预示:革命先烈为之奋斗的幸福社会已经实现。
(注:延年乔年的父亲陈独秀葬在今安徽安庆集贤关,故而延乔路与集贤路的分布更显深意)

值得一提的是,《觉醒年代》的编剧龙平平的爷爷崔筱斋,当年也是“戴镣长街行,走向刑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筱斋路”,同样承载着安徽人民对他的怀念。

曾经,英雄一步步踏出了胜利道路,如今,道路上处处写满英雄的名字。
“路名是无形的纪念碑,路在碑就在。”

在上海,有许多以“晋元”命名的地标:晋元路,晋元中学,晋元纪念广场,晋元里,晋元公园,晋元体育中心……谢晋元这个名字,是烙印和深植于上海的记忆之一。



淞沪会战中,他率“八百壮士”死守上海四行仓库,孤军奋战四天四夜,用生命守护了一个民族的尊严,更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抗战热情。在被叛徒杀害前,曾有人劝他潜离上海,他却说:“光明而来,亦当正大而去。”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样一位刚毅果敢的抗日英烈,也曾向往安静的世外生活,想要“抱入山唯恐不深之愿,以待余年”,却因为抗战大局“始终未有片刻安闲”。
常有人问,和平年代我们为什么还要怀念英雄?这便是原因之一:他们曾经想过而没能过上的生活,如今是我们在安享着!

在山西,有一个县叫左权县,在1942年9月之前,它被叫作辽县,左权将军牺牲后,为了纪念他,辽县易名为左权县,“两千多平方公里大地为他更名。”

而在左权将军的家乡湖南醴陵,也有左权镇、左权路、左权红军小学……人们以各种方式缅怀着这位“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八路军最高将领”。


英雄也是凡人,他也是某个人的丈夫——就在牺牲前的几天,他还在信中述说着对妻子刘志兰的思念:“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

英雄也是凡人,他也是某个人的父亲——牺牲那年,他的女儿只有2岁,在家书里,他写道:“我的最亲爱的人,恰在千里之外,空想一顿之后,只得把相片摆出来,一一地望着。”

英雄也是凡人,他也是某个人的儿子——牺牲七年之后,左权的母亲才知道儿子不在的消息。坚强的母亲没有恸哭,而是请人代笔撰文悼念儿子:“吾儿抗日成仁,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
正是无数个这样的凡人,这样某个人的丈夫或妻子,某个人的父亲或母亲,某个人的儿子或女儿,以自己的热血牺牲,换来了不凡的抗战胜利!换来了今日的盛世华景!

除了以上这些,在央视新闻微博的评论里,网友们还分享了更多他们身边用烈士名字命名的地点、建筑。
在一位位网友的分享里,我们惊觉于这场深情的盛大!我们感动于这种铭记的深刻!它发生在中华大地的各处,提醒着我们革命的星火曾如何燎原,提醒着我们先烈的牺牲有多么勇毅,提醒着我们今日的山河是多么可珍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