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优雅变老的艺术:美好生活的小哲学》第3章(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原文标题:《“老龄化社会”还是“赢得的时光”?》,作者:奥特弗里德·赫费 [德],头图来自:《飞屋环游记》剧照
由于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今天我们常说到“老龄化社会”和“老龄化”,然后就不由自主地想到不断加剧的衰老,欧根·罗特(Eugen Roth)以他的讽刺诗句对此进行评论:“一个人在电车里/ 一个挨一个地打量着人们:/ 突然间他准备放弃/ 各种永生。”
害怕在经济领域,可能也害怕在科学文化领域中创新力下降,与此同时,需要护理的人数却不断增长,我们社会的这种占主导地位的自我认知是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关于“西方国家的没落”的文化批评论断的一种当代变体,实际上经不起进一步的审视。
首先,这让我们想到了一种多义性。德语中“Alter”这个词并不必然意味着一个人生命的晚期。“年龄结构(Altersaufbau)”“年龄的确定(Altersbestimmung)”“年龄限制(Altersgrenze)”和“年龄差别(Altersunterschied)”,还有“盛放的岁月(blühendes Alter)”和“岁月的力量(Kraft des Alters)”这样的表述至今可以证明,它一开始并不专指高龄。
拉丁语中,“aevum”更多是用来表示年代和时代,而“aetas”是用来表示年龄、年纪的(s. Deutsches W¨orterbuch ,Bd. I,268f.)。并且这一意义很可能是从高龄的相反阶段发展而来的,即意味着“从未成年成长起来”,然后再扩展到一般意义上的“年龄段”,然后才是与之前所有的生活阶段不同的“晚年(senectus)”的意思。
“高龄”这个阶段经常会与“老年护理”“养老院”“老弱的人”“养老金”和“老花眼”这样带“老”字的表述联系起来,“老龄化社会”及“老龄化” 的概念暗示了高龄阶段和晚年。
源自实践的社会研究却给出了一个与字面意义相悖的结果:近年来,变得需要被照顾的风险几乎没有上升,而且痴呆症的患病率甚至有所下降。我们当然可以提出异议,因为现在有一半的医疗费用都投入在65岁以上的人群。但无论人是在年老还是年轻时死去,这一半的费用其实都用在了其生命的最后六个月。
如果将所有社会研究结果放在一起,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新的总体印象,真实情况比我们所说的“老龄化社会”好得多,我们应该称之为“赢得的时光”:我们没有患上因年老而产生的疾病,这样度过的时光意味着我们的“健康期限”已经大大延长了。因此,我们并不是面临老龄化,而是“赢得了生活质量”。相比前几代人,今天的老年人更少患梗阻和血管钙化,他们的大脑甚至普遍更大了。
不断提高的预期寿命
与不假思索的“老龄化社会”的说法恰恰相反,这种新的形象强调“赢得的时光”,而且从人的预期寿命的巨大变化开始。16世纪,米歇尔· 德· 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在随笔《论年龄》(De L’aage ,1580)中写道,那个时候,“人死于老弱非常罕见,是不同寻常的死亡”。自1840 年获得可靠数据以来,人的平均预期寿命翻了一番,而且每10 年会提高2.4 岁。20 世纪初,中欧60 岁的人预期平均还能再活13年或14年,今天,这一预期提高了一倍,大概是再活24年,女性的预期寿命相较男性稍微高一些。
预期寿命提高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直到20世纪,瘟疫一直席卷欧洲,如天花、鼠疫、霍乱、斑疹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肆虐欧洲的西班牙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数比世界大战本身的死亡人数还要多。
幸运的是,西欧和北欧70多年以来没有再受到战争的伤害。卫生条件的改善、抗生素的使用和其他医学及保健方面的进步,加上工作和居住状况的改善、营养条件的改善,以及其他更审慎的生活方式,还有冷藏使食物不易变质,都使欧洲大部分地区人的平均寿命有所提高。
其实,在两千多年前,许多伟大的希腊人已活到了非常大的年纪:雅典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活到90 岁,和后来的哲学家皮浪(Pyrrhon)、毕达哥拉斯一样;诡辩家高尔吉亚(Gorgias)甚至活到109 岁;众所周知,哲学之父柏拉图死于80 岁,到达了所谓“《圣经》的年龄(das biblische Alter)”(意指高龄);斯多葛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Epiktet) 活到88 岁;原子论的奠基人哲学家德谟克利特(Demokrit)活到89 岁。我们可以把这些当作特例,但希腊作家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在他的《名哲言行录》中所涉及的人,今天经过数据考查,平均年龄并不低于75 岁。
让我们再回到现代,还能找到无数例子,这些人的长寿并不能归功于现代医学:弗朗西斯·培根在快100 岁时才去世,这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的人生智慧——“用餐、睡觉以及身体运动时无忧无虑,开开心心,是长寿的秘诀之一”。
现代早期卓越的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曾为培根担任秘书,他尽管树敌无数,还有过两次艰苦的逃亡,却还是活到了91 岁。伊曼努尔·康德虽然自出生以来就体弱多病,却在57 岁那年发表了作品《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这部作品第一次使他在世界上声名鹊起,之后他又活了23 年,并且不断地出版哲学著作。
今天,男性的预期寿命只比希腊哲学家高三年,就这三年来说,可以说现代医学对于提高预期寿命方面的贡献相对并不大。今天我们所享有的平均预期寿命其实早已有之,只不过从前大部分这样长寿的人都属于受过教育的中上阶层。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研究人员通常很少注意到另外一个研究结果:不仅仅是希腊名人,除了我们所谈到的哲学家,还有许多其他近现代的天才都活到了更高龄。戈特弗里德·贝恩(Gottfried Benn),非学院派研究老年人的学者,同时也是医生和作家,不同于那些受专业限制的人,他引证了当时已经去世的画家和雕塑家,例如99 岁的提香和89 岁的米开朗琪罗。他还提到了86 岁的戈雅(Goya)、88 岁的利伯曼(Liebermann)、81 岁的蒙克(Munch)、83 岁的德加(Degas)、86岁的莫奈、90 岁的门采尔(Menzel)。贝恩所提及的18 个人,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平均年龄近84 岁,比希腊著名人物的平均寿命高了近10年。
然后贝恩提到了诗人和作家,歌德活到83岁,萧伯纳94岁,托尔斯泰82岁,伏尔泰84岁,维克多·雨果83岁,格哈特·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84岁,冯塔纳(Fontane)79岁。这里他提到了26个人,平均年龄为82.4岁。伟大的音乐家如威尔第(Verdi) 活到了88 岁,许茨(Schütz)87 岁,海顿(Haydn)78岁,凯鲁比尼(Cherubini)82岁,15个人平均寿命近79岁。
贝恩的评论很有道理,他说这些数据首先驳斥了“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意识形态”所说的“艺术耗费心力的特征”,所谓的典型——如席勒46 岁时去世,克莱斯特(Kleist)34 岁去世——或是有严重疾病(如席勒),或是自尽(如克莱斯特),并不是由于艺术将其生命消耗殆尽。最重要的是,他在这里与蒙田的看法相悖,认为衰老根本不是什么新话题,新话题只是所有民众都期待长寿,而并不仅仅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和天才有这样的愿望。
但在1930 年代的《故乡》(Altheimatland )杂志的一篇报道中,根据一位巴伐利亚高官的说法,在1800 年,泰根湖(Tegernsee) 地区的女人尽管要生8 到10 个孩子,但她们都能活到“80岁”,而男人却很少有活到“60~70 岁”(Tegernseer Nachrichten,M¨a rz 2008,26)。
这一点上,让我们看一下人类生物意义上的亲戚——灵长类动物。研究表明,智人与猴子和狐猴(原猴)有共通的衰老模式。在生命之初,死亡率非常高(不过人类只有从前才是这样),然后在青少年阶段死亡率很低(倘若不卷入战争),以及——请允许我道出一个众所周知的论断——随着年龄增长,死亡率再次增高。
众所周知,女人比男人预期寿命高。猴子也是这样,但是有一点区别很有意思:灵长类的雄性越是追求雌性的青睐,两性之间的寿命差别就越大。在几乎是一夫一妻制的猴子中,两性之间寿命差异较小,相反在多配偶生活的大猩猩和黑猩猩中,两性之间寿命差异很大。因而那些过着禁欲生活的人类,那些未婚独身的人,还有僧侣、修女等,他们的预期寿命差异将会很小吗?随着妇女越来越多地参与职业生活,我们将会见到两性预期寿命的差异缩小吗?女人需要得到男人垂青的职业领域是不是尤为如此呢?
按日历划分人生阶段值得推敲
一个社会、一个团体根本不可能老化,所以老龄化社会的说法具有误导性。更要命的是,它还以外部日历为导向设置了年龄限制,而不是以实际生活和经历为导向,即既不是参考生物意义上的,也不是参考情感、社会及精神意义上的年龄。
根据历法年龄,老年于60岁开始,不仅在西方国家,在世界各地都是广为流传的传统。这一说法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中世纪和近现代在欧洲得以巩固和继续发展,非欧洲文化也是如此。但实际上,在历史中最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说法其实更多具有一种象征意义。
很少有人知道他们自己到底有多大。这一事实令我们这个有出生证明和身份证的世界着实感到震惊,而这并不是由于缺少出生和死亡登记,而是在当时的生活和工作中,对于自身年龄的认知并不重要。很多时候,某些领导职位对年龄的要求只有下限而没有上限。
本质上讲,到了工业社会,尤其是因为20世纪的退休金、养老金制度,这种以日历划分人生阶段的方式才获得实际的意义,并同时支配了整个生活。只有在某些领域才可以不受退休年龄限制地工作,如在政治领域,或作为独立企业家、乐队指挥、知识分子和作家生活。
这些群体示范性地展示了很多人的情况:身体、精神、灵魂都不会退休,更不会今天还工作着,明天说退休就退休。此外,健康及工作能力方面的个体差异不断加大,同一年龄段的人与平均值的差异到了老年会更大。
持久的活力
单凭较高的预期寿命并不能证明“赢得的时光”是正确的。重要的是,“健康期限”这一说法使人联想到,无论身体还是精神,另外还有情感和社会方面都保持持久的活力。
再以哲学家为例:2016 年末到2017 年初,有人从海尔曼· 吕贝(Herrmann Lübbe) 开始,为精神健康并超过90 岁的德国哲学家进行排序。吕贝后面是迪特· 亨利希(Dieter Henrich)、罗伯特· 施佩曼(Robert Spaemann) 和克劳斯·海因里希(Klaus Heinrich)。海尔曼· 克林斯
(Hermann Krings)享年90 岁,卡尔-奥托·阿佩尔(Karl-Otto Apel) 享年95岁,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甚至活到近98 岁,汉斯-乔治· 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享年102 岁。今天如果被问及年龄,很多人都认为他们现在正处于“最好的年龄”,他们会觉得自己比实际年龄年轻10 到15 岁。无论如何,如果说每个60岁的人都“老了”,那就真的太草率了。
但是我们另有一个真相:孩子生得更少了。问题并不在于人们所说的人口老龄化,而在于缺少年轻人,也就是“Unter¨jungung”。今天,生活在欧洲的超过60岁的人比15岁以下的人还要多。
人口结构已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这是无可争议的。随之而来的却并不是“老龄化社会”,而是结构上的年轻化。英国老年问题研究员汤姆·柯克伍德(Tom Kirkwood)问,我们为什么在病历中赋予年龄如此重大的意义,他表示:在家庭护理和养老院中,至今都要求填上年龄,为什么我们不干脆把年龄去掉,而以人的生物状态为导向呢?(Kirkwood 2001)另外,以精神的(认知的)、社会和情感的(心理的)状态为导向应该更明智。
尽管只是特例,但电影世界展示了更广阔也更现实的可能,例如《007》系列电影就让50岁的女演员莫尼卡· 贝鲁奇(Monica Belucci)扮演所谓的邦德女郎。还有一些50多岁的演员,如朱丽叶·比诺什(Juliette Binoche)和朱丽安·摩尔(Julianne Moore),甚至60多岁的女演员梅丽尔· 斯特里普(Meryl Streep),也扮演着生动、迷人的角色。与年轻的美女相比,她们因生活经历而更加成熟,脸庞看起来不那么平淡。电视节目中最受欢迎的侦探系列剧的剧名正是《退休警察》(Die Rentnercops )。
我们不必害怕罗伯特·波格·哈里森(Robert Pogue Harrison)的小说《我们为何膜拜青春》(Juvenescence ,2014) 以及电影《年轻气盛》(Youth ,2015) 中所宣扬的,为了永恒的青春而废除掉年龄。以日历纪年来看,年龄增长而带来的成熟往往在多年以后才能被看出。就统计数据来说,老年人年轻化的现状也与所谓的人口老龄化是对立的,“老龄化社会” 及“老龄化”这些概念掩藏了老年人年轻化的事实,暗示节奏缓慢而不是生机勃勃,暗示保护既得利益而不是为了创新的喜悦而愿意冒险,暗示人们囿于过去而不是以未来为导向。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到了老年一切都变得更糟,似乎对于悲哀的晚年的恐惧也社会化了。事实上只不过是身体力量更小,反应更迟钝罢了。但通常情况下,我们有了更多经验、社会能力和日常生活的技能。
因此,从前占主导地位的老年人形象,即贬损的、匮乏的形象被经验丰富、活力持久的能干形象所取代。国家不必过分担心老龄化的社会,因为国民经济是不会停滞不前的。
人口统计研究员凡妮·克鲁格(Fanny Kluge)甚至期待变老的人口更有成就、更环保、更富有、更健康:老年人受过较高教育的比例提高了,所以更有成就;老年人比年轻人消费得更少,旅游更少,所以更环保;老年人财产分配给更少的孩子,所以更富有;而且他们疾病减少,所以更健康(Kluge u.a. 2014)。
尽管有人并不完全赞同这一乐观的判断,但由于专业技术人员缺口变大,由于近年来越来越多企业建立起来,也由于退休人员有更多时间去旅游,所以不可否认的是,今天的退休人员不再像从前一样坐在长椅上度过晚年,或只是从窗口注视着依然生机勃勃的人,自己却不再参与其中。
“2017 年忠利集团老年研究”显示,65 岁至85岁的德国退休人员对生活状况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满意:绝大多数退休人员认为自己经济不错,并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作出完全正面的评价。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果是:过去的退休人员政策就仅仅是护理政策,而今天,这种以护理为主的政策根本不再适合晚年的多样性了。
有益于老年人的学说
勒内·笛卡儿在他卓有影响的《谈谈方法》(Discours da la méthode,1637,第五部分)中预计,在未来,我们不仅会“摆脱无尽的肉体和精神的疾病”,而且凭借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医学,我们“也许还会摆脱老弱”。
然而最好的医学,即使延伸到化妆品和保健品业,也难以阻止典型的衰老现象。脱发和头发花白虽然可以通过染发、植发,严重时甚至可用假发套来克服,但要真正克服其他衰老现象是很困难的,如肉体及精神灵活性的降低、皮肤松弛、关节炎,由于短期记忆衰退而找不到合适的词的事儿也不断发生。柴可夫斯基的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奶娘叹息道,“从前所知道那些古老的故事,现在都记不住了”(第一幕第二场景)。
更有甚者,亲朋好友都相继去世。简·加尔达姆(Jane Gardams) 的小说《最后的朋友》
(Letzte Freunde ,2016)中,一个女人叹息道,童年和青少年生活过的地方经常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前的故乡现在变成异乡了,因为在那里既没有家的感觉,也感觉不到自己受欢迎。
特别是一些流行歌星,虽然他们按照“活在当下,及时行乐”这样的口号生活,或者是“希望我在变老前死去”,实际上有些人过早地燃尽了自己,另外一些人则为无节制的生活付出了代价,生命尽头很少有快乐。还有一些人也活到相当高龄,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鲍勃·迪伦(Bob Dylan)在七十几岁时依然非常活跃。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曾经将晚年恶毒地描绘成精神针对肉体的战争,在此战争中,对于肉体来说,失败是无所谓的。而有益于老年人的学说就是要对抗这种无所谓。这些学说帮助我们的精神来享受“赢得的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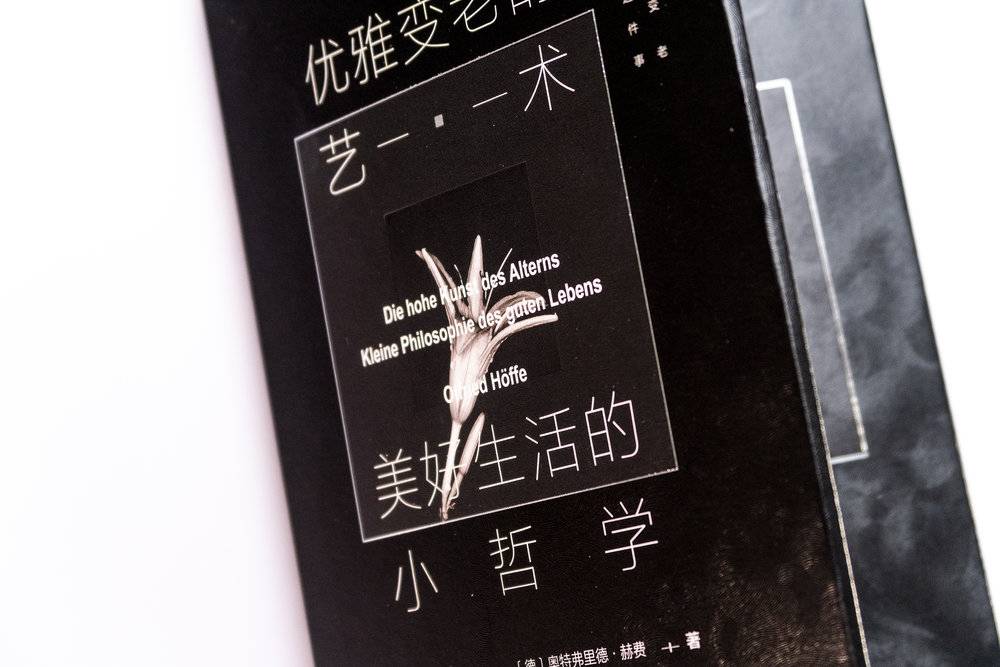
作者:[德]奥特弗里德·赫费(Otfried Höffe)
译者:靳慧明
定价:49.0 元
出版时间:2021 年 2 月出版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文摘自《优雅变老的艺术:美好生活的小哲学》第3章(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原文标题:《“老龄化社会”还是“赢得的时光”?》,作者:奥特弗里德·赫费 [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