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ID:new-weekly),作者:戈多,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一股高楼建造潮席卷中国,建造者们声称,要在“宇宙和地表之间建立连接”。但对普通的高空作业者来说,所谓的“宇宙美学”,或许只是一场心惊肉跳的灾难。
从300米的高空望下,地上的行人消失不见,最小的能见物是汽车,首尾相连的彩色斑点在灰色的轨道上移动穿梭,城市像一座铺展开来的模型。
俯瞰世界,是每一个高空作业者的日常。在这里,他们拥有了短暂的上帝视角。
回到地面,他们就成了“被世界俯视”的人。前一刻尽收眼底的“笋楼”,后一刻把他们层层包围、倾轧。在写字楼入口前,保安催促他们快速离开,白领看到他们绕道而行。
城市CBD里,没有高空作业者的位置,他们只存在于“云端之上”。

在全世界最危险的职业列表中,高空作业者始终位居前列。和其他事故不同,高空坠落,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
而高空作业者的命运,就盛放在一块58厘米长、16厘米宽的木制吊板上。一根直径 1.4 厘米的绳子,则是他们在空中与世界的唯一连结。
“蜘蛛人”是他们共同的名字,但他们知道,自己没有超能力。
一、恐惧和杂技
从事高空作业之前,任哥帮村里人盖过房子。
当他在2楼砌砖的时候,离地3米,任哥觉得腿软,“害怕自己会掉下去”。他怎么也没想到,日后,他会在城市几百米的摩天大楼外爬上爬下。

2014年,任哥的女儿在老家河南出生。女儿出生两个月后,妻子离开了他。任哥的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大伯、伯母三人全部患有偏瘫后遗症,生活不能自理。走前,妻子留下一句话:这样的家庭只会拖垮我的生活。
同年,任哥从河南来到广州。他想找一份工作,一份薪水可以同时养活5个人的工作。对于任哥这样低学历的进城务工人员,高空作业是他最好的选择。但他知道,高收入的代价是高风险。
第一次高空作业,任哥需要清洗33层高的写字楼外墙,100多米。此前,他参加过高处作业培训,演习场地是一个临时搭建的3层支架。从实操培训到第一次上岗,跨度是30层楼。
到了楼顶,任哥把绳子系到了消防管上——打一个水手结的时间,只要5分30秒。但他希望这个时间能更久一些,好让工作来得不那么快。走到楼体边缘的下吊处,任哥突然感觉到一阵头重脚轻,脚下的深渊仿佛在召唤他坠入。出于对死亡的防御本能,任哥退了回来。

不可抑制的恐惧,让任哥在楼顶徘徊了5个小时。本来早上9点出工,但直到下午2点,任哥才鼓起勇气坐上吊板。
任哥感觉腿不断地往下溜,手心的汗液让他的手掌在塑胶手套里打滑。任哥只能强迫自己,目视前方,不往下看。但玻璃墙映射着身后巨大的城市,时刻提醒着他所处的位置。
驯化自己对高处的恐惧、制止自己对于坠落的想象,是每一个行业新手的日常训练。
然而,摇摇晃晃的吊板、突发的天气状况,都会让人的恐惧感加倍。
想象一下,一个体重140斤、身高1.7米的成年男性,在空中的唯一支撑就是一个58厘米长、16厘米宽的木制吊板,并且一坐就是五六个小时;直径1.4厘米的主绳,在起风之后,会轻易地摆动、旋转,甚至打结。
“在空中,绳子转两圈你就晕了。但往下一看,百米深渊。”任哥的同行、年近六十的王师傅说。

55岁,是高空作业者的年龄上限,但为了攒钱给儿子娶媳妇,老王对这行仍旧“依依不舍”。在同行们看来,这个“中气不足”、身体瘦弱的“小老头”,骨子里有股不可思议的力量。
工作的时候,高空作业者是杂技演员,他们从吊板下的桶里不断掏出各种工具,胶枪、电钻、刷子、扳手等,不仅要保持平衡,还要防止“高空坠物”。他们的“招牌表演”是“高空秋千”。因为双臂展开所能够到的区域面积有限,所以高空作业者需要左右晃动身体,让“秋千”荡漾起来,以便触碰到更多的区域。
比如一个工人一次只能清洁两米宽的区域,一面墙需要5位工人同时作业。但是由于老板想要节省成本,只会雇佣4位工人,这样一来,每位工人都需要大幅度地左右摆动,去够到更多的区域。
每一次晃动,都成了对“恐高”本能的宣战。
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一股高楼建造潮席卷中国。城市CBD里“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摩天大楼成了城市发展的代名词。在广州,光是200米以上的建筑,就超过40座。
与此同时,建筑也越来越奇形怪状。螺旋状的“扭形”建筑、漏斗形建筑、帆船形建筑,等等,给高空作业者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这些造型古怪的超高建筑声称要在“宇宙和地表之间建立连接”。但对高空作业者来说,所谓的“宇宙美学”,只是一场心惊肉跳的灾难。
在刘慈欣的小说《中国太阳》中,倾斜大厦是蜘蛛人的恶梦。倾斜大厦的墙面与地面的角度小到65度,这也意味着,工人需要靠吸盘才能把自己固定在墙面,清洁玻璃幕墙。
但是吸盘不易固定。通常情况下,吸盘要打两三下,才能打稳,而且常常脱吸。一旦脱吸,工人会被反弹回空中、打转。没有着力点,人就像风中的纸屑,飘飘荡荡。
二、风雨和烈日
5月11日,一支“武汉大风中吊篮撞楼”的视频引发全网关注。此前一日,武汉局部遭遇10级雷暴大风。下午1点半,天朗气清,两名工人开始了高楼幕墙的保洁作业,1个小时之后,大风骤起,工人所在的吊篮连续撞击大楼幕墙。20分钟后,两名工人被救出送医,经抢救无效死亡。
这支视频,立刻在全国各个蜘蛛人的微信群里炸开。和往常一样,每一起有关蜘蛛人的意外事故,都会刺痛行业工作人员的神经,但大家又会在短短几天内,归于平静。

时间久了,这一行的人比谁都更懂得老天爷的残酷。
任哥曾数次感觉死神在他的身后追着他跑。遇到4级大风,高空作业者可以在空中一瞬间被吹到六、七米开外。每当遇到这种情况,任哥就紧抓绳子,蹬直双腿,以防大风把他再次推向建筑的时候,面部会直接撞击墙面。还有一种选择,任哥会和兄弟抱在一起,增加重量,减少在空中摆动的幅度。
国家《高处作业分级》规定,5级以上的大风天气,施工单位不得让工人进行高处作业。但实际情况是,工人所处的高度、建筑物的形状、建筑周遭的楼群环境,都会影响工人所受风力的大小。
地面上的三四级风,到了高层之上,风速可以增加一到两倍;在临近的高楼之间,“峡谷效应”会让风更加猛烈;高楼的拐角处,则是最让工人们紧张的位置,即使在无风的晴天,拐角处的风也能把人瞬时吹飞。
大风会将工人推在外墙上“敲打”,长期下来,工人们的腿上、胳膊肘上残留着各种伤痕、淤青。

只不过,疼痛事小,挣钱事大。工人们最关心的,始终是“今天能不能出工”“下一周有没有活干”。
武汉高空作业者事故后,人们最疑惑的是:为什么明明天气预报已经发出暴风预警,但施工单位还是让人出工?当普通人因为监管方安全意识的单薄而愤愤不平时,一些蜘蛛人的回答却出人意料地平静:应该是为了多赚点钱,可惜了。
蜘蛛人的贴吧里流传着一张照片:“暴雨钻空干,没雨拼命干。”出了事,工人们就会拿出这张图用以自嘲。
“如果严格地根据天气预报判断是否出工,那饭就没得吃了。”任哥说。实际工作当中,工人们会结合天气预报,加上现场的天气观察,决定是否出工。
因此,合格的高空作业者,都是观天象的高手,并且身体极为敏感。入行十几年的老贾就是如此。
老贾指着天边奶油状的白云说:“这是晴空云,不用担心。但如果云朵像女人的发髻,高簇乌黑的,大雨就要来了。” 工作的时候,老贾感到手臂上的毛孔都是张开的,感受风与湿度的变化。如果是闷热潮湿的低压天气,身体的毛细血管也会预警。
身高一米五几的老贾,体重140斤,走在地面上,还有些许的笨拙;但到了空中,他身手灵敏,反应速度极快。在同行中,年近五十的老贾理论基础最扎实,带出过不少优秀的徒弟。
如果和乌云不期而遇,高空作业者需要在短时间内从绳子上滑下来。以20层的高楼为例,下滑的时间可以快达五六分钟。在这个过程里,工人需要用右手按压副绳(注:主绳用于悬挂吊板,副绳又名辅助绳,用于防止意外坠落)上的自锁器,调整绳子下降的速度,以及自身的平衡。
如果雨点已然坠落,绳子会变得很滑,摩擦力减小,每一次下降的距离都难以调控。哐啷一下,工人就能下坠一大截。
最难的是夏天。
玻璃板的温度超过70 °C,手碰到上面,像是“炭烤猪蹄”;而玻璃板反射出的强光,会让人立即晕眩,严重时则会让人短暂地“视觉丧失”——眼睛进入苍白一片,这是视觉的极点,危险自然随之而来。
几年前,老贾的一个徒弟就因为长时间不戴护目镜,导致视力终身受损。年轻男孩怎么也没想到,进入蜘蛛人这行没两年,就烙上了视力残疾,只能再次回到工厂做工。
每次一下吊板,老贾总能感觉到一股磅礴的热气从脚下蒸腾而上、冲到下巴。
因为要身着长裤长袖,往往是“下吊”了一两层,汗水就已经浸透全身。干这一行的,一到夏天,身体上就长满痱子,但最痛苦的,还是晒到“蜕皮”。在阳光的强辐射下,皮肤成了一层脆弱的糊在身上的纸,一撕就掉,红色的肉暴露出来,风一吹,刺痛遍布全身。
从楼顶到楼下,单程需要1.5小时到三四小时不等。这期间,工人不能上厕所,并且需要极为专注;口渴了,就把嘴凑到清洁幕墙的自来水管边喝一口。如果半空中遇到什么突发问题,人可能会被吊在空中四五小时,导致双腿麻木、失去知觉。
落地的一刻,永远是最开心的时候。工人们会立马拿起自来水管冲着自己浇水,给自己降温。但经过的路人总以为他们疯了。
三、疼痛与危险
老贾伸出一双黝黑宽大的手,手背上密集的白色斑点格外显眼,那是被“酸”灼烧过的痕迹。实际上,大部分的高空作业者都有一双这样伤痕累累的“黑”手。
清洁玻璃幕墙的时候,工人们需要先在玻璃上刷一层稀释过的“酸”。常用的酸包括盐酸、草酸、氢氟酸,一旦触碰皮肤,会立刻引起疼痛、红肿反应,严重的会致残、截肢。因此,在做清洁工作的时候,高空作业者都需要全副武装,从雨衣、雨裤,到雨鞋、乳胶手套。
因为盐酸水,任哥曾被烧掉了两个指甲。当他意识到手套指尖已经磨损的时候,手指已经开始灼热。等他从二十多层的高楼上滑下来,右手的两个指甲已经脱落,鲜血直流。
但任哥是幸运的,指甲脱落之后,还会长回来,而有的人,因为酸而终身残疾。
去年11月,任哥的一个兄弟在高空作业中发现自己的雨鞋开裂,氢氟酸瞬间流进了脚跟。氢氟酸的腐蚀性为酸中最强,能够强烈地腐蚀金属、玻璃,更何况人的皮肤。氢氟酸不仅能够导致皮下组织坏死,而且可以快速腐蚀神经,“杀死”神经元。因此,氢氟酸又称“化肉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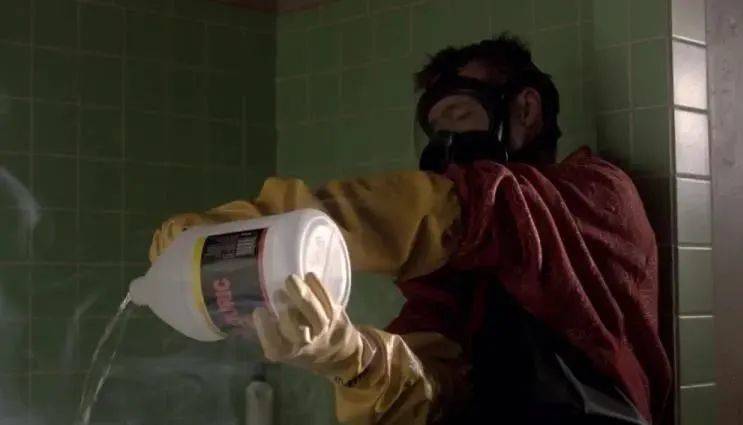
等到他着地的时候,脚后跟起了两个青色的大水泡,人彻底失去知觉。
“后来,这个大哥脚后跟的肉全被剃干净了,从大腿上挖了块肉补上去的。大半年了,还在家休养。”因为跛脚,这位大哥至今没有返工。由于施工单位责任不清,他没有收到除住院费以外的任何赔偿。
在“酸”之外,“自来水”也给高空作业者带来了长期的伤害。清洁工作中,工人需要用水冲洗大楼,幕墙上的水就会顺着吊绳流淌下来,溅到身上。长期“浸泡”在水中,工人们都会经历不同程度的关节痛、腰背痛、颈肩痛,在空中,这些疼痛会被极度放大。
高空作业者面临的更大风险,不是职业病,而是意外坠落。根据广东省应急管理处的数据,高处坠落为我国施工现场的四大伤害之首,占建筑施工事故总数的41%至53%。一旦坠落发生,只需0.6秒,工人的下落速度就会达到时速21公里,产生1089公斤的冲击力。
这些年,圈子里的每一起坠楼事件,任哥的另一位同行刘哥都“如数家珍”。去年3月,刘哥的一个朋友从3楼坠下,当场死亡。
出事后,刘哥朋友的绳子、安全帽等一系列作业工具,立刻被施工单位收走,禁止家属查看。但这件事却没有在圈内引起波澜——没收工具,已经是行业内默认的“事故处理行规”了。
“高空坠落,90%都是绳子问题,只有极少数情况是工人自己的问题。”老贾说。
一根主绳加一根副绳,不超过百元。但即便如此,施工方常常会在这些几十块钱的工具上想方设法“克扣”。有的时候,施工单位会在没有副绳的情况下,要求工人作业;如果工人发现绳子的磨损程度严重,向监管人提出意见,收到的答复时常是:这活你干不了,我就找别人干了。
然而,工人的性命,就挂在这一根绳子上。
为了让工人们更高效地工作,监工、包工头也会经常制造赶工游戏,激起内部竞争。监工们时常会在楼下拿出望远镜,像个指挥一样,观察他们谁干得最快、谁干活最慢。等到下次招人的时候,他们会专门联系那些干活快的工人。
于是,“内卷”开始了。本来3个小时能做完的工,现在2个小时就能做完,而快出来的1个小时,不仅没有帮助工人拿到额外的报酬和奖励,还让他们搭上了一系列的安全隐患。
这几年,安全隐患还在于入行门槛低、假证横行。

在国内,高空作业者必须持证上岗。考证之前,高空作业者需要做一系列体检,职业禁忌病如高血压、心脏病、恐高症都不允许上岗。但如今,培训机构不仅代出体检表,就连考试难度也降低了。甚至,可以直接“买证”。老贾说,但凡是湖南、江西、河南的证,十有八九都是找人代购的。
老贾透露:“培训机构以赚钱为目的,收了钱,就保你过。实操1天,理论3到5天。”未来的安全问题,他们根本不在乎。
四、影子工人:他们在清洁另一个世界
一面玻璃,分隔两种生活。
摩天大楼里,西装革履的白领吹着空调、敲着键盘,再下一层,旋转餐厅里,恋人们优雅切割牛排;消音玻璃的另一侧,是悬挂在烈日下、湿透了的蜘蛛人,他们脚踩百米高空,“命悬一线”。
他们时时刻刻都可以瞥见“墙内”的世界。对于任哥来说,他最渴望的不过是写字楼里的空调。
即使在写字楼里穿梭,高空作业者只能按照规定好的路线行走——他们要尽量避免与洽谈生意的CEO、争分夺秒的企业高管“碰面”。
他们不能乘坐普通的电梯,因为他们的形象会在白领中过于突兀、身上的气味会“妨碍”到其他人的工作环境。他们通常从地下停车场的货梯进入,直接通向楼顶。
碰到重要的领导接待,高空作业者需要立马停工。一个通知电话打来,他们就得从高楼外加速“消失”。
久而久之,高空作业者都有一种自觉:只出现在自己该出现的地方。
有一次,任哥和老贾在15层的写字楼外安装空调,结果楼顶的绳子缠在了一起,任哥和老贾就静静悬在空中,等待楼顶的同事处理。刚过5分钟,监工打来电话,说接到写字楼工作人员的举报,指控他们“偷窥”别人办公。
“偷窥”这个罪名,对蜘蛛人并不陌生。但他们无论以何种“得体”的方式工作,这项“罪名”还是会从天而降。
任哥说,在城市里,他总感觉自己是“被俯视”的。地铁上,他一坐下,旁边就会有人站起来离开;写字楼门口,保安永远都会对他和兄弟们大声呵斥;就算在超市里,推销员也会塞给他最便宜的东西。
任哥偶尔在走神的时刻,感到一种生存的荒谬。在云端,他看向脚下的城市,这里没有一寸是他的家——“干一年活,不吃不喝,我也买不起珠江新城一平方米的房子。”
他属于哪里呢?他不知道。
有一次,任哥在给一所小学做楼外装修。操场上,一位体育老师对同学们大喊:如果不好好学习,未来就要像这个叔叔一样,干这么辛苦的活!
“能当反面教材也挺好。”任哥笑了。
五、高空生活,老无所依
每当吊绳在风中剧烈晃动,老贾也感觉到了自己动荡的命运,那是缺少支点的命运,人只能束手等待老天对你的安排。1997年,20多岁的老贾从四川只身来到广州,但他的目的地,其实是香港。
“我想去看一下,‘四大天王’的老家香港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如今,20多年过去,他没有踏上过香港的土地。
中年离异,外加父母去世,老贾需要独自抚养在广州“借读”私立高中的儿子。生活的压力,让他选择了高空作业这一行。
在广州,高空作业者的工资为每天500元左右,最好的时候,一天可以拿到七八百元——“做这一行,没有什么自愿不自愿的,都是家里特别困难。你无路可走了,前面有一个悬崖,你跳不跳?”
“冒险精神“”城市勇者”,在高空作业者来看,都是大高帽,生活面前,没有选择。
在蜘蛛人的微信群中,“美女”是大家在谋生之外最常谈论的话题。老贾说,干这一行的,80%都是光棍。他们对婚姻和爱情有一种强烈地向往——这不,老贾本人,老王、任哥、刘哥全都离异了。
因为离异,“心里没老婆挂念”,入这行才没什么心理负担。
对蜘蛛人而言,再婚的机会也十分渺茫,虽说收入不低,但是女方一听他们工作这么危险、这么脏,基本都退却了。短视频网站上,有一句话踩到了他们的痛点:“好女不嫁工地郎,一年四季到处忙;春夏秋冬不见面,回家一包烂衣裳。”
不少“爱美”的兄弟对自己的“黑”特别在意。在他们看来,黑是一种择偶缺陷——你看,城里人“白”,帅气。
比起“蜘蛛人”这个称呼,老贾对“农民工”这个身份有着更强烈的认同,“得自己养活自己。”
生活的不安全感也来自高空作业这行的工作性质——零工群体。大部分的高空作业者都是日结工,干一天活,拿一天钱。他们没有劳动合同,工作受季节、天气影响很大。所以一年365天,他们就需要像候鸟一样,迁徙到各个地区找活干。
只是一年四季,干活舒适的日子屈指可数。
以广东地区为例,春节过后,行业内有一个月的空档期——工人们普遍在这个时候没活干;紧接着,梅雨季节来临,绵绵不断的小雨让出工难以保障;随后,5月到9月,高温天气持续,白天的平均气温在30 °C以上,午后两点,气温可以高达近40 °C;但到了冬天,手会因为寒冷变得僵硬,一碰到水,就更加难受。

此外,《劳动法》,在执行环节中,也经常被忽略。拿法定的劳动津贴“高温补贴”来说,这么多年,任哥和他的兄弟们从来没享受过。
这几年,行业内部有了一些进步,比如有了保险。只不过老板买的是集体险,保额不高。
这大概是工作给他的视角,想把日子过下去,就要从高处看问题,不能计较。
任哥的微信昵称是:希望在前方,我们在路上。
端午节快到了,行业的接活小高峰也来了,任哥、老贾,和兄弟们一起,又在忙碌的路上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ID:new-weekly),作者: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