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第二号玩家(ID:dierhaowanjia),作者:瓜,头图来自:《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
从东京大学,这个世界一流的学府毕业之后,他的面前出现两个选项:
选项A:用这个金光闪闪的学历作为敲门砖,进入日本最大的公司,从雇员做起一路晋升,最终成为高管。与一个美丽温柔的妻子组建幸福的家庭,并供养家人一直到退休。
选项B:同上。
但这个名叫Nito Souji的男人选择了隐藏的C选项,从那一天开始他躲进了自己的房间,这一躲就是十年。

十年后,Nito在YouTube上发布视频,记录下自己作为”骨灰级宅男“的一天——学霸宅起来,还是与我们普遍印象中的阿宅不太一样。
上午10点,他准时起床准备早餐,早餐是一份芝士吐司,一碗水果酸奶以及一杯咖啡,10年来,顿顿如此。Nito的房间不大,除了一张床,一张堆满了书籍纸张的桌子、电脑和数位板,就是一把椅子。
准备好早餐后,Nito蹲在地上,把早饭放在椅子上开始享用,这样还能一边浏览网页。

10年下来,这把兼职饭桌的椅子,把地面磨出了一道光秃秃的痕迹,从这块地面的斑秃上就可以想象Nito做了几十万次坐下又站起的动作。

Nito现在成为了一名蛰居型独立游戏开发人,因此在浏览收发一会邮件后,他开始开发游戏。下午2点是午餐时间,吃过后就可以继续投入到开发游戏的工作中。晚上7点半,这是工作间隙的休息时间,Nito用来健身和学习英语,直到晚上10点,他正式“下班”。
用房间厚厚的墙隔绝开996和大小周后,他的生活甚至可以说是规律且健康。
Nito的生活或许并不像我们一直以来对蛰居族的刻板印象,尽管他一直称自己为Hikikomori(蛰居族)。蛰居族是这样一些人群,他们逃避社会,隐蔽在卧室中,不接触社会、不上学、不上班,不与外人交往。一旦这样的状态超过半年,ta就可以被定义为“蛰居族”。

在日本,和Nito选择了同样生活方式的还有百万人。2019年,据日本内阁统计,蛰居族群体数量在日本已壮大到115万以上,年龄层次可从15岁跨越至64岁,其中80%是男性。
但一连蛰居10年的Nito算得上其中的王者级蛰居族了。
方寸之地
Nito是在从东大毕业后一头栽进自己的壳子里的。
在采访中,Nito表示自己是很喜欢纪录片的,所以在毕业之后他便投了简历给电视台和制作公司。
“但我极度厌恶日本的职场文化和人际关系,所以即便被这些公司拒绝了,我也没有放在心上。”Nito自己是这样说的。但或许可以想象,一个名校毕业、心高气傲的高材生,却在进入社会之初就碰壁,那么“厌恶职场”似乎也就成为了一个必要的理由。
而在日本,如果在最初的找工作过程中不够顺利,那么几乎就可以确定这个人失去了继续在职场上晋升的机会了,至少Nito是这样认为的。
在他还与这个世界保持联络的时候,他认识的一个东大前辈就因为毕业时没有找到心仪的工作,于是决定在学校里再待上一年,一年后才终于得偿所愿。
但Nito不喜欢这样,不过人总是还有别的出路,毕竟世上无难事,只要肯逃避。于是Nito决定放弃进入电视台这样的大企业,转而开始写作。
开始的计划总是很理想,Nito盘算着,一开始可以先做些零散的工作,然后用这些生活经验作为灵感写成书,等到写作获得的收入可以养活自己的时候就可以辞职了。
回忆起来的时候,Nito用他自学的,有浓重日式口音的英语一字一句地说道:“我那时真是傲慢又愚蠢。”
宅了一段时间后,Nito终于意识到,作为一个没有光环的普通人,那些随心所欲写出来的东西压根不被市场所接受,而当他想用适应市场需求的方式来写作的时候,却发现其实自己并不具备这方面的天赋——即使是龙傲天系列的烂梗网文也是需要功底的。
于是他放弃写作,“弃笔从黄”。

Nito搬回了老家,住进位于神户的婶婶的公寓里,靠着婶婶的接济过活。但是老家没有朋友,自己也没有经济收入,Nito渐渐对出门这件事情感到羞耻——他开始正式变成一名蛰居族。
蛰居在家的期间,闲着也是闲着,他买了数位板,开始自学画画,做起了同人志。
“说起来有一点羞耻,但是日本80%的专业同人志画手都是在画色情的内容,在日本,创作色情内容相对来说是更容易被接受的(或者说是更容易被忽略的)。”Nito说。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Nito用自己丰富的画可爱女孩技巧成功出版了两本书,一本在2014年,一本在2015年,两本加起来一共卖出去2000份,总收入93万日元,折合人民币大概在五万四。

对于一个没什么花销的蛰居族而言,五万四的收入似乎也能满足日常需求,但Nito更想在自己房间的方寸之地中找到人生的意义,而显然画同人志并不能做到这一点。而就在这个时候,虚幻引擎(unreal engine)平台免费开放,“这时我觉得,做游戏或许可以成为我人生最后的机会。”
家里蹲模拟器
被Nito称之为“人生最后选项”的是一款名叫pull stay的游戏,预计将在2022年4月正式发售,目前已经可以在steam上下载demo版。
Pull stay,就是日文“蛰居族Hikikomori”的英文直译,或许可以直白地翻译成“蹲在家”。

游戏目标很简单:保护这个名叫susumu的宅男,因为这个世界上多得是想要闯进他的房间里尽情嘲笑他的人,这些人有的是格斗家,有的是不良少年,甚至有可能是拉面师傅。可以说,是一个浓缩版的小社会试图闯进susumu与世隔绝的房间里。
而玩家要扮演的是一名和susumu长相一样的机器人,可以在横版2D的各个房间中设置不同的陷阱,有烤鱼炸弹,西瓜水枪或者牙膏大炮,带有浓浓的日式风格。
而在卧室中你可以放一个美少女等身抱枕,试图闯进房间的外来者看到美少女就会不由自主地躺到床上,抱紧抱枕,头上冒出爱心的泡泡,然后抱枕就会从中间裂开,变成兄贵,将敌人吸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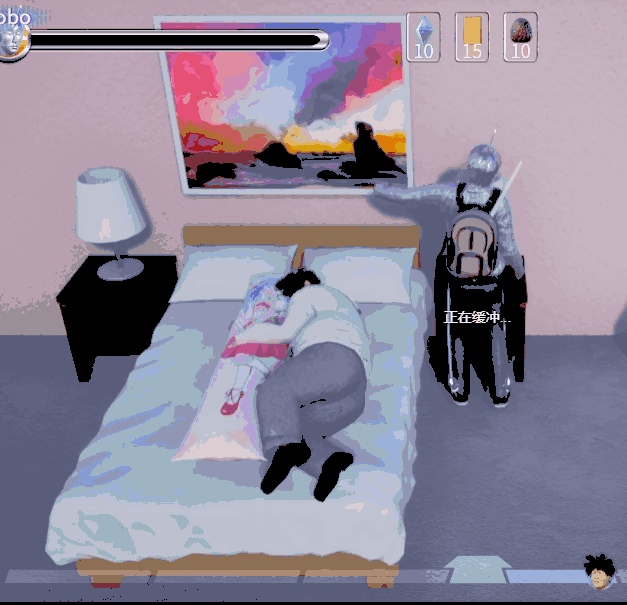
至于susumu本人——就像游戏标题画面剧透的那样,只会拿着一捧小花在洗衣机里转圈圈。

机器人与susumu共用着Nito本人的脸,这似乎也象征着Nito身体内的两个灵魂,一个是拒绝出门只会哭泣的懦夫,一个是钢筋铁骨打败一切入侵者的守护神。
在房间布置陷阱之余,机器人其实还可以通过格斗技巧打败敌人,有点像塔防与格斗的结合。而敌人掉落的材料则可以让susumu在自己的房间制作道具,用以增强机器人的各种属性。
但让人无语的是,机器人在与敌人厮杀的期间,还得抽空去看一眼躲在房间里的susumu到底有没有在认真工作,因为这个听到点风吹草动就开始哭喊着“救救我”的死宅,却在我杀得一脸血时安心睡过去了。
于是筋疲力尽的机器人还要把susumu从他的被窝里唤醒,而不知是什么逻辑,用乒乓球拍或者棍子将他一阵虐待后,这个胆小如鼠的宅男就会恢复活力,继续开始工作。
尽管只是demo版,但《pull stay》游戏本身还是稍显粗糙,一旦失败就只能从第一关重新再来,这降低了不少可玩性,建模看起来也有些简陋,不过这些都是Nito花费了五年心血开发出来的。
开发游戏最困难的部分在于英语,编程需要英语,写游戏脚本也需要英语。于是Nito在开发游戏时开始活跃在twitter上,坚持用英语发布,从一开始的颜文字和几个语气助词,慢慢地也能组织起一整段语言,甚至面对纯英文的采访。
这几乎是孤注一掷的梦想。“如果生命要用来做什么事情的话,我希望是去创造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作品。同时,我已经是一名蛰居族了,我再也无法逃到任何其他地方去了,所以开发这款游戏是我生命最后的出路。”
但当记者小心翼翼地问Nito,如果这个被你称作“人生最后选择“的游戏并没有获得成功,你会怎么办。
Nito的回答却意外地很洒脱,如果这部作品并没有达到期待,那么他将凭借这个作品寻找和游戏开发相关的工作,10年的蛰居生涯对他而言从来不是浪费,或许只是个时间长了一点的间隔年。而在10年的蛰居生活最终结束,重新踏入社会的那一刻,往后的人生显得危险却又值得期待。
尽管Nito依旧保持着线上与人交流的技巧,在每一个视频中也会毫不在意地表示自己蛰居族的身份,但或许他仍旧没有避开他人的目光,即便有厚厚的墙壁阻隔,但这个世界对于“懒惰”的鄙夷,还是有如实质般投向他。
所以在他的蛰居Vlog中,到了8点的点心时间时,Nito面对镜头表现出了一丝歉意:“对不起,作为一名蛰居族,但我还是吃了零食。“零食是葡萄干泡水和两块小饼干,依旧是放在被当做餐桌的椅子上。

都市隐士
像Nito这样只是不出门,但仍旧没放弃生活,甚至比很多打工人更努力追求梦想的人,似乎并不符合普遍定义上的蛰居族。因此,如果可以,我更想称他们为”都市隐士“。
见到大原扁里的时候,发现他虽然从不用化妆品,但却喜欢涂上一层厚厚的唇膏。这是因为虽然它看起来是保养品,但在分类上却属于准药品。
“虽然被排除在医药界之外,但我仍然算是药喔。”对于被社会划分出去,但仍然算是人类的大原扁理而言,这根唇膏就像同类一样。
某种意义上,大原扁里可以说是贫穷版的Nito。26岁那年,大原扁里决定过一种“做二休五”的生活——工作两天,休息五天,用最低限度的金钱保证生存。
他在东京郊区租了间房子,成为这个巨型城市里的隐居者。
食物是不需要购买的,因为路边就有很多可食用的蔬菜:加在味噌汤里的艾草,可当下酒菜的薤白,味道像笋干的虎杖,以及生食就有清香味道的紫苏。于是在东京这样繁华的大都市里,大原扁理却过上了采集时代的生活。
在这之后,曾经也做过工人,累倒在月台的大原扁里突然发现,原来生活根本不需要花很多钱:比起超市中各种品牌的洗衣液,廉价的小苏打就可以把衣服清洗得很干净;因为不需要社交与工作,手机也索性停掉了;图书可以从图书馆借阅,电影则可以在线上看免费的老电影;不需要医药保健的费用,因为这种生活方式他很少生病;近十年没有踏足过理发店,自己理发已轻车熟路;更重要的是,因为不需要租工作地点附近的房子,他只花了一半的价钱,就在东京的郊区租下了自己的房间。
后来大原扁里将这种生活方式记录下来,写成一本书《做二休五:钱少事少的都市生活指南》。
负责大原扁里的编辑曾经有些惊讶地跟我坦白:在此之前,他们也曾在成都举办过一场见面会,虽然也很热闹,但人数大概只有北京场的一半。他推测原因或许在于,住在成都的人们对这样的生活见怪不怪,因为他们本身的生活方式就距此不远,然而生活在北京的人们却对这样的生活既好奇又羡慕。
穿行在拥挤的一号线,奔赴华丽写字楼的北京白领们可能不知道,或许就在对面一家破败的居民楼中,就有一个年轻人,ta有着跟自己相似的高学历,却情愿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拒绝真正进入这座城市。
他们被称为“蹲族”,一个蹲族男孩在论坛上说起自己的蹲族人生:”出门的时候我还穿着短袖,这才发现已经冬天了。“
因为“蹲”,所以他们成为了都市中的隐形人,但蹲着的年轻人并不在少数,他们甚至在网络上成立了”家里蹲自救同盟“,参与者有近3万。
蹲着的原因多种多样,有校园霸凌,也可能来自家里过高的期许。有人认为这只是一种自私、懒惰的生活方式,但有人却认为这是对主流价值观的反叛,是另一种勇敢的面对——蹲着的年轻人们或许发现,只要距离这个世界够远,内卷就卷不到我。
就像《生活大爆炸》里,谢耳朵面对朋友们发出的森林徒步邀请时反驳的那样:如果野外真的那么好的话,那为什么人类花了几千年让室内变得更舒服呢?
Nito、大原扁里,还有北上广蹲着的年轻人们,或许在某种意义上也实现了我们的人生终极梦想。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第二号玩家(ID:dierhaowanjia),作者:瓜

